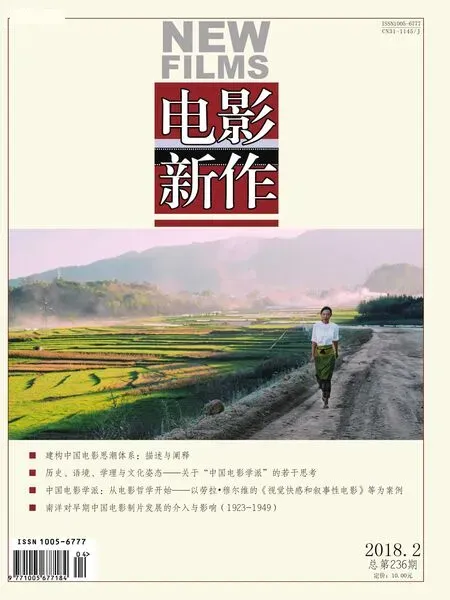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白鹿原》:從小說經(jīng)典到電影凡庸
——兼論小說改編電影的美學(xué)參照系
蘇月奐
小說《白鹿原》是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彪炳史冊(cè)的經(jīng)典文本,而電影《白鹿原》卻在一陣商業(yè)化的鑼鼓喧囂后淪為中國當(dāng)代電影中的凡庸之輩。《白鹿原》從小說到電影,其藝術(shù)境界和藝術(shù)命運(yùn)產(chǎn)生了云泥之差。這并非個(gè)案,而似乎是中國名著改編電影的共同遭遇。對(duì)于《白鹿原》的文學(xué)改編現(xiàn)象,盡管學(xué)界不乏探討,卻沒有觸及關(guān)于小說改編電影的美學(xué)參照系的重要元問題。那么,這些元問題是什么?應(yīng)該如何評(píng)價(jià)《白鹿原》的改編?可以從哪些方面提升《白鹿原》改編的質(zhì)量?
一
電影《白鹿原》的上映曾引起社會(huì)各界的廣泛關(guān)注,其中關(guān)于“改編”話題的討論尤其激烈。學(xué)界對(duì)《白鹿原》的改編有著截然相反的兩種評(píng)價(jià),一種是褒揚(yáng),一種是貶抑。這本不稀奇,一部電影總有其優(yōu)缺點(diǎn)。怪異之處是,發(fā)表在國內(nèi)知名期刊上的文章竟然對(duì)相同的電影元素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評(píng)判。這暴露出小說改編電影的美學(xué)參照體系的缺失。
吳輝和周仲謀各自從三個(gè)方面肯定了《白鹿原》的改編,其中有兩個(gè)方面是重合的。這兩方面分別是電影對(duì)小說的提煉式改編和電影對(duì)民俗的影像呈現(xiàn)。吳輝還稱贊了電影對(duì)原小說刪繁就簡的人物選擇,周仲謀認(rèn)為電影的主題表現(xiàn)也是成功的。更多的人則是對(duì)《白鹿原》的改編展開了包括這些方面的批判。謝剛提出,電影《白鹿原》在企圖兼顧刪繁就簡和存續(xù)史詩氣質(zhì)的矛盾中陷入了“騎墻敘事”的窘境,影片對(duì)民俗的展示也由于時(shí)代語境的改變和符號(hào)隱喻效能的衰退而淪為對(duì)地域文化的直白宣傳。潘樺認(rèn)為,電影《白鹿原》中核心意象和獨(dú)特人物的缺失導(dǎo)致電影失去了原著的詩性智慧和詩性品格。在主題方面,孫宜君提到,電影《白鹿原》忽視了原著的精神內(nèi)核。李楊也指出,電影《白鹿原》丟棄了小說的“去革命化”和“再傳統(tǒng)化”兩大主題,其漏洞百出的欲望敘事是“失魂落魄”的。雖然批評(píng)的聲音高于肯定的聲音,但聲音的高低、文章數(shù)量的多少不是判定《白鹿原》改編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
對(duì)《白鹿原》改編得失的探討固然應(yīng)該百家爭(zhēng)鳴,可是對(duì)諸多相同問題的判定完全相反卻并非正常現(xiàn)象。審美和評(píng)判的感受與角度再多樣,也不應(yīng)美丑不分,畢竟是非好壞總有個(gè)標(biāo)準(zhǔn)。改編似乎沒有可以遵循的尺度。原著就一定是完美無缺、至高無上的嗎?原著的品質(zhì)如何界定?改編的依附標(biāo)準(zhǔn)為何,還是完全自由?評(píng)論應(yīng)當(dāng)以什么為依據(jù),還是各說各話?誰是權(quán)威,市場(chǎng)還是學(xué)者?這些都是當(dāng)下小說改編電影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中十分關(guān)鍵卻被長久擱置的元問題。這些元問題呼喚一個(gè)統(tǒng)一的美學(xué)參照體系,沒有這個(gè)美學(xué)參照體系,再多的爭(zhēng)論也無法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

圖1.《白鹿原》
翻檢古今中外的敘事文本,那些經(jīng)得起時(shí)間淘洗的經(jīng)典必然是能夠陶冶情操、凈化心靈、啟迪思想的作品。而這些作品的形式不論是主觀化的,直觀化的,還是超現(xiàn)實(shí)化的,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特質(zhì),那就是都有“客觀真實(shí)”的內(nèi)核。所謂客觀真實(shí),就是對(duì)本真人性的再現(xiàn)和表現(xiàn)入木三分,進(jìn)而引發(fā)共鳴,令人回味無窮的藝術(shù)真實(shí)。那些堪稱經(jīng)典的藝術(shù)文本必然呈現(xiàn)了豐滿立體的典型人物和真實(shí)透徹的生活本質(zhì)。如果一本小說原著不符合客觀真實(shí),充斥著對(duì)人性的虛假描寫,它就是應(yīng)該受到批判的。如果一部電影能超越小說達(dá)到客觀真實(shí),它也值得贊賞。電影改編應(yīng)該以客觀真實(shí)為美學(xué)參照體系,既不離開原著,又不應(yīng)該迷信原著。一次成功的電影改編既應(yīng)該贏得市場(chǎng),也應(yīng)該征服學(xué)者。
不論學(xué)者們?nèi)绾卧u(píng)價(jià)《白鹿原》的改編,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gè)客觀事實(shí),《白鹿原》從小說經(jīng)典淪為了電影凡庸。電影《白鹿原》從上映之前的備受關(guān)注到現(xiàn)在的幾乎無人問津只不過寥寥數(shù)年的時(shí)間。從客觀真實(shí)的美學(xué)參照體系來看,《白鹿原》的改編有著較大的硬傷。這一方面要從藝術(shù)語言形式轉(zhuǎn)變過程中的變化上尋找原因,另一方面要從小說作者與電影導(dǎo)演的文藝素養(yǎng)和對(duì)故事的藝術(shù)把握上探求差距。
二
《白鹿原》從小說到電影的過程,藝術(shù)語言也由文字變成了影像。這使文本的共時(shí)性和歷時(shí)性兩方面的表達(dá)和接受都跳入另一種模式。共時(shí)性的跳轉(zhuǎn)指文字和影像的指稱功能,歷時(shí)性的跳轉(zhuǎn)指小說和電影的敘事接受。
文字和影像的指稱具有不同的本性,這決定了它們之間的轉(zhuǎn)換要損失一些美感。文字的所指和能指是一對(duì)多的關(guān)系,不同人的腦海可以聯(lián)想和想象出不同的所指模樣。在藝術(shù)活動(dòng)中,想象與聯(lián)想本身就是審美的進(jìn)行時(shí),影像也能指示文字所描述的所指,這使文本從小說到電影成為可能。但是在一級(jí)符號(hào)系統(tǒng)里,影像的能指和所指是重合的,影像中指示房子的那個(gè)事物就是所指示的事物,而且此事物不是概念而是具體存在。觀眾一眼即見,省掉了從能指到所指再聯(lián)想和想象的過程,也損失了這個(gè)過程帶來的美感。藝術(shù)語言的本性決定了它的制約性,這個(gè)損失不能避免,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藝術(shù)形式轉(zhuǎn)換的不可行。
雖然小說閱讀過程的想象和聯(lián)想美不可言,但那種想要探究“那時(shí)那地那人那事”的愿望卻因想象和聯(lián)想的增強(qiáng)而更加強(qiáng)烈。尋求確定性的欲求作為對(duì)安全感的原始訴求,深深鑲嵌在人類基因中。這種尋求確定性的基因讓接受者對(duì)藝術(shù)世界從小說到電影的轉(zhuǎn)變充滿期待,而且越是名著的改編越引人關(guān)注。另外,確定性的影像抹掉了想象和聯(lián)想的美,卻帶來了視聽享受的可能。電影世界能給予觀眾很多在現(xiàn)實(shí)中無法得見的奇觀景象,比如古代風(fēng)情、奇幻、美人等,其取景框的構(gòu)圖本身就富于美感,聲音的加入也使影像世界更加完整逼真。小說世界令人向往,用電影復(fù)現(xiàn)小說世界無疑更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因此,從藝術(shù)語言的共時(shí)性層面來看,從小說到電影是有失有得的,也符合一般觀眾的愿望。如果轉(zhuǎn)換失敗,則要反思一下,是原著文字魅力太高,還是影像水平太差。文字魅力太高的小說以文字為靈,一經(jīng)改編便把優(yōu)勢(shì)喪失殆盡。錢鐘書的小說《圍城》語言幽默風(fēng)趣、諷刺辛辣、比喻絕妙,這是小半人力大半天賦所鑄就的精靈般的文字,是任何其他藝術(shù)形式都復(fù)現(xiàn)不了的。文字水平并不卓越且以情節(jié)見長的小說最適宜改編,改編成的影像也容易獲得超越小說的魅力。電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啟用林青霞演繹東方不敗一角,林青霞的英氣和俊美是文字描摹不盡的。電影《阿凡達(dá)》美輪美奐的影像也讓文字無力。小說《白鹿原》的文字并非出神入化,還在適宜改編的范圍之內(nèi)。

圖2.《白鹿原》
電影《白鹿原》開頭那無邊涌動(dòng)的麥浪,極具地域特色和時(shí)代特色的房屋建筑、室內(nèi)擺設(shè),那些古樸農(nóng)民、古調(diào)秦腔都可圈可點(diǎn)。電影中的白嘉軒、黑娃、田小娥、鹿子霖,從形象上也比較符合原著的定位。特別是黑娃的扮演者段奕宏,小說人物的那種自尊與自卑、質(zhì)樸和魯莽、善良和反抗在他的外形中都能有所蘊(yùn)含。電影中白嘉軒的正氣和硬氣,田小娥的妖媚、大膽和智力不足,鹿子霖的狡猾善變,都比較符合演員的色相特征。但白孝文和鹿兆鵬兩個(gè)角色卻令人失望。白孝文比黑娃小好幾歲,在電影中看起來卻比黑娃老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的長相遠(yuǎn)遠(yuǎn)達(dá)不到小說后來提到的“儒雅的仁者風(fēng)范”的程度。鹿兆鵬的選角是電影最大的敗筆,在小說中他是作者最鐘愛的角色之一,“眉高眼大,睫毛又黑又長”,這樣有些“歐范兒”的帥氣面孔與眼角、嘴角、臉頰都下耷且?guī)в邢矂∩实墓鶟龑?shí)在掛不上鉤。當(dāng)然,電影并非不可以對(duì)原著的人物加以合理的改編,但是電影《白鹿原》似乎并沒有對(duì)這兩個(gè)關(guān)鍵人物的“形變”賦予特別的解釋和思考,而更像是一場(chǎng)選角“事故”。
除了文字和影像指稱功能上的差異,小說和電影敘事接受方式的不同也是改編時(shí)需要適應(yīng)的。讀者閱讀小說是在沉思中接受故事,觀眾欣賞電影是在觀看中接受故事。在沉思中接受故事時(shí),讀者的外部感官處于抑制狀態(tài),全部的大腦都處在內(nèi)向的思考中,而且思考的節(jié)奏由讀者自己決定。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選擇,再加上聯(lián)想和想象,讀者對(duì)小說的再創(chuàng)造程度就很高,因此一千個(gè)讀者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在觀看中接受故事時(shí),觀眾的外部感官是開放的,至少視覺聽覺處于高度的興奮的狀態(tài),腦力要分出一部分維持視聽興奮,剩下的才用來思考情節(jié)。另外,影像不會(huì)等人,觀眾只能按照電影的節(jié)奏去接受情節(jié)。如果電影的節(jié)奏過快,或者有些復(fù)雜,超出了觀眾的思維水平,觀眾就只能囫圇吞棗。如果節(jié)奏過慢或者太簡單,無法挑起觀眾的興奮,觀眾就會(huì)感到無聊。即使節(jié)奏適中,也難免眾口難調(diào),因?yàn)橛^眾的思維能力差距很大。電影一旦形成,觀眾就無法選擇接受速度,再加上聯(lián)想和想象的空間小,觀眾對(duì)電影的再創(chuàng)造程度就相對(duì)低,因此,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中,對(duì)敘事的把握和改造尤為重要。
基本成功的電影敘事有兩個(gè)要求,一是將故事講完整,二是情節(jié)節(jié)奏要遵循觀眾的大腦活動(dòng)規(guī)律。講完整一個(gè)故事似乎并不是難事,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且前后照應(yīng)緊密即可。小說《白鹿原》以白、鹿兩家為輻射點(diǎn),以眾多具有不同代表意義的人物為支撐,講述了從清朝覆滅到新中國建立這段歷史時(shí)期內(nèi)白鹿原的興衰變化。電影《白鹿原》似乎是想不失原著的宏大歷史性,所以將重大歷史轉(zhuǎn)折都以事件的形式點(diǎn)明,但電影似乎又難以填滿這么大的骨架,所以只選取了田小娥的故事加以詳細(xì)展現(xiàn)。這就造成了整個(gè)敘事的畸形,對(duì)宏大歷史來說,田小娥的角落太“小”;對(duì)田小娥來說,許多歷史事件都是多余的,宏大的歷史大而無當(dāng)。這同時(shí)又造成了情節(jié)節(jié)奏的拖沓和與觀眾大腦活動(dòng)需求的錯(cuò)位。接受者在接受一個(gè)歷時(shí)性文本的過程中,其大腦興奮程度是不斷變化的。剛開始的時(shí)候,接受者的興奮需要被喚醒,因此強(qiáng)調(diào)文本開頭要設(shè)置懸念或者其他刺激。隨著情節(jié)的進(jìn)展,接受者的大腦興奮度升高,直至需要一個(gè)情節(jié)高潮使大腦興奮度達(dá)到最高值。待接受者腦力消耗殆盡,大腦興奮度急劇下降,結(jié)局就要在這個(gè)時(shí)候發(fā)生。如果電影開始時(shí)的情節(jié)沒有調(diào)動(dòng)起觀眾大腦的興奮,或者情節(jié)拖沓遲遲不讓情節(jié)高潮在觀眾腦力可維持的時(shí)間內(nèi)來到,又或者觀眾腦力不足時(shí)電影還未結(jié)束,都會(huì)使觀眾的觀影期待與電影的情節(jié)設(shè)計(jì)相錯(cuò),造成觀眾審美接受的疲憊和失望。
電影《白鹿原》開頭即按時(shí)間順序,開列清朝覆滅、民國建立、軍閥混戰(zhàn)的歷史,結(jié)尾又是以日本入侵扣合,這些與電影主要講述的田小娥的故事幾乎沒有關(guān)聯(lián),只有中間的鬧農(nóng)會(huì)、國共合作、國共合作破裂尚還牽扯她的男人和她的故事。從整體來看,宏大的歷史支架游離于中心故事,所以電影敘事顯得松散,不能有效地刺激和迎合觀眾的大腦活動(dòng)。所幸電影的時(shí)長只有兩個(gè)半小時(shí),中間田小娥的故事也有吸引人的噱頭,這種松散的敘事倒是沒有對(duì)觀眾的接受造成巨大壓力。
三
電影《白鹿原》在選擇鹿兆鵬和白孝文這兩個(gè)角色的失察,讓影片在敘事上有些松散,使文本從小說到電影的第一步走得有些踉蹌。但這第一步的不圓滿還不足以對(duì)改編造成致命傷害,致命性的問題在于電影的立意和表意與原著有著天差地別。當(dāng)然,并不是說謹(jǐn)遵原著就是改編的不二法門,本真人性和客觀真實(shí)才是改編的衡量標(biāo)尺,何況原著在本真人性的刻畫和客觀真實(shí)的表達(dá)上也不一定完美。小說《白鹿原》就存在人物形象扁平化和主題先行的缺陷。陳忠實(shí)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都明顯地帶有他的個(gè)人喜惡。那些他喜歡的人物,如朱先生、白靈是完美無缺的、被神化的,白嘉軒也是一個(gè)典型的符號(hào)化人物,這些人物設(shè)置都偏離了本真人性和客觀真實(shí)。他不怎么喜歡鹿子霖,則讓他小善小惡皆備,反而比較符合本真人性。關(guān)鍵人物形象的扁平則很大程度上要?dú)w咎于陳忠實(shí)所要極力完成的“去革命化”和“再傳統(tǒng)化”的主題,這就是主題先行的后果之一。原著的缺陷是完全應(yīng)該在改編中得到修正的,而這首先要求電影創(chuàng)作者經(jīng)歷一個(gè)吃透原著的過程。因此,電影改編基本成功的層次有二:一是電影創(chuàng)作者在吃透原著后認(rèn)為自己的素養(yǎng)層次不及原著作者而謹(jǐn)遵原著;二是電影創(chuàng)作者在吃透原著后認(rèn)為自己有更高明的修正方法而在電影中有所改進(jìn)。但電影《白鹿原》創(chuàng)作者似乎根本沒有領(lǐng)會(huì)小說渾厚的文化內(nèi)蘊(yùn)。

圖3.《白鹿原》
小說《白鹿原》以白鹿原上白、鹿兩家的恩怨斗爭(zhēng)為主線,串聯(lián)起了從封建社會(huì)崩塌到新社會(huì)建立這段波譎云詭的歷史時(shí)空,糅雜了陳忠實(shí)對(duì)歷史前進(jìn)勢(shì)不可擋的哀嘆和欣喜之情。白鹿原是一塊封建文化氣息濃厚的土地,一直以來,以白嘉軒為族長的封建宗族制度維持著原上的道德秩序。陳忠實(shí)對(duì)白嘉軒這個(gè)封建文化的代理人褒多貶少。白嘉軒在精神上深信封建道德,在行動(dòng)上謹(jǐn)遵鄉(xiāng)約,除了暗用手段跟鹿家換取了安置祖墳的一塊風(fēng)水寶地外,從來沒有做過虧心事。因此,他頭一挨著枕頭就能睡著,面對(duì)田小娥兇惡的鬼魂毫不畏懼毫不妥協(xié),身遭土匪的報(bào)復(fù)也大義凜然不現(xiàn)懼色。他寄予厚望的長子白孝文和他最鐘愛的女兒白靈都因背叛了他所恪守的封建文化而被逐出門外。他仁義、沉穩(wěn)、堅(jiān)定,帶著古老的睿智鑒證著封建道德懲惡揚(yáng)善的巨大力量,并有點(diǎn)自鳴得意。白嘉軒是封建秩序的維護(hù)者、審判者和執(zhí)行者,他的文化靠山是關(guān)中大儒朱先生。每有難辦的事情他便問計(jì)于朱先生,總能得到有效指點(diǎn)。朱先生在小說中幾乎被神化,游走于民間和各種政治力量之間,所到之處無人不對(duì)其禮敬有加、崇拜備至,甚至他對(duì)死亡和自己死亡后的中國政局都有準(zhǔn)確的預(yù)測(cè)。
朱先生所代表的就是封建文化的魂魄,他的死代表了封建文化的衰亡。陳忠實(shí)對(duì)他即將離開人世時(shí)的描寫充滿了傷感,對(duì)他的一生極盡贊揚(yáng),這也代表了他本人對(duì)作為封建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的認(rèn)同和熱愛。曾經(jīng)的叛逆者——黑娃和白孝文在經(jīng)歷了世事滄桑以后,發(fā)現(xiàn)沖破封建枷鎖獲得自由后的無所適從更加可怕。就像弗洛姆所說,個(gè)人一旦把確保安全的原始紐帶切斷變得孤苦伶仃,就不得不想方設(shè)法擺脫這種軟弱和孤獨(dú)的狀態(tài)。他們骨子里是封建文化中的人,除了封建文化,沒有什么能給他們踏實(shí)的精神依靠,他們最終轉(zhuǎn)身皈依封建文化。白孝文是投機(jī)的皈依者,自私和圓滑的本質(zhì)注定了他總是向利益靠攏。黑娃是虔誠的皈依者,被朱先生視為“最好的學(xué)生”,他的蛻變成功顯示了儒家文化的巨大魅力和對(duì)男性回歸者的包容。田小娥被情欲支配所行的盲目背叛則遭到了封建文化堅(jiān)決的鄙棄。封建堡壘里沒有一個(gè)人站出來引導(dǎo)她回歸,新興力量也沒有對(duì)這樣一個(gè)有些愚昧的舊式女人加以援助。她就在封建文化的排擠和新興力量的無視中走向了必然的悲慘結(jié)局——灰飛煙滅,永世不得翻身。這其實(shí)是一個(gè)很值得可憐的人物,美麗卻有些“是非不分”,想過安生日子卻總是被損害,“失足”后想回頭卻無岸,那些愛過她的男人們最終都否定了她。封建文化對(duì)女性如此苛刻,可惜陳忠實(shí)似乎并沒有給予她足夠的同情,因?yàn)樵谶@個(gè)問題上他站在了封建文化的立場(chǎng)。
陳忠實(shí)對(duì)儒家文化滿懷深情卻也對(duì)新生力量充滿欣喜。小說中只有兩個(gè)人物是“白鹿精靈”的化身,一個(gè)是朱先生,另一個(gè)就是共產(chǎn)黨員白靈。白靈出生在白鹿原上“腰桿最硬”的封建族長家里,卻最徹底地背叛了這個(gè)家庭所信奉的文化。和田小娥、黑娃、白孝文的背叛不一樣,她在沖破封建牢籠以后找到了新的精神皈依——共產(chǎn)主義。她安全順利地完成了這個(gè)過渡,既沒有像黑娃和白孝文那樣“吃回頭草”,也沒有像田小娥那樣被封建文化“處死”。她注定不會(huì)死于封建文化,也不會(huì)屈服于任何損害她的力量。陳忠實(shí)沒有讓白靈與封建文化正面交鋒,而是讓她經(jīng)歷了文化的交替。鹿兆鵬雖然是最有建樹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者,但他不是“白鹿精靈的化身”,不如白靈受陳忠實(shí)偏愛。陳忠實(shí)派他對(duì)封建祠堂進(jìn)行了無情的摧毀,完成了敘事的歷史真實(shí)。真正的革命是文化的嬗變。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和白靈代表的新文化都是作者所青睞的,他既對(duì)逝去的儒家文化留戀不舍,也對(duì)蓬勃興起的新文化由衷喜愛,他在內(nèi)心不希望二者交戰(zhàn)。兩個(gè)白鹿精靈的化身透露了他的情感傾向,也啟發(fā)讀者重新審視兩種文化的內(nèi)涵和價(jià)值。這對(duì)現(xiàn)代中國人重新認(rèn)識(shí)兩種文化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圖4.《白鹿原》
如果電影《白鹿原》剪掉了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封建文化就失掉了神韻,剩下的多是僵硬冷酷的部分。如果剪掉了白靈,令人振奮的新時(shí)代新文化,特別是女性解放的曙光也就沒有到場(chǎng),只留一個(gè)田小娥胡亂掙扎、至死不休。電影成了白嘉軒與田小娥的斗法場(chǎng),田小娥“毒染”了封建文化中的兩個(gè)優(yōu)秀青年黑娃和白孝文,白嘉軒像法海一樣代表封建文化鎮(zhèn)壓了田小娥這個(gè)“禍害”。但白孝文為了田小娥和他的娃能活下去“賣了自己”,黑娃為了給田小娥報(bào)仇親手打斷了白嘉軒的腰桿,也和父親鹿三斷絕了關(guān)系。白孝文和黑娃沒有“悔改”,反而因?yàn)榧糨嫷酱硕o人感覺他們?cè)凇皭邸钡牡缆飞侠^續(xù)走著。我們?cè)陔娪爸锌吹搅耍饨ㄎ幕瘜?duì)男女大欲的剿滅不近人情,但青年斗爭(zhēng)不屈。田小娥的悲劇就幾乎全要怪罪封建文化了。這種簡單幼稚的情節(jié)和立意曾被無數(shù)劣質(zhì)的影視劇所用,顯示了導(dǎo)演把封建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的錯(cuò)誤認(rèn)知,更泄露了導(dǎo)演文化素養(yǎng)的淺薄。實(shí)際上,田小娥、白孝文、黑娃三人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的新文化教育,他們腦子里“祖宗”“祠堂”等烙印根深蒂固,他們幾乎不可能完成以“新”代“舊”的變革。執(zhí)行和實(shí)現(xiàn)這種變革的是共產(chǎn)黨革命者白靈和鹿兆鵬,而他們被弱化到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
其實(shí),封建文化并非否定男女大欲。小說中孝義媳婦向兔娃“借種”,“棒槌神會(huì)”公開允許已婚婦女和其他男人交媾,這些在現(xiàn)代看來都不可思議的性行為在封建社會(huì)生殖崇拜、傳宗接代的文化環(huán)境中都被合理化了。封建文化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傳宗接代”的原則下才成立,田小娥是因?yàn)楸畴x了這一原則才萬劫不復(fù)。另外,封建婚姻也不是不幸的代名詞。小說中朱先生的婚姻以及黑娃的第二次婚姻都是幸福成功的。朱先生擇偶,“他已經(jīng)看過四五個(gè)媒人介紹下的七八個(gè)女子,都不是因?yàn)殚T第不對(duì)或相貌丑陋,在于朱先生一瞅之后發(fā)覺,有的眼睛大而無神,有的媚氣太重,有的流俗”,他最后瞅中了白家大姑娘“剛?cè)嵯酀?jì)”的眼睛,從那雙眼睛里他看到“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這個(gè)女人完全能夠持節(jié)守志,撐立門戶,撫養(yǎng)兒女”。黑娃找了一個(gè)知書達(dá)理能夠“管管”他的女人,漂亮地完成了他回歸封建文化的轉(zhuǎn)身。這兩樁封建文化中的婚姻以理性為基礎(chǔ),向讀者展示了理性的婚姻對(duì)人生圓滿的建設(shè)性作用。與理性婚姻相反的則是田小娥和黑娃感性的婚姻,這種婚姻以一見鐘情式的激情為基礎(chǔ),與作者想以婚姻傳達(dá)的理念是相通的。
叔本華對(duì)這兩種婚姻有過精辟的分析。他認(rèn)為,一見鐘情的婚姻體現(xiàn)了造物主的意志,令戀愛雙方以無可抗拒的巨大激情生育自然界最優(yōu)質(zhì)的后代,之后造物主就不管二人是否幸福了,兩人開始發(fā)現(xiàn)對(duì)方的缺點(diǎn),并為當(dāng)初的沖動(dòng)而后悔;理性的婚姻雖然沒有那么大的激情,但雙方各方面比較匹配,容易走得長遠(yuǎn)。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初的目的是建立理性的婚姻,維護(hù)家庭的和諧、社會(huì)的安定。然而封建文化代代相傳的方式是教條的,沒有原因和論證,因此現(xiàn)代人覺得很多東西不可理喻。在小說中,朱先生的婚姻和黑娃的第二回婚姻都是對(duì)封建婚姻制度合理性一面的佐證。電影中沒有孝義媳婦和兔娃,也沒有“棒槌神會(huì)”,沒有朱先生的擇偶,也沒有黑娃的重新選妻,而田小娥的悲劇歪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本質(zhì)。
在小說中,陳忠實(shí)對(duì)舊文化和新文化都采取肯定的態(tài)度。相應(yīng)的文化對(duì)應(yīng)相應(yīng)的社會(huì)形態(tài),封建文化適用于封建社會(huì),新文化匹配于“新”社會(huì)。從封建社會(huì)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必然要經(jīng)歷一個(gè)文化的變革。對(duì)于“新”社會(huì)來說,封建文化不適用了但未必不好。對(duì)于那些被封建文化浸淫的人們,堅(jiān)守他們心中的信念也是一種應(yīng)當(dāng)被尊重的生活方式。陳忠實(shí)的寬容和厚度正體現(xiàn)在他對(duì)兩種文化的態(tài)度上。電影卻恰恰相反,既不看好封建文化又對(duì)新文化冷眼相看。電影剪掉了封建文化和新文化的“精靈”,也砍掉了能立體呈現(xiàn)封建文化的枝椏。電影由白嘉軒、田小娥、黑娃、白孝文所構(gòu)成的是一個(gè)嚴(yán)重失實(shí)的封建生活群落,其所建立起來的封建文化單薄、畸形,讓現(xiàn)代人不僅無法正確理解作者想傳達(dá)的意味,還隔閡更深,誤解更重。電影對(duì)新文化的冷漠則主要體現(xiàn)在對(duì)鹿兆鵬這個(gè)人物的塑造上。小說中的鹿兆鵬外形俊美、勇敢、機(jī)智,矢志不渝地忠于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是一個(gè)近乎完美的正面形象。電影中的鹿兆鵬除外形不達(dá)標(biāo)之外,還以喜劇形式出場(chǎng),以逃跑的方式作為最后一次亮相。鹿兆鵬逃跑后再?zèng)]出現(xiàn)就暗示了他及其所背負(fù)的事業(yè)都前途渺茫,他所代表的文化也黯淡下去。而歷史早已確定無疑地夯實(shí)了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和新文化在中國社會(huì)變革過程中的正確性和光明性。對(duì)整個(gè)新舊文化的扭曲,從小的方面來說是一部電影的失敗;從大的方面來說是對(duì)中國文化、社會(huì)、歷史和觀眾的犯罪。

圖5.《白鹿原》
四
當(dāng)然,將一部五十萬字的小說改編成兩個(gè)半小時(shí)的電影確實(shí)難以做到面面俱到,但是,改編本來也并不要求面面俱到,而是要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突出原著中最能震撼人心的東西,并對(duì)其震撼力進(jìn)行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而向來以“文藝性”著稱的中國“第六代”導(dǎo)演中的優(yōu)秀代表王全安,因?yàn)闆]能正確理解小說、認(rèn)知文化,卻硬生生將一部富有文化韻味的小說改編成了靠情色噱頭吸引人的俗片。這是他向商業(yè)屈膝投誠的表現(xiàn),還是他本身文化素養(yǎng)的露怯?不得而知。
針對(duì)以上的分析,本文試圖對(duì)《白鹿原》的改編做一些修正,以使電影在現(xiàn)有的容量范圍內(nèi)能更接近本真人性和客觀真實(shí)。首先,鹿兆鵬和白孝文的扮演者應(yīng)該根據(jù)原著的描述重新選擇。鹿兆鵬的扮演者應(yīng)該兼具富家子弟和共產(chǎn)主義革命者形象的雙重氣質(zhì)。白孝文的扮演者應(yīng)該少一些滄桑和木訥,多一些文雅之氣。其次,電影中人物所承擔(dān)的情節(jié)任務(wù)應(yīng)該有所調(diào)整。朱先生若不出現(xiàn),白嘉軒身上不僅可以強(qiáng)化朱先生儒家文化智慧的一面,也可以獲得其理性婚姻的幸福,作為和田小娥命運(yùn)的對(duì)比。孝義媳婦“借種”懷孕的情節(jié)可以嫁接到孝文媳婦身上。白靈若不出現(xiàn),她的一些革命活動(dòng)應(yīng)該和鹿兆鵬的合二為一,加強(qiáng)對(duì)鹿兆鵬這一形象的塑造力度。黑娃即使后來不出現(xiàn),也比親自出來打斷白嘉軒的腰、逼死父親要合理。再次,電影中的情節(jié)重點(diǎn)需要做些變動(dòng)。電影前面沒有必要鋪墊那么多黑娃和孝文小時(shí)候的情誼,因?yàn)殡娪昂竺娌]有出現(xiàn)他們二人為了田小娥反目成仇等復(fù)雜情節(jié),省出的時(shí)間不妨將孝文多年后回歸封建文化的過程加以詳述。
這樣的改動(dòng)或許會(huì)稍微扭轉(zhuǎn)一下電影對(duì)小說原意的曲解和濫造,但是電影已經(jīng)公映,無法挽回了。虛假的人性和歷史已經(jīng)用藝術(shù)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傳達(dá)給了觀眾,那些扭曲的文化觀念已經(jīng)植入千千萬萬觀眾的心中。如果名著改編僅僅是讓電影能借著名著的名氣而大賺一筆,如果名著改編不能讓觀眾領(lǐng)略到影像的震撼和啟迪,如果名著改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欺詐行為,如果名著改編損害了觀眾的精神健康,如果名著改編污損了中華文化,這樣的名著改編還有何顏面屹立于中華大地上?這樣的創(chuàng)作者還有什么民族責(zé)任感和職業(yè)良心可言?這樣的改編不止《白鹿原》一部,讓人大跌眼鏡的導(dǎo)演也不止王全安一人。中國電影的改編不應(yīng)靠學(xué)者“馬后炮”的修正,而應(yīng)加強(qiáng)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文化素養(yǎng)。電影創(chuàng)作者應(yīng)在讀懂讀透原著的基礎(chǔ)上,有自己獨(dú)立的思考,以本真人性和客觀真實(shí)為美學(xué)參照體系打造真善美的電影。
【注釋】
①吳輝、別君紅.得,遠(yuǎn)大于失——也談小說《白鹿原》的電影改編[J].當(dāng)代電影,2013(9).
②周仲紅.西部鄉(xiāng)土史詩與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現(xiàn)——論電影《白鹿原》的改編藝術(shù)[J].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3(1).
③謝剛、李碩嘉.騎墻敘事、語境錯(cuò)位與隱喻功能耗散——電影《白鹿原》改編之失一解[J].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6).
④潘樺、鞏杰.詩性智慧與詩性品格的缺失——以小說為參照分析電影《白鹿原》[J].現(xiàn)代傳播,2013(6).
⑤孫宜君、高涵.從《白鹿原》改編看電影與文學(xué)的非良性互動(dòng)[J].揚(yáng)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1).
⑥李楊.《白鹿原》故事——從小說到電影[J].文學(xué)評(píng)論,2013(2).
⑦馬立新.論低碳藝術(shù)的本體特征及其建構(gòu)機(jī)制[J].現(xiàn)代傳播,2014(4).
⑧[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M].邵牧君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16.
⑨陳忠實(shí).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467.
⑩陳忠實(shí).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