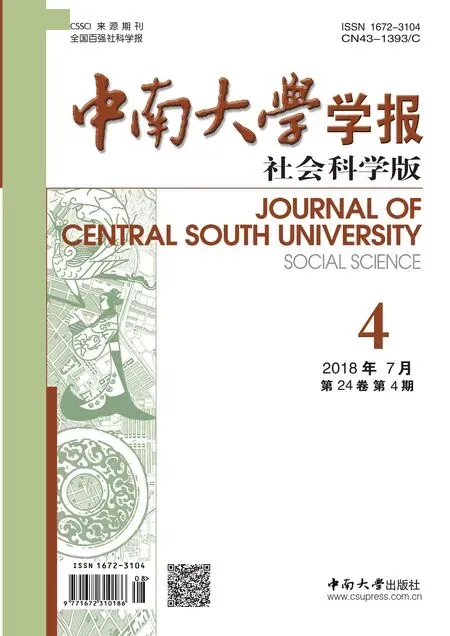文本與圖像:歷代赤壁圖的對話關系與多重意蘊
陳琳琳
?
文本與圖像:歷代赤壁圖的對話關系與多重意蘊
陳琳琳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100871)
作為最受中國古代畫家青睞的詩意圖題材之一,取材于蘇軾赤壁文學的赤壁圖為探討古代詩畫關系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一直以來頗受藝術史研究者關注,然而其文學價值與文化意義卻鮮有論及。歷代赤壁圖的創作者通過場景選擇與藝術轉換,精心構筑了新的視覺闡釋空間,延展了蘇軾赤壁文學的思想意蘊。在圖像內部,畫家通過再現蘇軾與客、蘇軾與赤壁、蘇軾與孤鶴的三重對話關系,完成了對文本的闡釋與再創造。在圖像外圍,文字題詠與赤壁圖之間具有相互映襯、相互補充的緊密關系。以赤壁圖為物質載體,題畫者、畫家與蘇軾之間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對這一層對話關系的解讀剖析,有助于重新審視蘇軾及其文學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赤壁圖;蘇軾;赤壁文學;對話;意蘊
作為詩畫結合的綜合藝術品,詩意圖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與繪畫的互動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然而,一直以來,詩意圖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藝術史視閾,尚未引起古代文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蘇軾關于黃州赤壁的二賦一詞自問世以來,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畫家的創作熱情,成為中國古代繪畫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詩意圖題材之一。圍繞蘇軾赤壁文學的繪畫創作實踐,涌現了一批藝術成就高超的赤壁圖,折射出不同時代、階層、流派、地域的畫家對蘇軾文學作品的不同理解與藝術詮釋。這既為爬梳詩意圖的發展流變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又為探索古代詩畫關系打開了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目前,有關赤壁圖的研究成果多立足于藝術史角度,由圖文關系切入,探討赤壁圖的文學價值與文化意義的成果較為稀見①。筆者嘗試從文學研究的視角出發,考察蘇軾赤壁文學對畫家藝術想像的啟迪與制約,探討歷代赤壁圖的闡釋空間與限度,并通過對赤壁圖及其題跋的綜合分析,重新審視后世藝術家與蘇軾之間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以期獲得對蘇軾及其赤壁文學的后世接受更為全面的觀照。
一般認為,傳世赤壁圖有兩種主要的表現形式:一種是敘事性長卷,多以《后赤壁賦》(簡稱《后賦》)為再現對象;一種是抒情性單景,多以舟游赤壁、江流臨眺等單一的文學情境為主題。前者采用跳躍的連環畫體制復現蘇軾原作的敘事情節,后者截取蘇軾二賦一詞的經典情境加以創造性的剪裁融合。通過不同的場景選擇與藝術轉換,歷代畫家不僅完成了對蘇軾文學作品的視覺再現,而且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闡釋空間。這一闡釋空間跨越了文學與繪畫的藝術界限,賦予蘇軾赤壁文學新的內涵。在這一闡釋空間之內存在著多重的對話關系,這些對話關系的建構,既關涉文學作品的視覺轉換,又揭示了蘇軾赤壁文學的多重意蘊。作為詩畫融合的藝術品,赤壁圖自身容納了繪畫與文學這兩種藝術門類之間的對話;而赤壁圖的直接題材來源,即以前后《赤壁賦》與《念奴嬌·赤壁懷古》為代表的赤壁文學,涵蓋了蘇軾與自我、歷史、自然乃至宇宙等多個維度的對話關系。因此,如何再現與詮釋赤壁文學所蘊含的多維對話,展現蘇軾原作復雜的多重意涵,成為歷代赤壁圖詩、畫藝術轉換的關鍵問題。在圖像與文本之間,我們可以看到蘇軾與客、蘇軾與赤壁、蘇軾與孤鶴,以及題畫者、畫家與蘇軾之間的多重對話關系。對這一系列復雜的對話關系的梳理與剖析,有助于我們討論赤壁圖在視覺轉換中的優劣得失,觀察歷代畫家群體對蘇軾原作深層意蘊的接納、闡釋與改造,探究后世畫家與蘇軾之間跨越時空的精神交流,進而重新體認蘇軾赤壁文學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蘇軾與客的人物對話
在歷代赤壁圖中,人物對話是最基礎的一層對話關系,以蘇軾與客的舟上對答為核心。在馬和之《后赤壁賦圖》②、李嵩《赤壁圖》③等早期赤壁圖中,舟上對答即已成為畫面的絕對重心。畫家通過對蘇軾與客的神情姿態的細致描摹,展現對話的歡暢愉快,且以童子、船夫等陪襯人物還原文本的對話情境,借舟上的杯盞狼藉暗示對話的歷時之久。明代畫家仇英所作的多幅赤壁圖,聚焦人物對話場景,對蘇軾與客在舟上對話的文學情境予以生動反映。仇英早年所作《后赤壁圖》④描摹蘇軾與客同坐舟中,相談甚歡,似未察覺掠飛天際的孤鶴;二客若有所思,似從蘇軾的一番人生論說中獲得思想共鳴。仇英另一幅《赤壁圖》(圖1)更為典型,仇英一反慣有的工麗謹嚴畫風,以優雅從容的筆調描繪蘇軾與客啜茗閑敘的場景。畫面沿襲文派赤壁圖的布景構圖,霜林層染、松蘿映帶與巉巖巨壁皆透露出明顯的裝飾意味;然而,仇英的創作焦點仍落于舟上人物的對話交流。區別于前一幅作品直摹對話場景的表現方式,此畫意在傳達蘇軾與客的情感交流:一客吹奏排簫,蘇軾側耳聆聽,如癡如醉、悠閑適意的神態生發出諸多聯想。仇英將平和的人生態度與簡淡的藝術追求投射于赤壁圖的創作之中,扭轉了蘇軾《后赤壁賦》孤高冷峭的敘事風格。就人物對話的刻畫而言,仇英忠實于文本的既有情境,以深細微妙的筆觸勾畫人物的具體面目情態,展現主客之間親密友好的精神交流。

圖1 (明)仇英《赤壁圖》⑤
就文學作品的解讀與接受而言,以人物對話為赤壁圖的表現中心,呼應了前后《赤壁賦》的文體特征與文學主題。主客對答是賦的創作手法,蘇軾《赤壁賦》(簡稱《前賦》)的主客對答,不僅是對賦的寫作傳統的繼承,而且與其說理議論的創作主旨密切相關。正是在來回往復的對話交鋒中,蘇軾對宇宙人生的思索歷程獲得淋漓盡致的展示。主客對話不僅是貫穿赤壁之游的中心情節,也是《前賦》文學主旨得以闡發的關鍵。如果說對“泛舟中流”的截取是畫家對文本發生情境的回應,那么對主客問答的視覺化還原,則或多或少反映了畫家對《前賦》中蘇軾與客辯論過程的關注。受制于繪畫的平面形式,“對話”這種歷時性的動態進程往往超出其表現范疇,蘇軾游歷黃州赤壁波折反復的思維過程,更難以形諸于畫。畫家只能通過設置開放的對話場景,構筑新的想像空間,將蘇軾與客關于人生、歷史與宇宙等命題的探討付諸觀者的想像。這種對話場景的重塑既包括蘇軾與客的動作神情(如對答時的姿態與眼神交流),又包括童子、船夫的表情反應,以及煮茶、品酒等文化活動的側面襯托。無論畫家是否有意識地嘗試運用對話場景為畫面注入潛在的動感,克服繪畫只適宜表現靜態的藝術缺陷,從畫面呈現的藝術效果來看,大部分優秀的赤壁圖都能令觀者由表面靜止的對話場景聯系到《前賦》內在流動的韻律,從而有效地觸發對蘇軾人生思索過程的聯想。觀者從蘇軾放松或警惕的姿勢,從客人猶疑或篤定的神態,甚至從船夫、童子羨慕或不耐煩的表情中,獲取對黃州赤壁之游更鮮活的視覺印象。與此同時,經由看似靜止的對話畫面,觀者可進一步感知蘇軾與客論辯的激烈、友誼的親密,以及在赤壁的自然風月面前的沉醉著迷。應該說,赤壁圖所表現的人物對話,并非普通的把酒閑談,而是一種嚴肅的哲思論辯,是蘇軾與客的精神交流與碰撞,它既關乎蘇軾原作精神主旨的傳達,又觸及文本潛在的情感張力。優秀的赤壁圖不僅能夠通過人物對話復原文本的發生情境,而且能夠有力地回應蘇軾在《前賦》中的感悟沉思,引導觀者探知蘇軾赤壁之游的心路歷程。
二、蘇軾與赤壁的時空對話
在蘇軾關于黃州赤壁的文學書寫中,赤壁不僅是純粹的自然景觀,而且承載著雙重的時空意義。在時間向度上,屹立千年的赤壁,象征著綿邈不絕的歷史,而人的生命歷程只有短暫的一瞬;在空間向度上,巍峨雄壯的赤壁,代表著廣袤無邊的自然,而人類渺小得就如同一粒塵土。蘇軾與赤壁的“對話”貫穿于前后《赤壁賦》之中,并成為歷代赤壁圖最重要的表現對象。事實上,黃州赤壁并非三國時期赤壁之戰的真實發生地,蘇軾在其詩文中也明確表達了這種質疑。如《與范子豐書》寫道:“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1](1452?1453)就文學創作而言,黃州赤壁究竟是否為赤壁之戰的真實發生地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黃州赤壁觸發了蘇軾的懷古情愫,見證了蘇軾對過往歷史的紀念與憑吊。
貶謫黃州時期,蘇軾多次游歷赤壁,寫下了諸多與黃州赤壁相關的文學作品,除了被赤壁壯麗的自然風光深深吸引之外,作為遺跡的赤壁所寄托的歷史悲歡也是重要的創作動因。蘇軾登臨赤壁之巔、注目滾滾長江,借“客”之口表達對曹操的傾慕,并著意構想了周瑜的“故國神游”,達成與曹操、周瑜等歷史人物之間的隔空對話,借由對古人豐功偉業的謳歌,反觀自身的年華虛度。與此同時,無論是《前賦》中“橫槊賦詩”的曹操,還是《念奴嬌》中“雄姿英發”的周瑜,都被染上了濃烈的傳奇色彩。“一世之雄”“千古風流人物”如今安在?功業的絢麗輝煌隨著時間的飛逝而“灰飛煙滅”。功名的幻滅與赤壁的永恒之間構成巨大的反差,促使蘇軾進一步思索歷史與當下的關系:人類轉瞬即逝的功名輝煌,究竟應該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安放?
借由登臨憑吊的行為,蘇軾實現了與赤壁的精神對話,當他凝視赤壁古戰場之時,不禁聯想起曹操、周瑜等“風流人物”,進而引發對歷史、人世、自然等多重命題的重新思考。然而,這種貫穿古今的歷史對話,若要轉換為視覺圖像無疑非常棘手。繪畫是一種靜止的空間藝術,只能表現特定時空之中的特定場景,如果在同一平面內疊加蘇軾、曹操或周瑜等不同歷史時空中的人物,不但會破壞中國繪畫的“神韻”,更容易給觀者帶來重重困惑。在歷代赤壁圖中,這種跨越古今的對話關系只能憑借特定的詩意化姿態予以暗示。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姿態有兩種:一種是蘇軾對赤壁的遠眺仰視,由仰望的姿態向觀者傳遞蘇軾對赤壁的敬仰,對曾經發生的赤壁之戰的緬懷,以及對遠逝的英雄事跡的追慕與感慨;另一種是蘇軾對長江的觀覽俯瞰,這種姿態有意放大了文本的懷古情懷,凝望滔滔江水的蘇軾,仿佛重新激活了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一古老的時間命題。經由蘇軾形象的引導,觀者可以進入歷史的隧道,回到遙遠的赤壁古戰場,再度瞻仰偉大的英雄人物。當然,一旦由想像回到畫卷本身,歷史不再,壯志滿懷的蘇軾已華發早生,人生的幻滅感由此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畫家所作的赤壁圖中,我們可以發現畫家對蘇軾原作懷古因素的直接強調。據日本學者板倉圣哲《日本繪畫中的赤壁形象》[2]一文的記錄,江戶時期南畫家彭城百川的《前赤壁賦圖》,以“泛舟中流”為表現中心,蘇軾所乘小舟軍旗飄揚,天空中掠過三只飛翔的黑鳥。軍旗是對“軸轤千里,旌旗蔽空”戰爭場面的呼應,黑鳥則回應了“烏鵲南飛”的文本意象。另一位日本畫家谷文晁的《赤壁圖》雙幅,不僅出現了軍旗意象,連木舟也變成了戰船,蘇軾形象被置換為不可一世的曹操。這兩幅作品均疊加了蘇軾與曹操的人生經歷,強化了黃州赤壁之游與赤壁之戰的歷史關聯。當然,從畫作整體看來,軍旗、戰船與赤壁的風月美景顯得略不協調,質實的物象破壞了蘇軾夜游赤壁縹緲綽約的浪漫意境,與追求山水韻致的中國赤壁圖截然不同。不妨對比一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畫家王翚《仿唐寅赤壁圖》⑥,畫面雖題寫“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烏鴉形象卻被畫家排除在外,文人趣味才是畫作的底色。
日本畫家采取的直接圖現的方式,一度出現在中國早期的詩意圖作品中。曹植《洛神賦》描寫洛神的絕世容顏“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驚鴻、游龍、秋菊、春松皆是虛構的比喻意象,卻被顧愷之直接圖入《洛神賦圖》之中(由宋摹本所見)。不過,這種虛實不分的表現手法在詩意圖的創作實踐中逐漸被拋棄(僅在木刻版畫系統中得到保留)。日本畫家所繪赤壁圖采用這一樸拙的再現方式,盡可能地保留所有的文本意象,也暴露了對異域文本的理解缺陷。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兩幅赤壁圖印證了畫家對《赤壁賦》歷史想像與懷古意緒的關注,象征性的視覺符號明確提示了蘇軾與歷史人物的對話關系,如板倉圣哲所言:“在這些作品當中,隱含了將遭遇左遷命運的蘇軾,與后來大敗的曹操作一比較的意味。”[2](272)在同一平面內,不同時空的人物形象或歷史情境的疊現,制造出古今如一的幻覺效果,旨在啟發觀者,作為歷史延續的當下終將成為新的歷史,有力地回應蘇軾“人生如夢”的深沉慨嘆。
在蘇軾的兩賦一詞中,黃州赤壁是巍峨的大自然的象征。在廣袤的自然面前,人類如同一葉扁舟黯然失色。在空間維度上,赤壁的雄偉與人類的渺小形成強烈的對比,蘇軾由此感受到自然的震懾力,以及面對自然的無力感,隨即刺激了政治失意的無奈情緒,世事滄桑、人生須臾的感受噴涌而出。如果說在表現歷時性的精神對話上,赤壁圖不可避免地暴露了繪畫作為空間藝術的本質局限,那么在詮釋文本的空間意蘊之時,赤壁圖則彰顯出強大的視覺力量。事實上,蘇軾原作蘊含著豐富的繪畫質素,諸多生動精彩的山水意象為畫家提供了直接的視覺素材。險峻的赤壁,浩蕩的江水,加之清風木葉,天光白露,皆是中國古代山水畫的典型要素。一方面,傳統山水畫的主題、風格對赤壁圖的創作具有重要的影響,諸如水圖、舟行等山水題材為赤壁圖畫家提供了直接的藝術借鑒;另一方面,歷代赤壁圖的創作者盡力發掘蘇軾原作潛在的視覺因素,在繼承繪畫傳統的同時,也利用個性化的視覺處理,強化烘染文學主題。因此,對赤壁形象的關注,既是對山水繪畫題材的自然回應,又是對蘇軾原作時空意蘊的創造性表現。在赤壁圖中,畫家極盡能巧地刻畫黃州赤壁的陡峭險峻,通過壓倒性的視覺對比,凸顯赤壁的宏偉與孤舟的渺小,暗示蘇軾對自然的敬畏之感,呼應“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人生慨嘆。舊題南宋畫家楊士賢的《赤壁圖》(圖2)是表現這一空間對話關系的佳作。橫貫江面的赤壁是畫面的絕對中心,畫家極力烘染赤壁巍峨雄壯的氣勢,相比之下,湍急的江流之中,一葉扁舟載蘇軾與客數人,顯得尤為渺小。經由宏偉的自然與渺小的人類之間的懸殊對比,蘇軾原作的思想主旨獲得精彩的視覺闡釋。這種夸張的對比式構圖逐漸成為赤壁圖的經典范式。例如,明人程嘉燧創作多幅赤壁圖,在其畫作中,赤壁被高度意象化,畫家以極簡的構圖與線條畫垂直聳立的赤壁,突出赤壁與扁舟之間的鮮明反差。這種高度凝練的寫意方式,是對蘇軾與赤壁的空間對話的視覺提煉。

圖2 (舊傳)南宋楊士賢《赤壁圖》⑦
不過,文學作品書寫的蘇軾與赤壁之間的“對話”,畢竟是一種想像性的精神交流。作家并非以“靜物攝影”的方式攝取自然山水,而是將自身情感投注其間,蘇軾赤壁文學中的自然描寫即帶有濃重的抒情色彩。畫家圖寫赤壁之游,即是在揣測、想像蘇軾眼中的赤壁。在這個過程中,畫家的主體意識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自明代中葉始,文徵明等吳門畫家筆下的赤壁圖,逐漸消解了黃州赤壁陡峭巍峨的固定形象,引入了現實生活中溫婉的江南山水,圖像詮釋的重心也隨之由文本嚴肅的人生命題,轉移至游山玩水的閑情逸趣之上。畫家創作意圖的改變,使得蘇軾與赤壁之間的對話關系被大大削弱。在某種意義上,借由蘇軾赤壁之游的視覺化還原,吳門畫家意欲呈現的并非蘇軾的自然觀,而是畫家自身與自然山水之間的情感對話,是畫家自我對自然宇宙的感悟與思索。
三、蘇軾與孤鶴的“神交”
蘇軾赤壁文學之所以備受畫家青睞,除了豐富的山水意象和觸人心弦的人生哲思之外,神奇迷幻的文學意境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蘇軾的筆下,《前賦》的自然山川被抹上了一層迷幻的色彩,《后賦》更以道士化鶴的離奇情節,刻意制造“陌生化”的閱讀效果,令觀者頓生恍惚之意。“返而登舟”之后,蘇軾的畏懼情緒漸漸緩和,但孤鶴的掠過又打破了“放乎中流”的寧靜;緊接著,蘇軾在夢中與道士晤對,前夜“戛然長鳴”的孤鶴竟是道士所化;道士以“赤壁之游樂乎?”挑動蘇軾心弦,觸發蘇軾的曠達今古之思。突兀的自然意象與波折的敘事情節,形成閱讀上的斷裂感,使《后賦》始終籠罩于幽峭神秘的氣氛之下,文本深邃的哲理意味即是在這種氛圍中透顯出來。
在《前賦》中,蘇軾與客保持著密切的互動交流;而在《后賦》中,除了開篇尋找佳肴美酒略有問答,隨著敘事情節的展開,客人卻始終沉默,與蘇軾之間鮮有對答。這一精心的安排旨在烘染蘇軾孤獨悲涼的心境,并為孤鶴的出場制造必要的聲勢。月夜中突然掠過的孤鶴是《后賦》最具奇幻色彩的意象,它的孤獨與清高,映照著同處寂寥的貶謫境遇的蘇軾。不甘寂寞的孤鶴,尋覓志同道合的伴侶,“掠予舟而西”,表示對蘇軾的友好[3](324)。在蘇軾的筆下,“鶴”的形象被高度人格化:一方面,落寞孤獨的蘇軾與客同游卻不能交心,反將孤鶴援為精神知音;另一方面,蘇軾與孤鶴之“神交”,暗示著即將出現的夢境,既制造了敘事緊張點,又強化了文本內在的情感張力。在《后賦》結尾,孤鶴、道士與蘇軾仿佛混為一體,物我皆夢的虛幻感自此生發。因此,孤鶴橫江、夢會道士是《后賦》最重要的情節之一,關乎《后賦》思想主旨的最終揭示。
在歷代赤壁圖中,孤鶴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構圖元素,甚至有研究者認為,孤鶴逐漸成為區分前后赤壁圖的唯一標志[4](23)。這種說法并不是很準確,尤其是明代之后的赤壁圖,文本依據越來越模糊,畫家往往只是給出赤壁之游的一種綜合印象。在筆者看來,孤鶴意象的出現,最重要的意義不在于鑒別圖像的文本來源,而在于創造性地構建了蘇軾與孤鶴的精神對話。當然,這種“對話”是一種象征性的精神互動,由文字轉換為視覺形象,則多體現為蘇軾對孤鶴的聚焦凝望。就圖文轉換而言,這種對話關系的視覺再現,有利于還原《后賦》縹緲奇幻的文學色彩,為再現蘇軾對晤道士的夢境作必要的鋪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后賦》潛藏的深刻意蘊。
早在傳為北宋喬仲常的《后赤壁賦圖》⑧中,蘇軾與鶴的這種對話關系就已經出現。美國學者謝柏軻(Jerome Silbergeld)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泛舟場景中,“只有蘇軾意識到了鶴的存在,可能只有他一個人感知到鶴隱含的情感信息”[4](24)。除了喬仲常之作,明代畫家丁云鵬的扇面《畫后赤壁》⑨亦有類似的藝術匠心。畫家通過剪裁并置不同時空中發生的敘事情節,突破文本的敘事順序:登臨的蘇軾正眺望著橫江東來的孤鶴,仿佛正與其進行一番精神對話。清代畫家錢杜的《后赤壁圖》⑩運用類似的表現方法:站在赤壁之巔的蘇軾并沒有將視線投向滾滾的江水,而是凝望孤鶴飛去的背影若有所思。畫家別具匠心地將“臨江觀眺”與“孤鶴橫江”兩個敘事情節并置于同一畫面,以蘇軾對孤鶴的瞭望情態勾起觀者的種種聯想。孤鶴究竟因何吸引蘇軾?由此,畫家設置了一個懸念,引導觀者返回《后賦》文本尋找答案。另外,部分畫家則借助描摹二客的姿態動作,輔助呈現蘇軾與鶴的對話關系。例如,在南宋馬和之的《后赤壁賦圖》②中,舟上所有人物皆以突出的姿態回望橫江飛來的孤鶴,盡管未能突顯蘇軾與孤鶴之間的神秘關聯,但孤鶴帶來的視覺沖擊仍然是顯著的,夸張的回望姿態顯示眾人對孤鶴的關注,而這種關注即隱含著特定的象征意味。在清人王素所畫冊頁《人物故事·赤壁夜游》中,蘇軾正凝神遠眺從天際飛來的孤鶴,在其感染之下,一客也接受到孤鶴攜帶的情感訊號,興高采烈地遙指孤鶴,似向蘇軾述說他的驚喜。
當然,在相當一部分赤壁圖中,這種“神交”的對話關系并未成立,“孤鶴”僅作為一個標志性意象出現,被用以強化圖像與文本的關聯,其象征意義被全然忽視。明代文徵明的長卷《仿趙伯骕后赤壁賦圖》表現泛舟赤壁的場景,人物構成與喬仲常之作如出一轍(蘇軾與二客、一童子、一船夫),然而人物的視點卻截然不同:蘇軾與二客不約而同地望向遠方,孤鶴自他們身后飛來,二者并未形成任何交流。這一藝術處理方式直接影響了吳門后學,如仇英《后赤壁圖》④畫蘇軾與客把盞言歡的場景,雖有孤鶴自天際掠過,但蘇軾甚至沒有意識到鶴的存在。在此后不可勝數的《后赤壁圖》扇面中,“孤鶴”的點綴性質愈加突出,畫家多以簡筆勾勒蘇軾與二客,人物面目表情尚難以辨識,更不必言及與孤鶴之間隱秘的情感關聯。
對“鶴”形象的描繪,說明畫家已經捕捉到《后賦》文學敘事的緊張點,利用“孤鶴”形象揭示《后賦》的情感高潮,渲染蘇軾筆下奇幻縹緲的文學意境。遺憾的是,“孤鶴橫江”的象征意味及其承載的情感寄托,似乎沒有獲得畫家的足夠重視,或者說超越繪畫藝術的表現范疇。恰如戴表元所云“畫圖不盡當年恨”(《題赤壁圖》),蘇軾與孤鶴“惺惺相惜”的心理狀態,即使在《后賦》文本中也表現得相當隱晦,直接圖入丹青則更為不易。這些“不太成功”的畫作也在提醒我們,文學文本的視覺轉換始終存在難以克服的藝術缺陷。透過赤壁圖中的孤鶴意象,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后賦》的奇幻色彩,卻難以領會蘇軾與孤鶴之間神秘的對話,更無法深入探知蘇軾幽邃的人生哲理。
四、題畫者、畫家與蘇軾的精神對話
畫家以生動的視覺形象演繹蘇軾的赤壁文學,通過再現蘇軾與客的舟上對話、蘇軾與自然的精神交流、蘇軾對鶴的心靈感應等內容,對蘇軾原作加以視覺詮釋與再創造,并結合自身的經歷感受,重新思考蘇軾原作寄寓的人生命題,在圖像內部形成與蘇軾之間的對話關系。而在圖像之外,還有另一重對話關系值得重視,即題畫者、畫家與蘇軾的精神對話關系。這一層對話關系的確立,以文字題跋為主要載體。一般來說,繪畫作品的題跋分為兩類,一類直接題寫于卷軸上,以畫家自題居多,除了記錄創作時間等基本信息的簡單款識以外,具備敘事或抒情功能的詩詞短文也較常見;另一類則書于畫作拖尾,不作為畫面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歷代赤壁圖中,第二類題跋數量尤為龐大,同一幅赤壁圖往往經由多人書寫題跋,各段題跋的內容、字體、甚至書寫風格各不相同,集中反映了不同題畫者對畫作、畫家以及蘇軾赤壁文學的不同理解。在圖像與文本之間,題畫者、畫家與蘇軾構筑了又一層重要的對話關系,一方面充分展示了赤壁圖詩畫相融的藝術特點:視覺畫面與文字題跋相互映襯、相互闡發、相互補充,共同呈現后世藝術家對詩、畫這兩種不同藝術形式的理解與創造;另一方面,借由題跋這一物質載體,觀畫者與畫家展開了以赤壁圖為中心的情感交流與思想碰撞,共同參與了與蘇軾之間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
受制于繪畫的表現局限,幾乎所有畫家都無法一一復現《后賦》記敘的游蹤變化,更不必說蘇軾赤壁之游復雜幽微的心路歷程。為了彌補這一藝術局限,歷代畫家(尤其是文人畫家)往往以自題的方式“發聲”,直接點破圖像蘊含的主旨深意。不過有時候,這一任務則留待具備一定鑒賞能力的題畫者,他們或是畫家的摯友,或是畫家的后學晚輩,又或是畫家的異代知音,皆以題寫詩賦的藝術手段揭示潛藏在畫作背后的思想情感,形成對畫面的延展或補充,生動地展示了蘇軾赤壁文學的多重意蘊。
首先,圖像與畫家自題的詩文相互映襯、補充,共同展現蘇軾原作的多重意蘊。例如,明代畫家張瑞圖《后赤壁賦圖》截取登臨的片段入畫,刻畫蘇軾俯觀江流之時百感交集的情狀。全幅筆墨簡凈,意在烘染早冬的蕭索光景,畫家題《后賦》“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卷后自書蘇軾《赤壁詞》,氣勢磅礴,與平和靜穆的畫面形成較大反差。畫面的清冷與題跋的激越交相映襯,構成了蘇軾形象的疊影效果:站在赤壁山巔的蘇軾,究竟是陷入“愀然而悲,肅然而恐”,還是驚嘆“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張瑞圖將視覺畫面與有關黃州赤壁的多個文學作品貫穿起來,提示圖像詮釋的多種可能。
其次,畫家借助題跋表白赤壁圖的創作動機,呈示與蘇軾之間的異代對話。明代畫家陳淳的《前赤壁圖》自題:“客有攜《前赤壁賦》來田舍,不知余何時所書,乃欲補圖。余于赤壁,未嘗識面,烏能圖之?客強不已,因勉執筆圖。既玩之不過江中片時耳,而舟中之人,將謂是坡公與客也,夢中說夢,寧不可笑耶?”陳淳用詼諧性的語言講述了赤壁圖的創作來由,他并未去過黃州赤壁,但因不好拒絕客人的盛情,遂按照腦海中閃現的“程式化”的赤壁圖元素作畫。雖是玩笑性的口吻,卻真實地揭示了入明以后畫家創作赤壁圖的心理狀態,“夢中說夢”更在無意間點破陳淳對《后賦》虛構性的理解與把握。學者巫鴻曾征引這條題跋并指出:“并非每個畫過《赤壁圖》的畫家都真的去過赤壁,他們之所以繪制這類圖畫的一個原因在于這一藝術行為相當于象征的旅行。”[5](84-85)巫鴻的解讀確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旅游意識盛行的明代,作為“勝跡”的赤壁激活了畫家的懷古情懷,滿足文人對旅行的想像與期待。不過,“赤壁之游”之所以成為一個象征性意象,旅行主人公蘇軾也發揮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在赤壁文學之中,蘇軾對自然的審美觀照、對歷史的洞察、對宇宙的探索以及對現世的感發,都有效地刺激了畫家的創作沖動,甚至觸發他們對蘇軾赤壁之游的效仿與競賽心理。
清人張在辛《赤壁賦書畫》(圖3)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個案。畫卷上有一段自題:

圖3 (清)張在辛《赤壁賦書畫》(局部)
丁酉八月九日,偕王石丈兄泛舟南灣卜畫,及夜月初弦,水光如鏡,樹影參差,與岡巒相映,不勝江湖之想,因念此景不得與歷長兄共之,深以為歉。明旦,遣人西行,敬書髯蘇《赤壁賦》兼綴以圖相寄,使知我輩衿懷到處不乏清興。若令高西園知之,又不知作何艷羨?白亭弟張在辛記。
張在辛攜友人王啟磊(字石丈)泛舟出游,江山風月之美令其生發“江湖之想”,欲將此番雅興寄予遠方的友人王德昌(字歷長)。在張在辛眼中,抒寫泛舟之游的清興并不需要多么精彩的辭章,一幅《赤壁賦書畫》就足矣。可見,在清代,以《赤壁賦》為主題的書畫創作已然成為一項具備特定意涵的文化活動。張氏《赤壁圖》的創作動機,雖是伴隨著書《赤壁賦》而產生,卻并非簡單的文圖轉換,而是融入了自我經驗與私人化的情感因素。《赤壁賦書畫》恰是張在辛與王歷長精神交流的物質媒介。從這段題跋看來,構建以《赤壁賦書畫》為物質媒介的精神對話,張氏本人頗為自得,“若令高西園知之,又不知作何艷羨?”張在辛擅長鐫刻印章,王啟磊工畫,王德昌精于裱褙字畫,高鳳翰目之為“三絕”,并與他們交往甚密。當高鳳翰看到此圖之后寫下一段跋語,饒有興味地回應了摯友的調侃,盛贊張氏書畫令人“塵眼頓洗”,字里行間流露著傾慕之意。
從這則題跋可以看出,在清初書畫家的眼中,赤壁圖即是對“清興”的最佳詮釋。以《赤壁賦書畫》為中心的唱酬贈答,聯結了數位清初著名的書畫家,展現了他們共同的生活情調與藝術追求。清初畫家通過創作《赤壁圖書畫》,分享從自然山水中獲得的樂趣,表白對蘇軾人生態度的羨慕與效仿。就藝術成就而言,張氏此幅無論是構圖、筆法還是風格諸多方面并無新意,大概就是一幅“程式化”赤壁圖,故在美術史上無人問津。然而,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看,這幅赤壁圖及其題跋極為生動地揭示了蘇軾及其文學作品在清初的重要反響,不僅折射出蘇軾在清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反映了蘇軾赤壁文學在清初的經典化面貌。
清人楊晉畫《赤壁圖》,自題:“庚申閏月廿有六日,客水云精舍,偶觀董思翁《赤壁圖》,展玩之余,座上人出紙索畫,率筆為此,不計工拙也。”激發楊晉創作靈感的不是蘇軾原作,而是董其昌的《赤壁圖》。此圖主要呈現蘇軾與赤壁的空間對話,以視覺形象的鮮明反差回應《前賦》的思想要旨,對文本的闡釋效果極佳。不過,楊晉卻言“率筆為此,不計工拙”,這自然是謙辭,但也表明他對赤壁圖的“展玩”態度。楊晉不是在創作一幅嚴肅主題的繪畫,而是以赤壁圖為載體抒寫某種文人情致。這種文人情致不需要實地重游才能獲得,鑒賞或創作《赤壁賦書畫》便是一種極佳的藝術路徑,恰如畫面的題詩所云“只愛圖中風月好,不須赤壁問重游”。赤壁圖儼然成為文人趣味的代名詞,而這種文化功能的獲得,應是根源于蘇軾赤壁文學經典地位的確立。
當然,僅以“清興”“玩賞”等文人雅趣概括蘇軾赤壁文學及其夜游赤壁事跡的后世影響,未免過于狹隘。事實上,蘇軾關于黃州赤壁的文學書寫,在敘事、抒情、議論等多個維度都具有開放性的意義空間:低沉與昂揚、浪漫與豪放、憂懼與坦然、苦悶與閑適、掙扎與解脫多個面向并存,共同呈示了蘇軾極其豐富的精神世界。在藝術實踐中,抽象的精神內涵是極難簡化為直觀的視覺形象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軾原作廣闊的情感空間令絕大多數讀者都能從中找尋共鳴,也因此激發了歷代畫家持續不衰的創作熱情。表面上,通過對文本內容的剪裁入畫,畫家意欲傳達對蘇軾原作的獨特理解;而更深層的藝術追求則是借助赤壁圖的創作,抒發對蘇軾人生際遇的惋惜,對其生活態度的認同與效仿,對其藝術才華的稱賞與追慕,以及對其人格魅力的贊嘆與欽佩。誠如王水照所論,蘇軾通過文字傳達出的“人生體驗、人生思考與人生境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后繼者的“人生模式的選擇與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6],歷代赤壁圖及其題跋皆綜合反映了蘇軾這種深遠的文化影響力。

圖4 (金)武元直《赤壁圖》
就題畫者、畫家與蘇軾的精神對話關系而言,金代武元直的《赤壁圖》(圖4)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這是一幅單景式赤壁圖,文本依據較為模糊,陡立的峭壁呼應《后賦》“江流有聲,斷岸千尺”,浩淼煙波又讓人聯想《前賦》“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翻卷的浪花又似乎是《念奴嬌》“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寫照。就畫面呈現而言,畫家一方面以典型的凝望姿態隱喻蘇軾與黃州赤壁的精神互動,借此構想蘇軾與曹操、周瑜之間的隔空對話,傳達江山依舊、英雄不再的歷史滄桑感;另一方面則以無邊的自然與渺小的孤舟之間的懸殊對比,暗示《前賦》“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于一粟”的人生命題。武元直并非專業畫工,這種藝術處理應別有一番用意。武元直生前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并不多,畫卷上也未留下只言片語。幸運的是,圍繞這幅畫及武元直的赤壁圖創作,仍有不少相關的題詠文字傳世。這些珍貴的題跋文字,生動地呈示了一場以赤壁圖為中心的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金人李晏作《題武元直〈赤壁圖〉》詩:
鼎足分來漢祚移,阿瞞曾困火船歸。一時豪杰成何事?千里江山半落暉。云破小蟾分樹暗,夜深孤鶴掠舟飛。夢尋仙老經行處,只有當年舊釣磯[7](102)。
此詩未被題于畫卷之后,詩人并未直摹畫面,而是敘寫對赤壁之戰的歷史追懷。詩歌結尾以“尋夢”的方式展開聯想,最終落在一個極具抒情意味的歷史遺跡之上,傳遞人世變遷的蒼涼之感。其中,“云破小蟾分樹暗,夜深孤鶴掠舟飛”似是對《赤壁圖》的釋讀,但意象、情景皆與武元直現存畫作不一致,有研究者據此斷言,此詩乃針對武元直其他畫作的題詠,非今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之畫卷[8]。這種說法未必確切,相比繪畫,詩歌的表現范圍與想像空間更加廣闊,“夜深孤鶴掠舟飛”亦有可能是李晏觀畫之后對蘇軾原作的直接回溯。通過觀覽《赤壁圖》,李晏完成了對《赤壁賦》的重新審讀,抒寫對蘇軾其人其事的自我認識。更為精彩的是趙秉文的《念奴嬌·追和坡仙赤壁詞韻》,全詞如下:
秋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扁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枻長歌,嫦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千丈。可能容此人杰? 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今古夢,只有歸鴻明滅。我欲從公,乘風歸去,散此麒麟發。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此詞書于武元直《赤壁圖》拖尾,詞人趙秉文以次韻赤壁詞的方式緬懷東坡,除了用東坡韻,還隱括了《前賦》與《念奴嬌·中秋》的詞句,表達對蘇軾深深的仰慕之意。詞作開篇即以“問月”點明泛舟赤壁的時點,緊接著轉入對泛舟赤壁的生動描繪,“叩枻長歌,嫦娥欲下,萬里揮冰雪”化用《赤壁賦》文意,逼真地還原了月夜的清冷氛圍。“京塵”一句筆鋒突轉,盛贊蘇軾為“人杰”,為其坎坷的人生際遇發出深沉的慨嘆。過片承接上闋的感發意味,并以李白騎鯨的傳說注入浪漫色彩,既是對蘇軾形象的豐富,也是對《前賦》夢幻意境的呼應。隨后,趙秉文再度感慨坡仙的逝去,流露“人生如夢”的虛幻感。晚年的趙秉文生活在金王朝沒落衰亡之際,深陷于救國無望的憂慮之中,掙扎于“入世”與“出世”的思想矛盾之間,與黃州時期的蘇軾有著類似的心境。最終,趙秉文從虛無中解脫出來,以“我欲從公”表白自我,高呼對蘇軾的堅定追隨。
在金代文人圈中,蘇軾享有極高的影響力,趙秉文對蘇軾尤為景仰,其詩風與書風皆有意學習蘇軾。此詞雖置于武元直《赤壁圖》的拖尾,卻是趙秉文人生感懷的自我書寫,詞人似乎遺忘了畫家武元直,盡管從其他題畫詩文來看,他對武元直其人頗為熟悉。因此,此詞是否即為武元直畫作的題詠,仍然存疑。不過,即使二者在創作根源上不存在緊密的關聯,就藝術效果看來,當圖像與文本并置于同一畫卷上時,繪畫與文學之間互相滲透、互相補充的關系獲得了生動的呈示。武元直濃墨渲染黃州赤壁的巍峨險要,以直觀的視覺形象說明:在永恒的宇宙自然面前,人類是如此渺小,巧妙地回應《前賦》對人事變遷的浩然長嘆。這種人生感慨在趙秉文身上被復制了,盡管處于不同的歷史情境,但情緒心態卻如此相似,仿佛跨越時空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種人生感慨的“復制”并沒有終結,它在元好問的《題閑閑書赤壁賦后》中再度出現: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才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余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徑,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后。《赤壁》,武元真(直)所畫。門生元某書[9](112)。
元好問盛贊蘇軾赤壁詞,并揣度蘇軾的創作意圖乃是以周瑜自況抒今古之思,繼而高度評價趙秉文的追和詞,以“仙語”道出趙詞清曠飄逸的特點。隨后,元好問以平實的筆調記敘題跋緣由: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元好問得以親睹此畫,他驚贊趙秉文的詞風與字畫俱得蘇軾衣缽,然而想到趙秉文已隨蘇軾故去,心中感傷萬分,遂寫成此跋,惺惺相惜之意表露無遺。可惜的是,據元氏所記,這段題跋理應書于趙詞之后,無奈原跡現已不存,有可能為人割去。如果直接題于卷后,則可向觀者提供更有益的鑒賞參考。趙秉文追懷蘇軾,元好問追懷趙秉文,類似的情思與感發一遍遍在歷史中重現。
更鮮明地體現這種“復制”式的人生感慨的是元好問《赤壁圖》詩:
馬蹄一蹴荊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誤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云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卷天為紅。至今圖畫見赤壁,仿佛燒虜留余蹤。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云閑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群雄?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10](1360)。
此詩未言明《赤壁圖》的歸屬,極有可能就是元氏接觸到的武元直《赤壁圖》,或是題畫,或是觀畫有感。元好問無意對《赤壁圖》的藝術水準進行正面評判,僅以“至今圖畫見赤壁,仿佛燒虜留余蹤”點明畫作逼真的藝術效果,側面烘托畫家技藝之高超。詩人以濃墨重彩寫三國赤壁之戰的史事,又以清逸筆觸寫蘇軾泛舟赤壁的雅興,但這兩者皆非文本的終極指向,作者更深層的用意乃是借由題詠《赤壁圖》,分享自身的生活體驗與內心感觸,抒發懷古傷今的情感意緒。在赤壁詞中,蘇軾錯將黃州赤壁當周郎赤壁,極寫周瑜“雄姿英發”以反襯自我的“早生華發”,抒發屈謫黃州的人生失意。生于金朝衰敗的時代,元好問寄希望于如同蘇軾的“群雄”出現以重振國運,但他也深知,蘇軾早年的壯志豪情最終在現實中消磨殆盡。時間流轉,無論是羽扇綸巾的周瑜,還是在黃州赤壁盛贊周瑜的蘇軾,無論是已經成就霸業的千古英雄,還是評說英雄功業的旁觀者,俱已故去,最終化為一聲悠長的哀嘆。元好問預感自己將步蘇軾后塵,為國憂心卻也無法力挽狂瀾。“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看似針對歷史人物的感慨,本質上卻是一種自我憑吊。此詩雖為詠畫,卻近乎完全脫離視覺形象,借助對歷史事件與文學場景的回顧,元好問從精神層面進入到赤壁圖內在意蘊的探討,積極響應了蘇軾赤壁文學關于宇宙人生命題的深沉思考。這種思考與感傷,在類似的人生際遇之下獲得了深化與 升華。
五、結論
歷代赤壁圖對蘇軾赤壁文學的視覺詮釋,集中體現了圖像與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關系,揭示了蘇軾赤壁文學的多重意蘊。在圖像內部,基于對蘇軾原作思想主旨的理解,畫家以生動的視覺形象復原了主客對答的人物關系,嘗試突破繪畫表現歷時性場景的藝術極限,以富有包孕意味的剪裁融化,引發觀者對蘇軾泛舟赤壁復雜的心路歷程的探索。對蘇軾原作蘊含的時空意義,尤其是承載雙重時空意義的赤壁意象,畫家積極作出回應:在時間維度上,畫家精心塑造蘇軾對赤壁的仰望或俯眺形象,隱喻蘇軾與“風流人物”跨越時空的歷史對話;在空間維度上,畫家對赤壁意象加以夸張化的藝術處理,在視覺上構成赤壁與扁舟的強烈對比,揭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懸殊差異,借此傳達蘇軾赤壁文學隱含的自然觀與山水精神。另外,部分優秀的畫家關注到“孤鶴”意象,通過特定的人物姿態與畫境營構,刻畫蘇軾與孤鶴的精神共鳴,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后賦》虛幻縹緲的神秘氛圍。此外,畫家還通過自題等輔助手段,在再現文本內容的同時,注入個性化的情感體驗與人生思考,在卷軸上達成與蘇軾之間的異代精神對話。
在圖像外部,赤壁圖題詠也是構筑對話關系的重要一環。優秀的題畫者往往巧妙地繞開了繪畫作品本身,將“觀畫”視為與蘇軾展開隔空對話的捷徑。題跋的創作者從自身的人生際遇出發,思考蘇軾曾經思考的疑惑,探索蘇軾曾經探索的命題。他們不僅是畫家的知音,更想成為蘇軾的知音。在同一幅畫卷的拖尾,不同的題跋猶如蘇軾原作的不同“副文本”,它們與“元文本”之間的并行、補充甚至背離的多重關系,形成了眾聲喧嘩的閱讀效果,展現了不同讀者在不同時代背景、不同生活際遇之下對文學經典的詮釋與再創造,共同組成了“東坡赤壁”復雜繽紛的多面影像。直至今日,當我們透過文本與圖像,重新審視后人與蘇軾的親密互動之時,我們也間接地參與到這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之中,“古今如夢,何曾夢覺”的人生感嘆仿佛在耳畔再度響起。
注釋:
① 以赤壁圖為對象的藝術史研究,詳參Stephen Wilkinson, “Paintings of ‘The Red Cliff Prose Poems’ in Song Times”,, 27:1(1981) , pp.76-89;Daniel Altieri, “The Painted Visions of The Red Cliffs”,, 29:3 (1983), pp.252-264;Jerome Silbergeld, “Back to the Red Cliff: Reflections on the Narrative Mode in Early Literal Landscape Painting”,, Vol.25, Chinese Painting(1995), pp.19-38;板倉圣哲撰,張毅譯《宋代繪畫和工藝作品中的赤壁圖》(《上海文博論叢》2006年第3期,第54-57頁);賴毓芝《文人與赤壁——從赤壁賦到赤壁圖像》(《卷起千堆雪——赤壁文物大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09年版,第244-259頁);郁文韜《〈赤壁圖〉經典圖式的形成與衰落》(中央美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郭薇《文本與繪畫的關系——以中日<赤壁圖>的構成元素為例》(《文藝爭鳴》2015年第2期,第199-204頁)等。古代文學研究者對赤壁圖的研究探討成果,參閱張鳴《文學與圖像:北宋喬仲常〈后赤壁賦圖卷〉對蘇軾原作意蘊的視覺詮釋》(《國學學刊》2017年第4期,第83-98頁);田曉菲《影子與水文——關于前后〈赤壁賦〉與兩幅〈赤壁賦圖〉》(載上海博物館編《翰墨薈萃:細讀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311頁);王兆鵬《宋代<赤壁賦>的“多媒體”傳播》(《文學遺產》2017年第6期,第4-19頁)。
② (南宋)馬和之《后赤壁賦圖》,卷,絹本,設色,25.9cm*143cm,故宮博物院藏。
③ (南宋)李嵩《赤壁圖》,團扇,絹本,水墨淡設色,25cm*26.2cm,美國納爾遜·漢金森藝術博物館藏。
④ (明)仇英《后赤壁圖》,卷,絹本,墨筆,24.3cm*39.9cm,上海博物館藏。
⑤ (明)仇英《赤壁圖》,卷,絹本,設色,25.1cm*90.8cm,遼寧省博物館藏。
⑥ (清)王翚《仿唐寅赤壁圖》,軸,紙本,設色,71.6cm*36.8cm,作于康熙十四年,故宮博物院藏。
⑦ (舊傳)南宋楊士賢《赤壁圖》,卷,絹本,水墨淡設色,30.9cm*128.8cm,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⑧ (傳)北宋喬仲常《后赤壁賦圖》,卷,紙本,墨筆,29.7cm*560cm,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
⑨ (明)丁云鵬《畫后赤壁》,扇面,金箋,設色,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⑩ (清)錢杜《后赤壁圖》,冊,紙本,墨筆,22.5cm*33cm,南京博物院藏。
[1] 蘇軾. 蘇軾文集[M]. 孔凡禮, 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2] 板倉圣哲. 日本繪畫中的赤壁形象[C]//臺北故宮博物院. 卷起千堆雪——赤壁文物大展. 臺北: 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社, 2009.
[3] 吳小如. 古文精讀舉隅[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4] Jerome Silbergeld. Back to the Red Cliff: Reflections on the Narrative Mode in Early Literal Landscape Painting [J]. Ars Orientalis, Vol.25, Chinese Painting (1995), pp. 19?38.
[5] 巫鴻.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M]. 肖鐵,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6] 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J]. 文學遺產, 1989(5): 87?96.
[7] 元好問. 中州集:卷二[M].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8] 衣若芬. 戰火與清游: 赤壁圖題詠論析[J]. 臺北: 故宮學術季刊, 2001(4): 63?102.
[9] 元好問. 元好問全集:卷四十[M]. 姚奠中.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10] 元好問. 元好問詩編年校注[M]. 狄寶心, 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Text and image: Dialogues and multiple connotations in the painting of “The Red Cliff”
CHEN Lin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ubject matters of poetic paintings, “The Red Cliff” offers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age and text in traditional China. Previous studies focus primarily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within the painting of “The Red Cliff”, while research on its literary value and cultural meaning has been somewhat lacking. Painters masterly transformed the literary texts into visual images, and thus amplified and extended the literary meaning of Su Shi’s works in their own ways. Within the pictures of “The Red Cliff”, there are multi-level dialogues between Su Shi, the “Guest”, the Red Cliff, and the lone crane. Beyond the images, literary inscriptions and colophons also reflect how different artists interpreted the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Su Shi’s works. In other words, “The Red Cliff” serves as a material medium that links the inscription writers, the painters and Su Shi together across time and spac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essay reconsiders Su Shi’s grea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Red Cliff”; Su Shi; “Prose-poems on the Red Cliff”; dialogue; connotation
[編輯: 胡興華]
2018?03?14;
2018?05?14
陳琳琳(1991—),女,廣東揭陽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聯系郵箱:cll9175@pku.edu.cn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18
I206.2
A
1672-3104(2018)04?01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