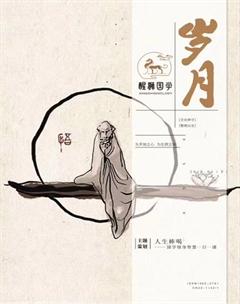一個王朝遠去的背影
陳華娟
想不到,有這樣一批文官武將,時隔800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站在煙波浩淼的東錢湖畔,就像當年守護著墓主一樣,虔誠地恭候每一位到訪的游客。也許有人會說“這只是石刻的形象嘛”,是的,它們是用石頭雕刻而成的。但任何一塊石頭一旦被雕刻成具體的藝術形象時,一股無形的生命的血液也就注入其中,它們就成為了一種寄托和象征。要不然怎么會有表情含蓄的文官、神態彪悍的武將呢?又怎么能感覺得到朝服的飄逸、盔甲的厚重呢?盡管他們不曾說過一句話。可當看到那些肢體殘缺、面目非全的成員時,一切已盡在不言中,因為任何語言在此都變得蒼白和多余。面對陣容肅穆的“江南兵馬俑”,我們仿佛穿梭在時光的隧道中,看到了一個王朝遠去的背影。
坐落在湖光山色之間的“南宋石刻公園”,為每一位游客營造了對話古人的空間、叩問歷史的氛圍。它既是一座石刻的博物館,又是一卷石刻的南宋史。
中國的石刻作品大都集中在佛教石窟和皇家陵園,但南宋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帝王夢想死后都能魂歸故里一回到河南鞏縣的宋皇陵安息,因此,南宋皇室身后都是草草暫厝,沒有留下能代表時代風格的宏大陵園。東錢湖的南宋墓道石刻群便成了那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南宋時期的京都臨安(今杭州)有著“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寧波)人”的格局,而當時的鄞縣更有“滿朝文武,半出史門”之說。史氏家族在南宋歷時一個半世紀,獲得了“一門二王,三相四宰,五尚書,七十二進士”的顯赫與榮耀。其中,史浩、史彌遠、鄭清之和史嵩之四個宰相死后以岙為陵,葬于東錢湖四周,由于他們的政治生涯幾乎涵蓋了南宋歷史上最重要的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和理宗五個時代,因此他們的墓道石刻也代表了當時南宋的藝術水平、審美標準、價值取向和社會地位,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國也屬罕見。這批豐富而又完整的歷史遺存充分展現了南宋石雕藝術的非凡創造力,為后人研究南宋時期的美術史、文物考古史和雕刻藝術史等領域填補了空白,同時也成全了東錢湖,使它在具有浩浩蕩蕩、浮光耀金的壯美之外,又多了幾重人文的沉淀和歷史的回音,增加了它的縱深度和厚重感。歷盡滄桑800年,曾經繁華過后的寂寞,長期蒼涼之中的沉郁,依然荒蕪之下的執著,都為人們找到了走近它、審視它、讀懂它的無數理由。
古代稱墓道石刻為石像生,它以凝固不朽的神態象征生命的永恒。人像又被稱作“翁仲”,翁仲是一位秦朝猛將,經常出征匈奴,所向披靡,勢不可擋。其死后的銅像被立于咸陽宮司馬門外,所以后世遂將人物銅像和石像稱為“翁仲”,讓它“守”在宮外、墓道,以示護靈儀仗之意,其儀仗規格的大小也顯示了墓主的身份、等級和地位的高低。據初步統計,分布在今浙江鄞縣上水、下水、韓嶺、橫街和福泉山等地的墓道石雕共有50多處,計200多件。其中的文臣(忠)、武將(勇)、蹲虎(節)、立馬(義)、跪羊(孝),都是成對排列于墓道兩側,有的還有石雕墓表柱、石刻太師椅和仿木石牌坊等。在這些墓道石雕群中,最大的文臣武將石雕像高達3.5米,形神兼備,惟妙惟肖,或肅穆或震怒,個個都能呼之欲出,身上的衣冠盔纓、袍服甲胄都雕刻得極具質感。目光留連之間,仿佛讓人感覺鼓滿風雨的衣袖在舞動,披盡雷電的盔甲在作響。對動物的雕刻更是造型逼真,神態各異,各種圖案紋飾的設置也是精細入微,寓意深長,對封建倫理和文化作了極為形象的詮釋。
中華文化發端于黃河流域,中原大地便成了歷朝歷代演繹春秋的大舞臺,即使人生有限,帝王將相也不想就此罷休,還千方百計地把生前的霸氣、財氣和王氣帶進墳墓,讓石人石馬來守護那比尸體爛得更快的靈魂。結果,當后人發現那一座座地下宮殿時,墓主早已灰飛煙滅,而那些無名工匠留下的墓道石刻卻成了傳世的藝術瑰寶,北方陵園粗獷豪放、大氣激越,相比之下,南宋墓道石雕顯得精巧典雅、委婉多姿,這正是江南山的靈氣、水的秀美給了王朝滋潤,于是就把這種靈感化作了一件件墓道的石雕作品,形成了與北方皇陵墓道石刻藝術完全不同的風格。南宋石雕人物的表情在威嚴中又不失恭敬順從的神態,體現了將相權臣對皇權統治下的社會秩序的自覺維護。石馬的口、鼻、眼的各部位都極具質感,似乎剛從沙場歸來,正汗淋淋、氣喘喘,連頰部的經絡都清晰可辨。即使馬鞍、飾物這些附屬物,也不輕易放過對細節的詳盡刻畫,處處讓人能觸手可感:鐵質踏腳的沉重,絲綢飾物的飄逸,還有海獸、荷花、石榴、牡丹和金銀花等圖案的精雕細刻,叫人嘆為觀止。這些圖案分別寓意著“搏擊風浪”、“圣潔凈土”、“多子多福”、“榮華富貴”和“世代相傳”等,意味深長。如果說皇陵的雕刻著重表現為“國事”這一主題的話,那么作為宰相的史氏墓道石雕所表現的則是“家族興旺”的“家事”作為主題了。
南宋畢竟只是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國力贏弱,朝政腐敗。“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多少將士為了收拾舊河山,萬里赴戎機,頭顱拋疆場。可昏庸的皇帝卻依然整天沉湎于“日日歌舞,夜夜酒色”中,“直把杭州作汴州”。盡管南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沒有可以值得書寫的一筆,還茍延殘喘了150多年。但在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一道獨特的文化奇觀一名人輩出,著作宏豐,猶其是“宋詞”的創作成就,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是繼“唐詩”之后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在南宋的夜空居然也是星漢璀璨:岳飛、辛棄疾、陸游、張孝祥、劉克莊、李清照、范成大、張元干、吳文英和王應麟等,這一串串響亮的名字,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成為后人代代承傳的精神財富和文化脈絡,而散布在東錢湖四周的墓道石雕,更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它們在我國石雕藝術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如今它們已被人們所重新認識,并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誰會想到,這些作品的聞世時間比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還早了整整500多年。那些曾經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無名石匠一民間藝術家,或許都可以稱為藝術大師米開朗琪羅的祖師爺呢。若是當年大師能親眼目睹這些石雕的話,一定會驚嘆不已。米開朗琪羅在留下他的作品的同時也留下了他那不朽的名字,南宋的民間工匠們雖然沒有留下任何人的姓名,但是凝聚著他們無窮智慧和創造性的作品卻成了一座永恒的紀念碑。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南宋王朝畢竟氣數已盡,誰也挽留不住它那注定走向滅亡的命運。宰相也罷,望族也罷,生前的顯赫,身后的殊榮,都成為雕刻在石頭上的奢望與夢幻,總想與湖山共朝夕。然而湖山依舊,墓道無主,只有那些無言的石雕,在苦苦等待了800年后,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新歸宿。
800年的光陰畢竟是漫長的,即使再堅硬的石頭也會遭風化,精制的南宋石雕也不例外,于是留下了一些“殘缺的精品”:被砍了頭的文官,被斬了劍的武將,還有面目非全的馬、虎、羊,可它們依舊守著時空,在夕陽的余輝中面面相覷,形影相吊,仍在揖別逝者,揖別故國,恰似一首凝固的挽歌,還在哀怨著一個不幸的王朝。
編輯/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