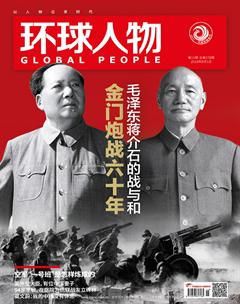劉小東,動物兇猛
許曉迪
他以精準、生猛的眼睛看世界,用相機和畫筆,記錄下社會變遷中的矛盾和毀滅。
1984年,剛從中央美院附中畢業的劉小東,花25塊錢買了一架舊相機,趁著暑假,和一幫同學跑到北戴河和南戴河玩了一趟。那會兒他正和同學喻紅談戀愛,“老有種像在做夢的感覺”,擔心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在海邊照了好多相,其中有些是偷著抓拍的,連喻紅都不知道。
最新出版的攝影集《眼前往事》里,18歲的喻紅出現在第一頁,短發厚密,面容沉靜。此后,她的身影成為書頁間的時間軸,劉小東在她身旁,從北京到紐約,從抱著女兒拍滿月照到三顆腦袋湊到一起,六只圓鼓鼓的眼睛亮閃閃。
34年過去,劉小東沒什么改變。只是此刻,他從拍照的人,變成了被拍者。坐在畫室一角,接受相機的定格,那張曾出現在王小帥、賈樟柯、侯孝賢鏡頭中的臉上,露出點局促。他抱怨著接受采訪的“痛苦”,身后的墻上掛著他在老家畫的畫——《金城小子》系列里的《我的埃及》。
無明、無辜、無情、無差別
《眼前往事》的封面上,豬、人、狗縱向排開,暗示著拍攝者一視同仁的目光。垂死的兔子,做完子宮切除的狗,土道上的死鴨子,兩只撅著屁股埋頭吃草的羊……劉小東鏡頭下的動物,總能咂摸出一些人間滋味。尤其是豬。“我覺得豬很簡單,但它能傳達一種被命運宰割的無奈,就像人一樣,總是被無法把控的力量推進自己也無法弄清的世事變遷中。”劉小東說,“我們都是同伙兒”。
在陳丹青看來,劉小東的稟賦正在于“如動物般觀看”,“無明、無辜、無情、無差別,不存意見,不附帶所謂文化”。他從來舍不得買一個貴相機,看似隨手拍,但一出手就老謀深算,親人愛人、豬狗馬驢、各國風物,那些微妙難言的時代況味與情感結構,都被他攝入照片,凝固儲存。
1990年,陳丹青在唐人街一家書店里,看到了《美術》雜志上的一幅畫。畫中陽光明媚,紅墻后露出青綠的田野。藝術家眉頭緊鎖,注視遠方,身邊的女友看向地面,表情滯重。這幅畫的“底片”是1989年劉小東帶喻紅回老家金城時拍的一張合照,他把它移上畫布,畫成這幅《田園牧歌》。
晚上回去,陳丹青就給劉小東寫信,“中國出了個天才,畫得這么好”。那一年,劉小東27歲,各種主義都玩了一遍,又民族又敦煌,一會兒畢加索一會兒梵高,學克萊因把墨潑在身上在畫布上滾,搞行為藝術,最后決定從汪洋大海般的美術史里往回撤,回到現實,回到具象,回到身邊人。
1990年的“劉小東油畫展”上,當這些描繪凡夫俗子日常瑣事的畫作被展出時,“從英雄頌歌到平凡世界”的藝術史翻頁也在悄然發生。在最早發現劉小東的批評家范迪安看來,他的出場代表著“中國藝術的年代轉換”,而那些“畫中人”也正是于上世紀90年代初登歷史舞臺的一代新人,他們面對鋪天蓋地的都市消費、娛樂文化和金錢資本,焦灼、混亂、浪漫、放縱,野心勃勃地尋找一種新鮮生猛的語言,講述自己與別人的故事。
這些人里,有王小帥、賈樟柯、張元,當然,也有劉小東自己。
尊重那些有意思的和沒意思的個人生活
1990年,一個學美術的20歲山西青年流竄到北京,一心想考電影學院。有一天,他跑去看一個畫展,擠在人群里,聽說邊上那個來回溜達的就是畫家。“我瞟過去,那個鏡頭就定格了:青煙盤旋,寸頭,一臉胡子茬,眉頭微蹙,青筋暴露……”
多年以后,賈樟柯仍記得那次看劉小東的畫,心里有多震撼:“看畫里面煙熏火燎的火鍋店,看白胖子扛著氣槍帶兒子穿過小巷,就知道這藝術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原來還可以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
而此時的劉小東,卻生起了拍電影的念頭。“當時年輕,野心勃勃的。繪畫多安靜,苦哈哈的一個人;電影多刺激,可以指揮那么多人,作威作福。”
他努力了3個月,還是沒考上電影學院的研究生,但拍電影的念頭一直沒斷。1992年,他和喻紅出演了王小帥的首部電影《冬春的日子》,本色出演一對青年畫家夫婦,在時代騰轉中苦悶挫敗又蠢蠢欲動。同年,他又擔任張元《北京雜種》的美術指導,“我清楚地記得臧天朔用鐵簸箕猛砸自己碩大頭顱的聲音,還有豹子般的竇唯……當然還有較勁的崔健”。
劉小東親歷并參與了這一代新人的“起事”,在藝術圈、電影圈、搖滾圈里廝混游走。他們糾合為一種力量,與那個年代的主流文化形成鮮明對照——拒絕寓言、崇高與大集體,回到邊緣、瑣碎與小個人。張元自白:“我每天都在注意身邊的事,稍遠一點我就看不到了。”王小帥表示:“拍這部電影(《冬春的日子》)就像寫我們自己的日記。”劉小東則說:“我越來越尊重現實,尊重生活,尊重那些有意思的和沒意思的個人生活。”
從這時開始,他畫中的“熟人”漸漸少了,開始把目光轉向紛繁的“眾生相”:《胖孫子》中的過肥男孩懶懶地倚著一輛嶄新的“寶馬”,《燒耗子》中兩個無所事事的青年以殘害生靈取樂,《違章》中的卡車上擠滿了臟兮兮的半裸民工……劉小東將這些無名無姓的小人物,定格在庸碌的日常狀態中——聚會、吃飯、郊游、喝酒、聊天、洗澡、睡覺,記錄下一個完整的社會文化現場。
“劉小東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們扔過來,真實極了。”陳丹青說。
給他們一些任何人都該有的尊嚴
在陳丹青看來,這些“生猛的作品”,全賴于劉小東“精準如射擊”一般地看:“唯動物如此兇狠而準確地看——那目標,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一回,他和劉小東出游京郊,中途停車,劉小東著急撒尿般奔向路邊,拍了幾個穿過田埂的村民,日后這張平淡無奇的照片就被植入到他的畫中。
《眼前往事》中的很多照片,都是劉小東作品的最初“底片”。“人的記憶力不可能記住每個細節,照片能凝固住那些細微的表情和狀態,以至一個門把手的光澤。”但對他來說,安身立命的仍是寫生,“照片只是個小小的平面,提供不了那么多空間和色彩的微妙變化;寫生完全憑你的肉眼,去感受這個世界的風吹雨打、陰天晴天,感受被畫者的氣息和現場突發的種種偶然。”
2002年,劉小東第一次到重慶奉節,彼時為了建三峽大壩,河床已經干枯,遠處就是已成廢墟的城市。回來后,他根據所拍照片,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完成了《三峽大移民》和《三峽新移民》,后者于2006年拍出2200萬元的天價,創下當時中國當代藝術的最高拍賣紀錄。
在北京展覽這兩幅畫時,劉小東請阿城寫點東西,“他吭哧吭哧在網上下載了整個三峽的歷史,將近10萬字”,寫了一篇《長江輯錄》。有感于阿城一絲不茍的態度,劉小東想再畫一回三峽,把畫室搬到現場——即將沒入水下的奉節老縣城中一座半毀的樓房頂上。“要克服文人的矯情,要真的像勞動人民一樣,真的去體驗。”
跟他一起去的還有賈樟柯。劉小東在畫布上創作《溫床》,他就在一邊用攝影機記錄。紀錄片《東》里,劉小東和民工們一樣光著膀子,畫他們或坐或臥地打撲克。2米多高、10米長的大畫布鋪在地上,他撅著屁股,像種地一樣,從中午畫到天黑,后背起包,嘴上長泡,“天天貼創可貼,不貼太惡心,貼了太難受”。
畫畫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工人死了,被正在拆除的樓骨架壓在了下面。劉小東帶著為他拍的幾張照片,回到他山村的老家。“試圖通過藝術改變什么,是很可笑的事情。”在影片中劉小東說,“但我希望通過我的繪畫,給他們一些任何人都該有的尊嚴。”《溫床》里的移民工仍將在各處需要廉價勞力的異地奔波,但那11副肌肉僨張、汗水津津的五短身材,卻被留在三峽山河的背景之上。
“在任何非常悲情、絕望的地方,你都會發現生命本身的動人。”三峽之后,現場寫生成為劉小東的主要工作方式。在泰國,他畫從事性工作的女孩;在青海,他畫戈壁灘上吐著濃煙的化工廠;在和田,他畫挖玉的人群,千瘡百孔的河道。
阿城說:“劉小東每到一個地方,待十天或者一天,馬上就能把那個地方的東西抓到了。”他說,這種對直感的抓取性,屬于薩滿的DNA。
金城小子的眼前往事
劉小東的老家東北,就是薩滿文化的興盛地,流風余韻不衰。2010年,馬不停蹄地走過很多地方后,劉小東回到了故鄉金城。
金城是東北的一個小鎮,曾擁有全國第四大造紙廠。上世紀90年代國營工廠改制,造紙廠瀕臨倒閉,如今再不見往日擠擠攘攘的工人,昔日的廠房被高樓、洗頭房、洗腳城、臺球廳淹沒。
1980年,劉小東17歲,離開金城去北京讀書,每逢春節回來一趟。這次回鄉,他頭一回在家里連續過了夏、秋、冬3個季節,每天和“發小們”踢球喝酒,請他們當模特,畫他們的臉、皮膚、各自的家庭,“為活過的幾十年留點證據”。
跟他一起來的,還有臺灣導演侯孝賢的拍攝團隊。頭一回來金城,侯孝賢卻涌起莫名的親切感,那些空曠的廠房與銹跡斑斑的小火車,讓他想起舊日的臺灣糖廠。紀錄片《金城小子》里有一幕,卡拉OK廳里,這邊是侯孝賢唱著臺語歌曲,那邊是“發小們”聲嘶力竭地吼著“你看吧這匹可憐的老馬”,劉小東則站在畫架前畫郭強——一個“身在黑道邊緣,心在嚴格律己”的KTV老板。
3個月里,他一共畫了8位這樣的“金城小子”:曾經入獄的樹軍抱著自己老來喜得的大胖兒子;下崗的旭子在家徒四壁的客廳里光著膀子露出文身;以前一起練武的小豆,穿著野性又敞亮的裙子站在臺球桌前,風情依舊……
在城市化、市場化的洪流里,金城成為一個被歷史遺忘的地方。劉小東在日記里寫:“我們的記憶被膨脹的發展吞食了。”無論是畫三峽還是畫金城,他關注的都是中國社會變遷的種種欲望、矛盾與毀滅,“一面是迅猛的發展,一面是舊有的生活,一切關系都被打碎”。
攝影集《眼前往事》里,有他拍的鄂爾多斯爛尾樓前漫步的驢,當“東方迪拜”淪為今日“鬼城”,“農業社會的痕跡遺留在現代化的城市里,像戰爭一樣彼此對峙”。“我趕上了這個時代,我就要去畫、去拍,就要在混亂復雜的現實里度我的生命。”
在北京待了30多年,“金城小子”劉小東依然有著清晰可辨的東北口音。那種地域性的幽默與爽直在他身上留下了極深的烙印,讀他畫畫余暇時記下的日記,總會被諸如“咋整的,每次出來畫畫都會長出嘴泡”“昨天已經聯系好的驢還沒來,我已等到三點,三點啊,三點了”這些話逗樂。
采訪時,一連串觀念、想法把他問得有點苦悶,“像接受靈魂的拷問,太累了”。錄音筆一關,他就馬上如釋重負,哼著歌,沏好茶,熱情地招呼著“聊點兒實在的”,聊北京的生活成本,聊青春的苦悶,聊平常心。“有一顆平常心不容易,多見一點世面,多見一些人,你對所有的事情就不會那么大驚小怪了。”
他的畫室正重新裝修,小院里堆著雜物,他指著一個角落,說那里落戶了一窩野貓,每天躥來躥去。
突然就想起阿城說劉小東的一段話:“他身上的動物性非常強,就像一個貓忽然就跑進來了,看這么多人在這兒,它馬上直覺到這里不一定危險,因為他們都在聽一個傻瓜在講話,所以不會注意到我。這就是動物,一瞬間它就掌握到這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