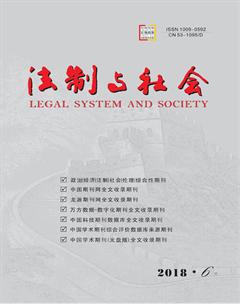淺談證人特權規則
黃藝 楊旭東
摘 要 證人特權規則是指證人在特定情況下能夠免除作證的義務。“證人特權”又稱為證人“豁免權”、“作證特免權”。證人享有“作證特權”的前提是具備證人資格和賦予其免除作證義務的特定情況。世界很多國家的法律都對證人免作證特權有明文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自2012年修改后,對拒絕作證權的適用有了明顯的進步。但就拒絕作證權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而言,我們還需要加強理論研究,以期在司法實踐過程中證據規則體系得以完善。
關鍵詞 拒絕作證權 “親親相為隱” 沉默權 刑事訴訟
作者簡介:黃藝、楊旭東,西北民族大學。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6.164
但凡知曉案件切實情況的人,都是證人,都有義務作證,這是當今各國廣泛適用的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此可見,證人作證的義務已經上升到法律層面,由法律對證人的作證義務加以規定。證人出庭作證具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是具有作證資格,也稱具有適格性,即證人必須是知曉案件切實狀況的人;二是具有可強迫性,依照《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證人有必須出庭作證的法定義務。由此,可強迫性的理解是證人出庭作證時,不得因出現特定的法定情形而免除作證義務。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必須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條件,證人的主體適格性和作證可強迫性并不互為前提,證人的主體適格性和作證可強迫性是橫向并列存在的,即具備證人適格性的主體,未必就一定可以強迫其出庭作證,二者不存在前后的必然聯系。證人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分別的兩個部分,“證人特權規則”就是證人適格性和可強迫性分開的表現。
一、證人特權規則的內容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明文規定證人具有作證義務,其第2款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這第2款的規定其實是一種不能作證的情形,這類主體或許是知曉案件狀況的人,但是基于其生理上、精神上的缺陷不能真實反映案件情況,不符合證據客觀性原則,故這類主體不具備法定的證人資格,但是并不妨礙我們將其推定為一種證人特權。現行有效的《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一條部分規定了證人的“免作證特權”,基于與被告人有特定身份關系而免于其法定作證義務。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當對某些問題的回答,將會對證人或證人的有關親屬引起不名譽或使其因犯罪或違警行為而有受追訴的危險時,該證人有權拒絕作證。”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80條也有類似的規定。諸如此類規范的還有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3款之規定。我們不難發現,當具有適格性的證人出現“特定情況”時,其作證義務得到免除,出現了“免作證特權”情形。不具有證人適格性的人當然不用作證,也就談不上“證人特權”。
證人特權的內容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 職業秘密特權
1.公務特權
證人有權就有關公務機密的證言不予回答。這主要指掌握國家秘密的公職人員和其他依職務掌握國家秘密并具有保密義務的工作人員。當這類人具有證人適格性的條件時,其作證的內容涉及國家秘密的部分應當不予作證,免除其作證義務。另外還有一類公職人員基于司法豁免權而免于出庭作證,即享有司法豁免權的外交人員,這是國際普遍使用的規則,其意義在于對國家主權的尊重。總的來說,在司法程序中,當證人掌握國家秘密或享有外交豁免權的時候,不得強制其出庭作證。
2.律師免證權
這主要是指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律師出于其職業的需求,對從當事人處取得的材料、證據信息等,不得強制其出庭作證。律師免證權主要在歐美國家較為普遍,英國證據法據對其有特別規定。我國對律師免證權的規定較少,在《律師行為規范》第56-59條作了律師具有保有委托人、代理人的商業秘密、隱私和其他信息的義務,對于其免于作證權沒有具體的規定。
3.醫生和患者之間的特權
這主要體現在民事訴訟活動中醫生對患者的個人隱私和信息具有保密義務。德國訴訟法典就規定醫務人 員在相關醫療救治過程中,對自己所知悉的相關事項能夠拒絕出庭提供證言。我們國家對此沒有詳細的規定,僅在執業醫師法中規定,醫師在執業過程中,泄露患者隱私造成嚴重后果的,給予警告或者停業,情節嚴重的吊銷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沒有規定醫生享有免于出庭作證的權利。
(二)親屬關系特權
“親親相為隱”的特權。指夫妻之間或者特定親等的親屬之間,不得就從對方獲知的信息作證或作出不利于對方的證言。“親親向為隱”又稱“親親得相首匿”。我國最早將“親親得相首匿”確定下來是在漢宣帝時期,主要內容為“卑幼藏匿有罪尊長,不追究刑事責任;尊長隱匿有罪卑幼,死罪上請廷尉決定是否追究罪責,死罪以下也不追究刑事責任。”這一刑法適用制度自漢代以后一直為后世歷代所沿用,始終作為中國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則。這種親屬之間藏匿犯罪不負刑事責任的準則,來源于孔子宣揚的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也是孔子“親親相隱,直在其中”的倫理觀念在法律中的直接體現。 “親親相為隱”更多的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思想,基于家庭或家族的特定倫理關系,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不強迫有親情關系的證人出庭作證,因為這有違綱常倫理,無論是對證人還是對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這都是違背其感情意愿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強迫證人出庭作證顯然是不合理的,法律應當對此加以特別規定。我國臺灣地區對有關親情關系的規定就特別能體現這種人文關懷。證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不作證:(1)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2)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3)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我國臺灣地區已經將這種具有親情關系的證人免于作證的特權范圍擴大到極為寬泛的地步。
相比較而言,大陸的《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的范圍就比較狹窄了,第188條規定證人無正當理由必須出庭作證且法院可強制其作證,但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面,人民法院能夠強行要求證人出庭作證,這合乎我國大陸《刑事訴訟法》第60條之證人具有作證義務的規定;另一方面,能夠看出我國大陸《刑事訴訟法》關于“證人特權規則”的完善,即對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作證豁免權的確定,很明顯地吸收了“親親相為隱”的思想。但只限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和子女享有免作證特權,與我國臺灣地區的親屬作證豁免權的親屬范圍相比確實狹窄,這還需要在我國大陸的司法實踐中進一步加以完善。
“親親相為隱”制度是一種合乎人性化的制度。將“親親相為隱”上升到立法,法律對親屬之間彼此藏匿包庇犯罪的行為減輕或免除處罰,這是一種人道主義關懷。社會生活以血緣為紐帶,以家庭為本位,國家如果強制我們在大義和親情之間做出選擇,這并不容易,如果選擇去揭發親人,雖維護了國家大義,但卻違背了親情綱常倫理。親屬之間的彼此藏匿包庇是合乎人性的。將“親親相為隱”上升到立法層面,體現了法律的人性化內涵,更加體現法的人道主義標準和要求,這代表著法律與人權的結合,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的建設,使人與社會更加和諧。
(三)其他類型的證人特權
1.拒絕自證其罪的特權
這是一種對證人的保護,即證人出庭作證,有可能使本人或本人親屬受影響甚至被要求承擔刑事責任或被判有罪時,就可以不出庭作證或部分免除其作證義務。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拒絕自證其罪”是被告人的一項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一條的意義在于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必須堅持“反對自證其罪原則”。在西方國家,反對自證其罪原則被稱為米蘭達告知規則,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警察提問時有權不予回答。這其實是一種沉默權制度,沉默權制度本質上就是“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體現。自證其罪是一種違反人類本性的體現,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自己證明自己有罪有悖于人的本性,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我們不能期待他人將自己置于一個危險的狀態下。法律也應當認可這種價值取向,法律是規范人的行為的規則,那么作為一部良法的話,就不得不體現出其人性化的一面,這個人性化可以解釋為人權。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表現了法律對人性對人權的維護。
2.宗教神職人員與懺悔者之間的特權
因為該職業比較特殊,故筆者將其作為其他類型的特權證人。這類證人特權主要是在西方國家有所體現。我國的民族政策與宗教政策相融合,情況相對較為復雜,對宗教人員的證人特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在此不作討論。歐美國家大多信仰基督教,宗教在西方社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神職人員因其職業性質的特殊性,在其作為證人時,應當給予特殊保護。在神職人員和懺悔者之間,基于人與人之間的信賴,神職人員有對懺悔者向其透露的秘密保密的義務。以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為例,神職人員對于在作為心靈感化時被信賴告知或者知悉的事項,有權拒絕作證。英國法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們不難發現,神職人員的證人特權多考慮的是宗教因素,在主要奉行宗教的國家,宗教作為一種信仰為世人所信賴,那么在訴訟活動中,我們就應當將這種人與宗教之間的關系考量進去,其表現的就是一種法與宗教、法與社會的和諧。
二、結語
證人特權規則,就是“以犧牲發現真實為代價,來換取法律所保護的更重要的法益”。這一規則充分考量了法律的實效性,更多的體現了法的價值的實現。證人特權實質上就是在兩個法益保護之間做出選擇,當證人特權所代表的法益價值高于發現真實所代表的法益價值時,犧牲發現真實的法益價值是有意義的。即維護知情人的實在利益比查明案件真相更有價值。因此,證人特權規則一旦在我國真正確立,這對我國訴訟體系的完善具有重大意義。
注釋:
曾憲義.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參考文獻:
[1]何家弘、張衛平.簡明證據法學(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2]王丹.論證人特權規則.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1.
[3]曹吉明.淺談對證人特權與豁免制度問題的思考.科技視界.2015.
[4]何家弘.中國式沉默權制度之我見——以“美國式”為參照.政法論壇.2013.
[5]曾憲義.證人特權規則探究.中國法制史.2008.
[6]柯葛壯.刑事訴訟比較.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