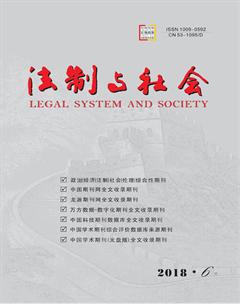網癮戒治機構的監管機制研究
摘 要 據統計,在中國約160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網絡成癮,其中400萬屬于深層網絡成癮。央視財經評論員劉戈曾說:“如果每個人沉迷網絡,父母花一萬元對他進行糾正,那就是400億。”近幾年來,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社會上各類網戒機構叢生,數量已達上百家。然而,這塊巨大的市場“蛋糕”管理重合,職能交叉,國家未指定專管的部門。在各類網戒中心里,最為知名的便是山東楊永信網癮戒治中心,其電擊療法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前年九月份網絡上流傳的一篇文章《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再次將其拉回公眾視線,而去年的豫章書院更是將網戒機構推到風口浪尖上。本文旨在運用相關的經濟法理論知識來研究建立統一的網戒市場監管體制,結合我國網癮戒治的消費體系和市場體系,借鑒國內外成熟經驗,解析網戒中心的法律性質以及建立網癮戒治中心監管體制的合理性、可行性,發揮其作為民間培訓機構的正面效應。
關鍵詞 網戒中心 網癮 監管 法律
基金項目:2016年西南政法大學學生科研創新項目資助 名稱:網癮戒治機構的監管機制研究——以楊永信網戒中心為例。(項目編號:2016XZXS—119)。
作者簡介:王笛冰,西南政法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學。
中圖分類號:D926.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6.196
一、網癮戒治機構存在理由及性質
(一)網癮戒除機構是疏導正確用網的必要機制
在互聯網與經濟生活深度融合的過程中,逐漸成長的直播平臺及資本追捧下的各類網絡項目,成為昔日被稱為“網癮少年”的群體謀生致富的手段,人們對待互聯網的態度日益開放。然而,并不是所有網絡使用者都能夠以此糊口發家,亦不保證所有使用者都能夠做到合理合法,過度用網、沉溺于網絡的現象依舊嚴重,網癮戒治機構作為一種社會自發形成的心理矯正的機制和民間力量,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
2017年《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20-29歲年齡的網民占比最高,達 29.7%,10-19 歲群體占別為19.4%。據中國青少年網絡協會及其他權威機構的報告,24歲及其以下的青少年網絡成癮綜合癥和嚴重的網癮傾向的人數約有1000萬。統計數據顯示,青少年網絡成癮已成為日益突出的心理,家庭和社會問題。針對以上問題,網癮戒治機構對網絡成癮的表現、防治進行了初步研究,找出了一套獨特而有爭議的網癮戒治模式。
(二)網癮戒治機構是一種“民辦培訓機構”
市場上的培訓機構命名各異,以“精神衛生中心”、“民辦學校”、“拓展項目”、“訓練營”居多,迄今為止,網絡成癮還沒有被權威機構正式確定為醫學疾病,而多數機構也未獲得教育部門承認的辦學資質。無論從市場主體、行為方式,還是經營模式、法律效果等要點,這些擁有不同外觀都具有“民辦培訓機構”這一本質。
但與此同時,這種民辦培訓機構還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2009,衛生部衛生防控部主任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衛生部沒有批準任何醫療機構治療網癮。”國家計委在2014年也說過:“我國還沒有批準任何醫療機構治療網癮。”然而,各種各樣的網絡成癮治療機構隨處可見。這些機構大多是商業或私人機構。主管部門為各類部門,社會培訓機構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審批,公司形式的教育培訓機構應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主管。一些機構沒有任何部門批準就開始招收學生。
二、網癮戒治機構提供產品時的行為邊界
(一)網癮戒治機構的權利
不少青少年都是因為學習障礙引發沉迷網絡的問題。網癮戒治機構可用軍事鍛煉和拓展訓練等方法作輔助治療,但是用藥一定要慎重,暴力一定要杜絕。戒治機構為達到戒除學員網癮,保證合同目標實現的目的可享有以下四項權利:(1)檢測學員身心狀態的權利。(2)要求學員配合的權利。(3)限制網絡使用權的權利。(4)學生終止合同的違約責任請求權。
(二)網癮戒治機構的義務
雖然沒有相關機構和法律法規將網絡成癮認定為一種“精神病”,但一些“網癮治療中心”卻將網絡成癮看作精神疾病來治療,引起了公眾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質疑。
山東省臨沂市第四醫院是臨沂精神病院的前身,是一家主要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該院網癮治療中心因“電擊療法”而聞名全國,這是由該中心負責人楊永信發明的。據精神科醫生介紹,在臨床醫學中,電刺激療法被用來治療嚴重的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癥和嚴重抑郁癥。然而,從目前來看“網絡成癮”并不屬于精神病范疇。
2009,媒體曝光楊永信的“電擊治療網癮”的方法后,衛生部立即將其叫停。但是對于經歷過“電擊療法”的孩子來說,這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無法抹去的陰影。
所以,為了避免上述狀況的出現,戒治機構為達到戒除學員網癮的同時應負有的四項義務:(1)保證當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義務,在戒治過程中要杜絕暴力,人體傷害等治療手段;(2)保障學員人格權的義務,必須要尊重學員們的人格發展;(3)保障學員活動自由的義務,不能限制學員們的生活自由;(4)尊重學員隨時解除合同的義務,不能使用非法手段強制學員進行治療。
上述權責關系就形成網癮戒治機構在提供服務產品時的行為邊界,超過邊界,行為皆有瑕疵,需要受到經濟法規制。
三、國家對網戒機構的監管
(一)國家監管的理論依據
經濟法調整對象有兩種類型。一是宏觀調控關系,二是市場調節關系。網癮戒治規制機制的完善便應該建立在經濟法的市場調節理論基礎之上。
(二)行政監管主體的確定
近幾年來,在市場利益的驅使下,社會上各類網戒機構叢生,數量已達上百家。然而,這塊巨大的市場“蛋糕”管理重合,職能交叉,問題不斷,國家未指定專管的部門。新聞出版總署、工商部門、消防部門,有衛生部門,公安部門都有法定范圍內的管理權限,網絡市場的多頭管理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監管部門的不作為。學歷教育機構的審批工作主要由教育部門管理。社會培訓機構應當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審批,公司形式的教育培訓機構應當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①在現有法律政策下應尋求以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為主導,多部門聯合執法,以解決網癮戒治機構的監管主體難題。
(三)立法建議的提出
早在2009年初,衛生部相關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便明確表示:“衛生部尚未批準專門從事網絡成癮治療的醫療機構。2014,國家衛生發展規劃委員會明確表示:“我國尚未批準專門從事網絡成癮治療的醫療機構。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精神障礙診斷標準。
此外,大多數網癮治療機構不是醫療機構,而是以“咨詢中心”和“成長學校”的名義存在于市場之中。對于網絡成癮的治療,法律或行業監管是空白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網癮戒治這個行業。我國應對網癮戒治市場必須進行規制,通過建立行業準入制度、設定行業資質認定標準等手段對其進行規范化管理
(四)國外經驗的借鑒
早在2003年,德國就開始網絡成癮的治療,通過繪畫、舞臺劇、合唱、游泳、騎馬、蒸汽浴等自然療法,來減少網絡成癮者對互聯網的關注。而美國則更側重于預防“網癮”,通過法律建立起互聯網分級制度,來減少未成年人對易上癮內容的接觸。
在網絡成癮的預防和治療中,我國應制定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專門法律法規,堅持預防為主,戒治為輔的思想。并從法律、技術、教育三個方面提出來形成網絡游戲分級管理體系。同時,應建立公益性基金,支持開展防成癮軟件研究和網絡成癮治療研究。此外,還應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提高未成年人正確使用互聯網的能力。
四、網癮戒治機構與消費者權益的救濟
(一)網癮戒治機構與消費者的關系
該部分將探討網癮戒治機構與消費者達成合同后,在履行合同時發生的侵權行為的原因、類型、特點和后果。而作為消費者的學員,在網癮戒治機構面前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常被強調“服從”與“遵守”的義務,更容易成為侵權行為的受害者,因此消費者權益救濟方式的探討是本章節重點。作為弱勢一方,如何保證自我權益不受侵害,我們應從以下幾點出發:(1)設立投訴監督機制,當消費者在戒治過程中受到身體上的創傷時,有權撥打投訴電話,監督機制應積極下派人員進行調查;(2)完善監控設備體系,在日常課堂以及生活區進行監控管理,避免治療機構出現暴力體罰消費者現象;(3)建設網癮戒治機構備案,對出現體罰、暴力對待學員的機構進行嚴重處罰,吊銷其繼續經營的執證,列入黑名單。(4)建設流動人員監督機制,對所有的網癮戒治機構進行監督,下派工作人員進行不定期視察,對不法機構形成威懾。
(二)消費者面對侵害的救濟
作為典型案例,楊永信采用了電擊、捆綁、限制個人自由和建立權威等方法來“治療”網癮。未經允許學生不得擅自離開醫院。即使網癮被戒除,學員若出現了“復發”仍需要回到網癮戒治中心繼續接受“復查”和“治療”。然而,多年來,侵犯學員人身權利的網癮中心仍在招生,人們發現楊永信的電擊治療“網癮”仍在繼續,全國類似的網癮戒仍在使用體罰等暴力手段來“治療”、“網癮患者”。在受到“暴力戒網”機構的人身侵犯時,學員要學會用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條: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制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檢舉或者控告。果斷求助于公安部門與法院,依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及時終止與網戒中心的合同。為了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網絡而對其使用暴力的行為,如人身自由、體罰、責罵、禁食等,已經超越了法律規定的方式,且侵犯了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權等民事權益,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禁止虐待未成年人的規定。父母身為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可以在收集證據的前提下追究這些機構的法律責任。
注釋:
①高海麗.青少年網絡成癮對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麗水學院學報.2008,30(1).88-90.
參考文獻:
[1]楊永信.用“心”戒網癮.科學出版社.2011.
[2]楊永信.網癮的是與非.科學出版社.2015.
[3]閭丘露薇.誰給他電擊的權力.中國社會保障.2009(7).
[4]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課題組.關于未成年人網絡成癮狀況及對策的調查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