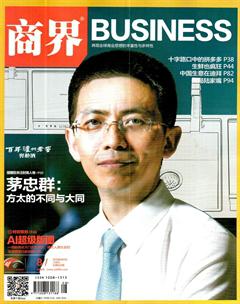玩具大王的致命游戲
陳江婷
奧飛動漫進軍兒童智能玩具市場,戰略投資法國藍蛙、圖靈機器人公司;驊威文化由玩具到游戲和影視的“泛文娛”公司轉型,玩具業務收入只占總營收的15%以下。從這些玩具公司的身上,甚至看不到太多關于玩具的影子。
2010年以后,玩具的智能化發展成為行業趨勢,并且大多與動漫、電影、游戲等相關。在這波浪潮中,有些企業順勢而起,有些只能關門大吉,而曾經有著先發優勢的群興玩具,營收慘淡,遠落人后。
這家市值曾達到22億元的上市公司,在經歷了4次并購重組后,2018年宣布關停玩具生產,員工也從原來的1000多人,到現在的只剩不到30人。
在消費升級與二孩政策的利好刺激下,玩具行業正在迎來新的“生機”。群興玩具這個曾經的“行業大佬”,卻在一個仍有增長空間的領域內,走向沒落。
群興玩具究竟做錯了什么?
以不變應萬變
2011年4月30目的上市答謝宴上。群興玩具創始人林偉章和黃仕群,頻頻向現場來賓祝酒,《好日子》《明天會更好》等喜慶歌曲一首接一首。作為汕頭澄海率先上市的幾家玩具企業之一,林偉章與黃仕群意氣風發、壯志滿懷。
殊不知,觥籌交錯之際,玩具行業已是暗流洶涌。
汕頭澄海,被稱為“中國玩具禮品城”,這里有奧飛、驊威、星輝等上百家玩具企業。在澄海小城里,群興玩具稱得上是明星企業,它專注于玩具童車生產,并且在這個垂直細分領域中拔得頭籌,獲得“玩具童車大王”的稱號。
群興玩具的創始人林偉章,也是身兼多職。中國玩具協會常務理事、廣東省玩具協會常務理事、澄海玩具協會副會長,履歷中“具備20多年玩具行業從業經驗”一條,更是足以證明他在玩具行業里的大佬地位。
但事實上,玩具行業20多年來的緩慢變化,反而讓林偉章在面對新時代快速激烈的動蕩時,有些固步自封。
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玩具出口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國際市場對中國大量出口玩具感到緊張。設置了眾多的貿易壁壘;另一方面是中國的玩具產業處于國際產業鏈的末端,附加值低,加上上游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上漲,都讓玩具產品很難再靠低價贏得市場。對于多數依靠出口的澄海玩具企業來說。這無疑是雙重打擊。
林偉章不是不知道行業發生了什么。但2012年群興玩具5.05億元的營收,讓他志得意滿。他覺得公司營收可觀,行業寒冬也并沒有真正到來,只要按兵不動,過段時日行業一定會重新步上正軌。
恰恰,這成為了群興玩具走向沒落的開始。
2013年,奧飛已經“嗅”到了行業動向,推出了與動漫片相關的主題玩具“悠悠球”,年銷售額1億多元。而林偉章還是做著童車玩具加工出口生意,下滑的業績,并沒有給公司運營帶來太大的影響,當然也撼動不了林偉章等待行業“復蘇”的心。但他忘記了,即使春天會到來,冬天也不能不做任何的防護準備。
決策者可以“以不變應萬變”,但對于行業的變化絕對不能麻木,一定要有所思考并且給出相應的“備用方案”,才能在面對發展大勢的時候不至于失去方向。
并購并不夠
林偉章有“備用方案”嗎?顯然沒有。
2014年,隨著《歐盟玩具新指令》的出臺,進入國外市場的“門檻費”越來越高了。很多中國玩具出口企業,需要加大在生產設備與管理方面的投入,利潤微薄,這讓一些企業直接選擇關門大吉,另外的企業選擇出口轉內銷或者進軍非洲等其他新興市場。
主業萎靡不振、利潤連年減少,林偉章當時是如何的焦慮,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明顯意識到,企業轉型勢在必行。可是怎么轉?
彼時的奧飛,已經走出了一條“動漫+玩具”的發展路徑,自己投錢拍動畫片,然后推出周邊,四驅車、悠悠球、陀螺等玩具。林偉章可以怎么做?復制奧飛的成功模式并不容易,動畫片的制作需要時間與成本,也不一定會成功,那試試與別人合作,如何?
由此,群興玩具踏上了并購重組之路。
2014年7月,群興玩具公告稱,宣布收購藝動娛樂母公司星創互聯。這是一家以開發《全民英雄》手游產品出名的公司。林偉章想通過“手游+玩具”的模式,來開啟轉型之路。但是,先不談發展方式。這次收購本身就“迷霧重重”。
林偉章擬購買星創互聯100%的股權,當時計劃交易總額為14A億元。可是星創互聯是一個連年虧損的企業,賬面價值也只有不到1個億,這樣的企業,林偉章為什么要收購它?這樣反常的行為也立馬引來監管審查,2014年11月,這個收購重組方案因為標的公司盈利能力不足被否決。
坊間傳聞,林偉章此舉是為了套現。不論真假,這個曾經有著“汕頭市人大代表”頭銜的企業家,公眾形象似乎有些“變味”。林偉章的第一次并購,也以失敗告終。
如果說,林偉章第一次的并購重組,還是在學習他人模式,渴望找到新的發展路徑,那么他的第二次并購重組,或許就是“病急亂投醫”。
花16億元收購“核電+軍工”概念企業三洲核能,不僅與玩具主業毫無關系,而且重組標的公司中有一家中國核動力設計研究院。按照相關規定,中國核動力要完成股權交易,需要財政部審批,程序繁瑣且難度大。所以重組方案2個月后就宣布“流產”。這一次的并購重組,比起第一次,甚至找不出任何的理由。
林偉章想要以并購重組的方式,引入優質資本,這樣的做法或許并沒有錯。但是在自身沒有形成品牌的基礎上,將轉型的動力“掛靠”在別人身上,這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沒有獨特的玩具文化,也沒有品牌影響力的玩具企業,終究只是一個玩具加工廠的角色。在這個角色之中,勞動力價格、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人民幣的升值等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生死”。
并購重組,應該是為了擺脫這樣的一種“人設”,降低對外國市場的依賴,形成自有品牌。而林偉章盲目花費時間在并購重組上,甚至不管玩具主業的情況,結局定然是丟了西瓜又丟了芝麻。
入了資本的套
群興還沒有“玩”完,林偉章也沒有停止并購重組的步伐,只是這一次,他將主業丟得更加徹底,甚至連自己都“出局”了。
2016年6月。面對呈斷崖式下跌的業績,群興玩具實行董事會改選,原來的董事會7人包括林偉章、黃仕群等創始人,沒有一個出現在董事會候選人員名單里,這是怎么回事?
面對外界的諸多猜測,群興玩具發布公告稱:受玩具市場需求飽和、無序競爭加劇、技術更新加快、家族企業效率下滑等多種因素影響,公司近3年營業收入均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產品利潤空間受到擠壓。新一屆董事會成員之所以全部改選,是因為公司控股股東和原董事會均意識到,玩具產業的轉型升級和第二主業的選擇擴展均需要具有相應素質、能力、視野、格局的專業人才來決策和執行。
或許連林偉章自己也不愿意承認企業的失敗,但聘請專業的人才也是合情合理。不知當時林偉章是以怎么樣的心情“退居幕后”。可此時此舉,更像是他對群興玩具的一種“放棄”。
林偉章找的“專業人才”,就是紀曉文,曾經擔任瑞茂通供應鏈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惠程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但顯然,他對玩具行業并不熟悉。果不其然紀曉文在出任董事長一職后,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資本運作上。
他發起了群興玩具的第三次重組。擬通過發行股份的方式以29億元的價格收購時空能源100%的股權,并擬募集配套資金不超過10億元,用于年產3GWH電動車用動力電池組建設項目和伊卡新能源電動車用動力電池組研發中心項目。公告發布后,群興玩具股票暴漲,股東卻借此減持。
當運作資本在公司存亡中扮演了太過重要的角色,同時主營業務又陷入泥沼,那么企業就像無根之木,必然無法更好地發展。
半年后,群興的第三次重組也宣布終止。在12月的時候,群興更是拋出公告停牌重組,擬轉讓53.02%股權,受讓方將成為公司控股股東,相當于“賣殼上市”。
2017年,群興玩具營收成0;2018年,員工人數只剩不到30人,并且這些人里面,沒有一個玩具生產人員。上市7年,一家玩具公司卻無人生產玩具,這何嘗不是一種諷刺。
自從董事會改選之后,林偉章就此消失在“江湖”之中。管理層的重組故事,在投資者的眼中,已然成了一種“忽悠”。群興玩具,這次可能真的“玩完”了。
這7年里。林偉章看似花了大把的時間尋求轉型,努力找到發展的新路徑,但卻將最根本的主營業務丟棄。如果一切能重來。林偉章還是做他的“童車玩具大王”,從內部驅動轉型升級,群興的結局或許就會不同。
可是,現實沒有“如果”,在玩具行業浪潮翻涌之時,那條叫作“品牌化”的船,林偉章從一開始就沒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