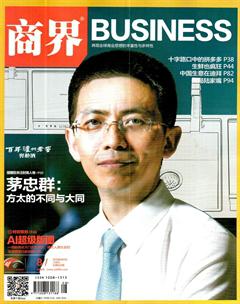為廣告找魂
楊紅艷
世界杯帶來的不僅是全球各地球迷的狂歡,還有各大品牌的廣告狂歡。馬蜂窩、知乎、BOSS直聘的洗腦、卡屏廣告在此期間瘋狂刷屏,引發了輿論的熱議。
而6月底剛結束的“廣告界奧斯卡”戛納國際創意節,則顯得格外冷清。不但今年的參與人數下降超過20%,報獎的創意廣告作品也減少了8798件。以寶潔、聯合利華為代表的廣告金主更是紛紛削減了廣告預算。
為了獲得消費者和品牌的青睞,廣告公司通常運用流量、大數據等工具讓廣告產生意想不到的商業效果。但一味依賴工具卻又容易讓廣告人陷入到創作的誤區。當一切方法開始逐漸失靈,創意需要回到“C位”。
流量是把雙刃劍
案例:名模Kendall Jenner主演的百事可樂廣告于2017年4月4日上線,但不到一天時間就被百事可樂公司撤下。原因在于對美國民眾而言,無法接受由一位時尚、娛樂化的真人秀式明星擔起如此嚴肅、敏感的政治“重任”。
誤區:流量至上。
理想狀態:利用擁有龐大粉絲群的明星和KOL引爆熱度,為品牌導入流量,進而實現商業變現。
事實情況:流量是一條能讓品牌大熱的捷徑,其快速、廣泛的影響力的確讓人嘖嘖稱奇。但是,這條捷徑帶有風險。雖然流量能讓消費者在短期內關注品牌,倒將其注意力實現長期的留存,才是形成商業變現的關鍵。
并且,一旦流量本身出現差錯,過于依賴于此的廣告公司就會付出更大的成本去解決相應的問題。正如凱絡中國的CEO侯靜雯所言:“只有創意能讓流量變得有影響力,不然流量就是烏合之眾。”
數據淪為背景音
案例:2017年3月,百事、沃爾瑪、星巴克等公司紛紛從YouTube上撤下了廣告,就是因為擔心上面的負面內容影響到品牌的形象。
誤區:癡迷數據。
理想狀態:通過大數據分析實現受眾的精準定位,以便廣告發揮更大的效用。
事實情況:讓數據分析為廣告服務,本能起到錦上添花的效果,但廣告公司過度癡迷于此容易形成畸形的生態系統。互聯網時代,數據信息的收集不是難事,但如何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并使其變得有效,成為廣告公司必須考慮的問題。
同時,在政府加強對網絡數據運用監管的背景下,大眾也逐漸提高了信息安全保護意識。道德規范、數據審查等問題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廣告公司考慮,這也意味著廣告公司在利用數據分析時會付出更高的人力與技術成本。
有話題不代表有出路
案例:在奧迪二手車2017年7月推出的廣告中,婆婆通過捏鼻子、揪嘴唇等“粗暴”的方式檢查兒媳,引發網友質疑其將女性物化。風波過后,奧迪被迫撤下了該廣告,并在其官方微信公號上發出致歉信。針對“女性”“婚姻”這類在國內比較敏感的話題,奧迪這次明顯是玩過了火。
誤區:濫用社會話題。
理想狀態:結合爭議性的話題,擊穿復雜的數字媒介和行業競爭,贏得寶貴的關注。
事實情況:廣告曾經構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如今,失聲的廣告遠離了文化,只能拼命向大眾流行的話題靠攏。社會話題,幾乎成了消費主義時代下廣告業的一針強心劑。
雖然將社會議題結合到廣告之中能為品牌創造熱度,博得大眾的熱議;但對品牌而言更為重要的是,要實現產品的商業價值。廣告公司在創造優質內容的基礎上,再適當結合社會話題來塑造品牌形象,才能進而推動具體的商業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