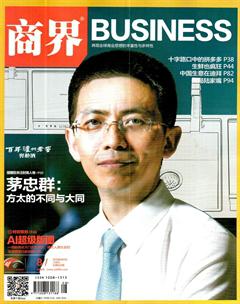央行與財政部的根本分歧在于地方債務
楊業(yè)偉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與一位署名“青尺”并供職于財政系統的作者,就財政政策的積極性展開了辯論。雙方觀點鮮明且對立,顯示了兩種不同的政策選擇方向,引發(fā)了廣泛的關注與熱議。我們暫且以“央行先生”與“財政先生”來代表這兩類觀點的持有者。
國際上,小型經濟體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制定部門大多意見統一。但在傳統貨幣政策失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部門要保障金融穩(wěn)定,往往需要求助于財政政策。這一時期,大國內部的貨幣和財政部門極容易發(fā)生分歧。
目前,我國央行與財政的根本分歧在于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從“央行先生”和“財政先生”的辯論來看,在財政政策發(fā)力和增加財政對金融機構注資方面,兩者沒有本質分歧;差異僅在于實現方式層面,因此通過協商可以達成一致。更為本質的分歧在于處理地方政府債務的方式,特別是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出于防范潛在財政風險的考慮,財政部門主張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剝離隱性債務。這也是控杠桿在政府債務部門的具體體現。
控杠桿背景下。地方政府債務和房地產融資受到了嚴格限制;而作為實體經濟兩個主要的融資主體,它們的融資受限意味著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投放資金渠道不暢。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不暢則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發(fā)力空間,央行即使放松貨幣政策。也只能導致資金堆積在銀行間市場,難以有效地流入實體經濟。
2018年4月以來,央行2次降準,也僅僅推動銀行間流動性變得寬松,并未顯著改善實體融資。在貨幣政策失效的情況下'央行不得不訴諸財政政策。“央行先生”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呼吁財政政策加大寬松力度;“財政先生”事實上也并不反對財政寬松,只是在“寬松方式”上與之存在差異,但這種分歧并非不可彌合。兩者本質的分歧,表現在對地方政府債務的態(tài)度上。
我國經濟中存在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為代表的重要主體,它們享有地方政府隱性擔保,但卻是企業(yè)屬性,其經營并未納入政府預算。這類主體權責界定并不清晰,導致其融資時實際享有政府隱性擔保,但政府是否真正提供擔保卻具有不確定性。
特別是在大環(huán)境不好的時期,由于融資平臺自身償債能力較差,這種政府擔保的不確定性風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影響。如果財政不承擔這部分債務,勢必會導致金融機構壞賬攀升,信用風險劇烈上升。但如果財政承擔了這部分債務,則會增加未來地方政府融資泛濫的風險,敗壞財政紀律。
所以“央行先生”認為整頓地方政府債務不能一推了之,應著力避免財政風險金融化,不搞“一刀切”。而“財政先生”卻認為真正需要注意的,是站在金融機構立場上,以防范金融風險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對不該擔保或救助的隱性債務提供保護。
對控杠桿成本的承擔是他們的另一分歧。控杠桿要求控制或降低實體經濟杠桿率,這一方面要求壓縮債務,另一方面要求充實資本。年初以來表外融資劇烈收縮顯示債務已經明顯壓縮,而債轉股等政策的推行則是重要的充實資本措施。
但這些措施,都面臨金融機構資本金不足的約束。金融機構需要大量補充資本金,因此“央行先生”指出,在金融去杠桿背景下,國有金融機構資本不足的問題凸顯,應當以財政資金向國有金融機構注資。對此,“財政先生”并未顯示強烈反對態(tài)度。在這方面,兩者依然具有協商達成一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