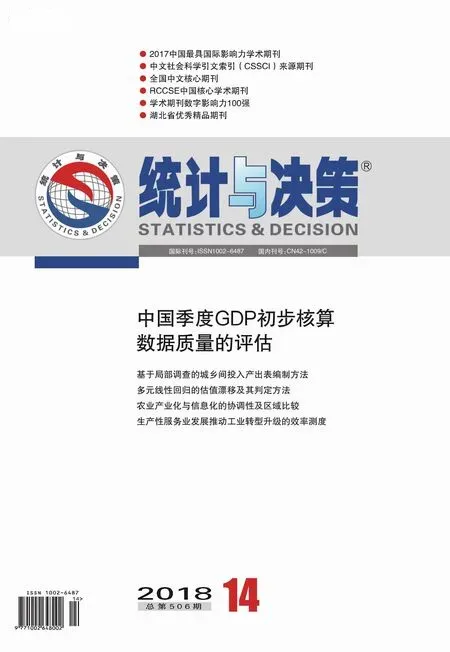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物價傳遞效應的統計考察
史新鷺,周正寧
(西安交通大學 金禾經濟研究中心,西安 710049)
0 引言
匯率傳遞通常被定義為匯率變動所引起的一國進出口商品以目的地貨幣計價的價格變化程度[1]。實際上,不僅對外貿易收支情況會受到匯率傳遞效應的影響,一國央行應對通脹的貨幣政策效力同樣也會受其影響[2-4]。保持國內物價穩定始終是一項重要的政策目標,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傳遞效應直接影響一國治理通貨膨脹的空間和自由度。到目前為止,只有較少數文獻以匯率變動對物價水平的傳遞效應作為研究對象,而其他文獻大都集中于研究匯率變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傳遞效應。但一般物價與一國經濟狀況的相關性更為直接和密切,目前許多國家都是以物價穩定作為首要政策目標,因此,研究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傳遞效應更具現實意義。考慮到實際匯率會通過影響國內外的相對價格而對一國物價產生作用,因此,本文將分析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5]對一般物價的傳遞效應。
1 理論模型構建
首先需要構建一個開放經濟菲利普斯曲線模型。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較高,本文設定廠商在生產過程中還需要投入能源要素,此時決定生產成本Cit的不僅是產量Yit,還有能源相對價格Zt/Pt。為簡化起見,這里參照Takhtamanova(2010)[6]對預期實際匯率變動過程的設定:Et-1qt=qt-1,即預期實際匯率過程是一個隨機游走過程。本文也假定預期能源相對價格遵循這樣一個隨機游走過程。
以外國廠商的最優決策為例來進行說明。假設每一個廠商只生產一種商品,其中外國廠商i的名義收入為(Yit是實際產出,是以本幣表示的外國廠商i所生產的商品價格),外國廠商i所面臨的名義成本為(P*是以外幣表示的外國總價格水平,Dit是外國廠商i的實際成本,)為間接名義匯率,則將外國廠商i的名義成本轉化為以本幣表示的成本就是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所示的外國廠商i的名義利潤:本文把實際匯率定義為,將其代入外國廠商i的名義利潤表達式可以得到相應的實際利潤:


設本國消費者對外國廠商i所生產的商品需求取決于其產品的相對價格以及本國的實際收入水平Yt,
其中,需求彈性記為ε(ε>1),則有:

此外,設實際成本為能源相對價格Zt/Pt以及產出Yit的增函數,其中,成本彈性分別記為γ(γ>1),η(η>0),則有:


其中,k1=(γ-1)/[ε(γ-1)+1],k2=(γ-1)/[ε(γ-1)+1],k3=η/[ε(γ-1)+1]。可以看到,最優定價與總產出、總價格以及能源價格正相關;最優定價隨著本幣的貶值而上升,其原因在于,本幣貶值的作用相當于提高了外國廠商的生產成本,因此會推動價格上漲。
由于是對稱模型,通過類似的推導可以得到本國廠商的最優定價:

對于每一期都能調整價格的廠商,稱之為“彈性定價廠商”,在本文的模型中,外國和本國這類廠商的占比都為δ;而不能隨時調價的廠商,稱之為“固定價格廠商”,這類廠商需要提前一期將價格設定為預期最優,在本文的模型中,外國和本國這類廠商的占比都為1-δ。在這種假設之下,可以得到外國商品總價格指數:

借助于對稱模型的便利,對應地可以得到本國商品總價格指數:

將外國廠商的最優定價(式(5))和本國廠商的最優定價(式(6))分別代入外國和本國商品總價格指數表達式(式(7)和式(8)),可以得到相應的國內總價格指數和國外總價格指數,并將其代入本國加權總價格指數表達式(式(9))即可得到如下的通貨膨脹表達式:

為得到本文最終所需要的開放經濟菲利普斯曲線,本文參考Takhtamanova(2010)[6]對式(10)進行進一步處理,假設預期通脹是央行所設的通脹目標與預期形成時的通脹率之間的加權平均,即將其代入式(10)并進一步簡化即可得到式(11):

從式(11)可以看出,實際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傳遞系數是-μδk2/(1-δ),由此可知,有四個因素會影響到匯率傳遞效應:其一是進口品在一國消費籃子中所占的比重,它衡量的是一國的貿易依存度,貿易依存度越高,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影響就越大,在本文的理論模型中,匯率是通過進口品這一渠道對國內物價產生影響;其二是彈性定價廠商所占的比重,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影響會隨著彈性定價廠商占比的增加而增加,其原因在于彈性定價廠商在面對匯率變動沖擊時,為了避免損失,這類廠商能夠及時對其定價做出相應調整,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傳遞率將隨著這類廠商占比的增加而增加;最后兩個影響因素分別是成本彈性和需求彈性,廠商壟斷勢力會因為這兩種彈性的增加而減弱,反映到物價上就表現為匯率傳遞率的下降。

進一步設定進口品在本國的消費籃子中所占的比例為μ,則可以得到相應的加權總價格指數:
2 計量模型和數據說明
2.1 計量模型與方法
本文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是前文理論模型中所推導出的開放經濟菲利普斯曲線方程式(11),根據式(11)可以

式(12)中的所有變量都是取過對數后的形式。其中πt為通貨膨脹率,為產出缺口(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差值),qt為實際匯率,zt為能源價格。
通過對模型(12)進行實證分析,可以得到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傳遞效應,即以β3衡量的短期匯率傳遞率。
在考察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傳遞趨勢問題時,本文采用滾動回歸分析方法,通過設定回歸模型的窗寬,獲得不同時期系統參數的變化狀況,具體的操作和分析在STATA11中進行。
2.2 數據說明
受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1994年1月到2015年1月的月度數據作為分析樣本,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國際清算銀行以及國家統計局。
所涉及的數據有通貨膨脹率、實際有效匯率以及產出缺口。其中產出缺口的月度數據是參考Tang(2014)[7]中的作法將季度名義GDP數據降頻獲得的,具體來說就是將季度數據均分三份,相應的月度數據就是對應季度數據的1/3。圖1是季度GDP經過H-P濾波處理后的產出缺口。得到如下的實證模型:

圖1 HP濾波處理后的產出缺口
本文采用的實際有效匯率(REER)來自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寬口徑指數(broad)。通貨膨脹率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變動率,即其中P為固定基期的CPI價格指數(2010=100)。
2.3 數據處理
首先需要對所有數據進行季節性調整,然后進一步對季節性調整后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為了得到更加可靠的檢驗結果,本文在估計時采用Newey-West異方差和自相關一致的協方差計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有關變量進行單位根檢定。從下頁表1可以看出,盡管原序列的檢驗結果都不能拒絕單位根的存在,但是一階差分后的序列都通過了單位根檢定。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物價水平的傳遞效應
通過對模型(12)進行回歸分析,可以得到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傳遞效應,表2展示了相應的計量結果。可以看到,只有產出缺口對通脹率影響很小,而其余變量對通脹率都有顯著影響。從這里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物價的傳遞是不完全的,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化一個單位,物價變化0.129個單位。

表1 各變量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2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物價的傳遞效應
根據前文理論模型部分的分析可知,在本國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匯率升值會使以本幣表示的來自外國的進口品價格下降,從而加權總價格也將隨之下降,這樣就會引起本國國內發生通貨緊縮現象。但是,表2的實證結果卻顯示,匯率升值會導致國內物價上升。究其原因,可能是樣本期內人民幣升值預期引起大量熱錢涌入國內,導致物價上升幅度遠超從進口品價格角度衡量的物價下降幅度。自從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與物價上揚的現象長期并存,該有悖于經濟規律的“雙高”現象一度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重點課題,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實際上,如果一國匯率升值預期存在,且其資本賬戶又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則此時一國國內就會涌入大量的熱錢。為了將匯率變化維持在特定范圍之內,一國央行通常就會進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外幣的操作,而央行的這一操作就會使大量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進市場,進而造成國內一定的通脹壓力。因此,本文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對以往“升值抑脹論”觀點的進一步質疑,針對這個問題,本文認為對于資本市場的監管應該繼續加強,防范匯率預期所造成的國際資本流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
3.2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物價的傳遞趨勢及決定因素
如前所述,近年來的實證研究表明匯率傳遞呈逐年下降趨勢,而且國外的學者大多將此現象歸結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成功地減小了公眾的通脹預期,即該下降趨勢與央行的貨幣政策密不可分。本文將主要分析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傳遞效應的變化情況,考察其是否存在下降趨勢,并分析其背后的決定因素。
本文在開放經濟菲利普斯曲線框架下,運用滾動回歸法分析了1994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間匯率傳遞率的動態變化趨勢。以往傳統的計量模型中,系統參數通常都會被設定為固定常數,但實際上系統參數會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呈現出動態的變化過程。而經濟系統的動態演變過程可以借助滾動回歸估計方法進行有效分析,具體來說,該方法在分析過程中需要設定回歸模型的窗寬,通過對窗寬進行設置就可以分析不同時期系統參數的變化情況。比起一般靜態回歸分析,滾動回歸的優勢是其能夠對系數的動態變化過程有一個清晰地把握。這里將滾動回歸樣本的窗寬設為5年(由于使用的是月度數據,所以窗寬實際上為60),樣本為1994M1—2015M1的月度數據,滾動回歸估計的結果見圖2。

圖2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傳遞趨勢圖
圖2(a)為匯率傳遞趨勢圖,可以看出,匯率變動的傳遞效應并不存在持續的下降趨勢,而是呈現出時升時降的狀態。在2000年以前匯率傳遞率大體上是逐年下降的,在2000—2005年間內呈大致上升趨勢,隨后在2005—2009年間又大致呈現出下降趨勢,此后較為平穩,近期又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另外,由于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能源變量,因此,這里也對能源價格系數進行了滾動回歸分析,如圖2(b)所示。可以看出,從90年代到現在,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國內物價受能源價格的影響也進一步加深。
由于彈性調價廠商的占比以及需求彈性和成本彈性無法準確衡量,因此,本文主要是從消費籃子中進口品的比重以及國內通脹環境兩個方面對圖2(a)所呈現的匯率傳遞動態趨勢進行解釋。
首先,匯率傳遞效應與通脹環境之間的關系。樣本期內的通貨膨脹如圖3所示,除了2000年以前及近期呈現的通貨膨脹下降階段與圖2(a)中匯率傳遞效應的下降階段吻合之外,其他時間段均難以相互匹配和對應,因此,總體來看,樣本期間內人民幣實際匯率傳遞系數大小與CPI通脹率之間的關系并不能完全支持Taylor(2000)[2]的研究結論。
其次,匯率傳遞效應與進口品比重之間的關系。從前文的理論模型中可知,一國消費籃子中進口品比重是影響匯率傳遞大小的因素之一,這里采用進口占GDP的比重作為消費籃子中進口品比重的替代變量。該變量在樣本期內的變動情況如圖4所示。

圖3中國CPI通貨膨脹率(定基比)

圖4進口占GDP的比重
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進口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與圖2(a)中匯率傳遞率的下降階段吻合,這也符合之前的理論結果。此后,在2000—2005年左右的時間段內,進口占GDP的比重呈上升階段,圖2(a)中的匯率傳遞率也在這一階段呈現上升趨勢。并且2005—2009年這段時間內,匯率傳遞率與進口占GDP的比重也同時呈現下降趨勢。
另外,通過考察這兩組序列的相關性發現,匯率傳遞率與進口占比之間的相關性為0.78,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從而進一步印證了理論模型的結論,即一國消費籃子中進口品的比重是影響匯率傳遞效應的重要因素,貿易依存度越高,物價受匯率變動的影響就越大,匯率傳遞效應就越顯著。
4 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一個開放經濟菲利普斯曲線,考察了1994年1月至2015年1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我國物價的傳遞效應,發現匯率傳遞的動態表現與進口品比重的動態表現一致,當進口品比重下降時,匯率傳遞效應也相應呈下降趨勢,而當進口品比重上升時,匯率傳遞效應也相應呈上升趨勢。與此同時,本文發現除了2000年以前匯率傳遞的下降階段與通貨膨脹的下降階段吻合之外,其他時間段均難以對應和匹配,總體來看,樣本期內的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與CPI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從穩定物價的角度來講,適當地降低貿易依存度,可以減少匯率對國內物價的影響,從而為央行制定穩定物價的政策提供更多的空間和自由度。同時也可以將經濟增長的視角從依賴外部轉向考慮國內經濟,從而有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