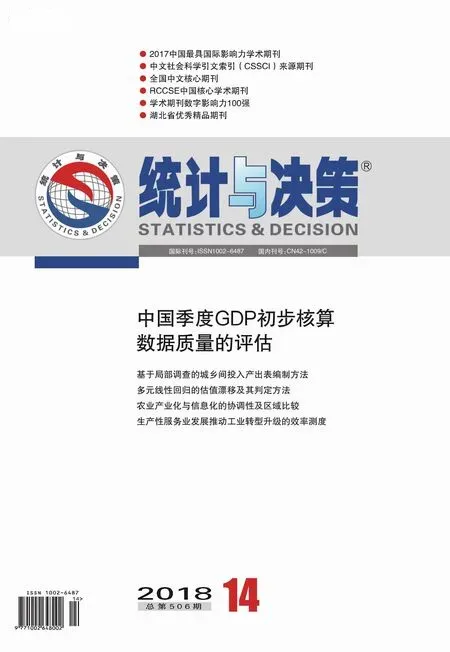資源稅對區域經濟與環境保護影響的實證分析
薛 鋼,李尚遠,陳婕瑤
(1.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財政稅務學院,武漢430073;2.卡迪夫大學 商學院,英國 威爾士CF14 3UU)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資源的過度消耗與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反映了各項經濟指標的上升是有代價的。不合理地開采與過度浪費資源不僅降低了資源儲備量,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還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作為調節資源消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資源稅在調節經濟增長、維護生態環境穩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現有研究缺乏針對不同地區具體情況的對比分析,難以全面反映區域間的差異問題[1,2]。我國對于資源稅的實證研究也基本上都是圍繞資源稅改革展開[3-5],但關于我國資源稅改革對環境保護的效應如何尚無定論。因此,本文針對以往研究的不足,借鑒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的研究框架,利用2006—2015年29個省級行政單位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對我國不同地區資源稅對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作用進行量化分析。
1 理論分析與模型設計
1.1 理論分析
本文模型設計原理主要參考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且生產要素的投入量與產出水平呈正相關關系,而主要依賴于科技創新與進步的生產要素效率對于經濟增長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影響。由此可見,稅收可以通過影響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而改變企業的決策,是政府用以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工具。通過合理的稅制設計,政府可以實現對經濟的有效調控。與此同時,政府可以將征收的稅收收入用于公共財政支出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例如環境污染)。這不僅提高了社會福利,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維護社會公平,也能提高消費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本文主要考慮資源稅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影響。征收資源稅一方面會直接導致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從而減少資源的使用,使產量下降,抑制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合理的稅收負擔可以促使企業通過改進自身技術以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促進經濟增長,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環境污染。此外,政府也可以利用資源稅收入,加大生態補償力度,增加社會福利,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增加對環境的保護力度。因此,從理論上分析,提高資源稅負擔水平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對于環境保護的影響卻是積極的。
1.2 模型設計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是由美國科學家C.W.Cobb和Paul.H.Douglas共同探討投入與產出關系時產生的生產函數,也是國際上分析投入與產出關系應用最為廣泛的模型之一。因此,本文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研究資源稅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應是比較合適的。另外,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經濟發展水平會對環境質量產生影響,即當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環境污染程度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然而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環境污染程度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在現實中,經濟與環境是相互影響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會破壞環境,而環境的惡化反過來會制約經濟的持續增長。原有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只分析了勞動與資本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本文在此基礎上增加資源稅收入與污染水平這兩個關鍵要素,形成擴展模型如下:

為避免方差波動影響,對式(1)兩邊同時取自然對數,模型將變為:

其中,Y表示區域生產總值,L表示勞動力投入量,K表示資本投入量,Rt表示區域資源稅收入,P表示污染水平,εit為隨機誤差項,i、t分別表示不同地區和年份。αi、bi、fi分別表示資源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對勞動、資本、污染產出彈性的影響,di表示資源稅對區域生產總值的影響。模型主要研究的是di和 fi的取值。若di和 fi為正,則表示征收資源稅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有促進作用。
2 實證分析
2.1 數據來源
由于上海市資源稅與西藏自治區物質資本存量的數據缺失,且港澳臺稅收制度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選擇了2006—2015年除上海、西藏和港澳臺之外的其余29個省級行政單位的數據進行分析。本文選取各地的GDP以表示區域生產總值,以就業人員數量表示勞動力投入,以物質資本存量表示資本投入。在原始數據中,各地GDP、就業人員數量、資源稅收入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物質資本存量數據來源于目前學界較權威的單豪杰的測算方法,以2000年為基期,自行測算。由于礦產資源是我國資源稅的主要征收范圍,其開采過程中典型的污染形式是大氣污染,因此本文選擇來源于2006—2015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的指標衡量各區域污染水平。由于部分年份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未被納入統計范圍,在保證數據完整性的原則下,本文選取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作為衡量污染水平的指標。本文所涉及的宏觀數據均用以2006年為基期的CPI進行了調整。
2.2 總體效應分析
根據經濟計量準則,為避免偽回歸需對面板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采用單位根檢驗方法對數據進行檢驗。利用Eviews7.2得到的四個檢驗方法的結果如表1所示。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大部分變量原始序列的P值大于0.01,而其一階差分序列P值均小于0.01,為平穩序列,因此判斷 InYit、InLit、InKit、InRtit、InPit同為一階單整序列,可進一步考察變量間的關系。
因為面板數據模型包括混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在分析前必須確定模型形式,因此首先需要對以下兩個假設進行檢驗,以確定選擇常截距模型還是變截距模型。

構造F統計量進行檢驗,F=192.183>F0.01(28,257),因此判斷采用變截距模型。接下來對式(2)的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并進行Hausman檢驗。Hausman檢驗概率顯示拒絕原假設,因此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根據以上結果,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對面板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

表1 平穩性檢驗結果

表2 全國省級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由回歸結果可知,模型擬合效果良好。總體來看,資源稅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資源稅收入每增長1%,區域GDP增長0.083%,說明征收資源稅對區域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此外,征收資源稅將產生正、負兩種效應。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資源稅收入合理安排公共支出,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優化投資結構,解決市場失靈,從而擴大社會福利,產生拉動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另一方面,政府投資也會產生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兩者綜合后影響系數仍為正,這說明征收資源稅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大于抑制效應。政府公共投資的擴大,必然會增加當地的資本存量,經濟發展又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由此系數αi、bi符號為正得到解釋。由系數 fi符號為負可知資源稅會降低污染水平,主要原因是征收資源稅后通過增強的稅收負擔使企業過去的外部性成本進一步內部化,逼迫企業改進生產技術與科學計量資源開采量,從而促使其資源利用率提高,抑制其過度開采與浪費的傾向,從而進一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2.3 地區效應分析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在地理位置、資源結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較大,且各地區資源稅征稅深度與征管方式也有諸多不同,因此資源稅對區域經濟與環境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有必要針對不同區域進行區別分析。下面將參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將我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四個區域對上述實證結果進一步檢驗。建立的四個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分地區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由表4中di的回歸結果可知,資源稅與區域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資源稅收入每增長1%,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地區GDP分別增長0.049%、0.076%、0.102%、0.053%。但。系數 fi的值在區域間卻有較大差異,東部、中部地區的值為負,而西部和東北部地區的值為正,說明東部和中部地區資源稅對環境的積極效應大于西部和東北部。開征資源稅的目的之一是合理調節資源消耗水平,保護生態環境,但在西部和東北部這樣資源富集的地區,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對資源的開采及消耗。現行的資源稅稅制并不足以對企業的行為產生較強的影響,資源稅的環保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2006—2015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資源稅對區域經濟增長及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針對地區差異,通過構建模型對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地區的具體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得出如下結論與建議:
從全國范圍來看,資源稅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政府征收資源稅有利于彌補市場失靈,調節投資結構,促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從而拉動區域經濟增長。同時,資源稅的征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企業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從地區差異來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地區資源稅收入的增加對區域經濟增長均有促進作用,但西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西部多為自然資源豐富地區,資源稅收入占地方財政較大比重,合理利用此收入將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而就資源稅與環境的關系來看,不同地區則存在顯著差異。對于東部和中部地區資源稅的征收可以降低當地的環境污染水平,這是由于我國東部與中部地區交通便利且開放程度較高,人口較為密集,對環境要求較高,因此無論是從主觀治理環境污染的偏好還是客觀的征管水平上都比西部與東北部地區優秀。而在西部和東北部的諸多資源型省份和重工業基地,經濟增長依賴于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及利用,現行的資源稅制度無法有效促使企業降低污染水平。其中,西部地區因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人口較少、科研水平較差,現行的資源稅政策對環境優化作用不大。
因此政府應當進一步深化資源稅改革,根據開發成本、級差收益、環境成本補償與資源的可持續價值等多方面因素選擇資源稅稅負水平,以適用地區經濟增長的差異性;合理設置資源稅的稅收優惠,鼓勵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積極優化產業結構,大力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因地制宜,實行多元化的發展戰略,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