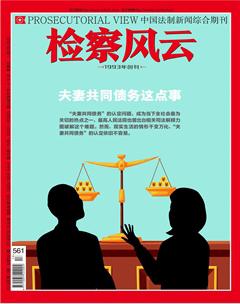法律保護的是表達還是思想
林海
“本片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虛構。”幾乎所有的電視劇里都時不時浮現出這樣的“免責聲明”。不過,“雷同”指的是什么呢?是故事橋段的相似,還是主題思想的相近?抑或是角色人設的相同?80多年前的尼科爾訴環球電影公司案,就涉及了這樣一個問題。
電影和戲劇“如有雷同”,是否屬抄襲
尼科爾女士是一位戲劇編劇。她的《阿比的愛爾蘭玫瑰》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生活在紐約富人區的猶太家庭里,父親固執地堅持他的兒子必須娶正統的猶太女子為妻。兒子違背了父親的意志,與一個愛爾蘭的天主教女子秘密結婚。為了減輕此事對父親的打擊,兒子謊稱對方是一位猶太姑娘。父親請來了拉比(猶太教的牧師),按照猶太人的儀式準備婚禮。
與此同時,這位姑娘的父親也被請到了紐約。與猶太人父親一樣,這位父親也固守其宗教信仰,拒斥其他教派。女兒同樣隱瞞了真相,騙父親說自己要嫁的,也是一位愛爾蘭天主教男子。然而,紙包不住火,兩位父親了解真相后,大發雷霆。然而,無論是天主教牧師,還是猶太人的拉比,都對此持寬容心態,認為這一結合很好。最終,拉比為這個婚禮主持了猶太人的儀式,牧師則為這個婚禮舉行了天主教的儀式——于是,婚姻有了雙重效力,兩位父親都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一結果。
一年以后,這對年輕夫婦有了一對一男一女雙胞胎。他們的父親都只知道有一個孩子出生了。圣誕節時,急于見到外孫和外孫女的兩位老人來到這對年輕人的家里,并在那里再度相遇——兩人再度爭吵起來,他們希望孩子信自己的宗教。好在,出生的是雙胞胎。于是,兩位老父親分別為兩個孩子取了天主教和猶太教的教名,最終達成了和解。戲劇在此結束。
這部戲劇的劇情與口碑都未見得有多出色,如果不是因為尼科爾起訴環球電影公司“抄襲”,恐怕在戲劇史上留不下什么漣漪。或許是參考了故事橋段,環球電影公司出品了內容與該劇如出一轍的電影《科恩家和凱利家》。電影的背景改為了紐約窮人區。長期以來互相憎恨的猶太人家庭科恩家,和愛爾蘭人家庭凱利家,成為了故事主角。猶太家庭的女兒與愛爾蘭家庭的兒子秘密結婚。兩個孩子相愛并秘密結婚。猶太人繼承了一大筆財產,搬進了一幢富麗堂皇的大房子里,并粗俗地炫耀財富。愛爾蘭男孩來尋找他的猶太新娘,卻被猶太人父親趕走。
原本就有罅隙的猶太人父親和愛爾蘭人父親在一場爭吵后都病倒了。待猶太人父親養病歸來后,發現女兒給愛爾蘭男孩生了一個小孩。對女兒竟下嫁給仇人的兒子,還生下了孩子,猶太人父親無比憤怒。兩位父親發生了劇烈沖突。女兒被父親趕走,她帶著孩子回到了她丈夫那貧寒的家。此時,情況突然發生了逆轉,原來猶太人繼承的那筆財產,實際上本該屬于愛爾蘭人凱利一家。最終,在財產、宗教和親情的三重因素影響下,猶太人與愛爾蘭人都決定將這筆財產留給孫子,兩家終于和解。
這兩個故事看上去確實有些雷同,因此編劇尼科爾提出,電影《科恩家和凱利家》抄襲了其戲劇《阿比的愛爾蘭玫瑰》中的角色與情節。雖然人物姓名和臺詞不同,但是對文學作品著作權的保護,不能僅僅局限于作品的原文上,否則抄襲者可通過對其作品中的一些非實質性意義的變化來逃脫制裁。尼科爾提出,環球電影公司的影片,抄襲了她的人物和情節,構成了侵犯其著作權的行為。
然而初審法院駁回了尼科爾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人物角色確實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但其前提是角色須具備獨創性。案件所涉及的兩部作品中,相似的四個角色——一對年輕情侶及他們敵對的父親——是久已存在的文學原型,比如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作品。他們是同類作品中的常見角色。角色越一般化,其受著作權保護的可能性越小。
故事橋段也是一樣,“敵對家族的年輕人叛逆結婚并最終得到諒解”,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能讀到。因此,初審法院駁回了尼科爾的訴訟請求,認為電影并沒有構成對戲劇的抄襲。尼科爾不服,遂提起了上訴。于是案件提交到了著名法官漢德面前。他決定借此判例確定一項原則,即“經過抽象之后的思想,不受知識產權保護”。
“老套路”不受保護,因為那是
“公共產品”
于是,漢德法官代表第二上訴巡回法庭作出了以下判斷:戲劇中的人物,因流于一般,缺乏獨創性而不受著作權保護。他認為,那對情侶的形象很蒼白,他們的作用,至多只能作為一種舞臺道具。任何作家都可以描寫年輕情侶相愛并生育子女的橋段,也可以展現父輩對年輕人婚姻的不滿與和解。更不要說孫輩的出世,財產的分配,這些更為常見的情節了。漢德法官認為,這些故事情節的相似性,需要進行抽象才看得見。可是一旦進行抽象,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種思想,而非一種表達。知識產權法只保護表達,而不保護思想。
在判決書中,漢德法官也提到了尼科爾及環球電影公司應當共同致敬的前輩作品——羅密歐與朱麗葉。猶太人和愛爾蘭人之間的沖突,穿插進年輕情侶的愛情與婚姻,這樣的情節只能算是一種“老套路”。這樣的“老套路”里,在相同主題里可以通用的情節、人物、場景,恐怕都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漢德法官寫道:“這兩部作品中最一般化的情節內容,已經進入了公共領域,它不受著作權保護。如同莎士比亞的戲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達爾文的物種進化理論一樣,不能被壟斷。”
漢德法官認為,兩部作品中的共同點僅僅是猶太父親和愛爾蘭父親間的爭吵,他們子女的婚姻,孫子的出生和最終和解。如果這也構成了雷同,那么只能說明,這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對于這個主題,即使尼科爾“發現”在先,但是她不能形成壟斷。盡管上訴人發現了脈絡,但是她不能獨占;因為選擇這一主題,是她的思想(反對宗教狂熱和種族隔離,尊重婚姻選擇與愛情之類)在起引導作用。然而,思想并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唯有對于思想的表達,才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對象。從兩部作品的表達方式來看,并不存在誰對誰的借鑒和抄襲。
這就是著名的“思想/表達二分法”。這個思想不是“創意”,而是一種理念的選擇。第二巡回上訴法院認為,尼科爾的戲劇《阿比的愛爾蘭玫瑰》確實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是,她在作品中傳遞的思想,并不因此而受到保護。他人的思想可以與她相同。據此,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維持地區法院的一審判決,駁回了尼科爾的訴訟請求。這一判例影響十分深遠,它確定了這樣一項原則:“任何一部確定的作品都可以是許多思想和表達的混合,借鑒或重復這些思想,并不構成抄襲或侵權。”
如前所述,在影視戲劇作品中,除了思想之外,還有一類“公共產品”,那就是“老套路”。漢德法官這樣描述:“當越來越多的枝節被剔除出去以后,留下的是大量的適合于任何作品,尤其是戲劇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式。這些模式不再受到保護,否則作者將會無法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表達。”但是,如果借鑒的表達過于具體,那么同樣可能構成侵權。
在尼科爾訴環球影視公司案判決的六年以后,漢德法官又受理了一起相似的案件(謝爾登訴米特羅-高德溫電影公司案)。由于所涉作品取材于歷史上的真實案件,因此法院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改編作品中哪些東西處于公有領域,哪些內容系原創。對此,漢德法官指出,由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以及事件發生順序與背景,都與歷史上的史密斯案件有著很大的不同,它們屬于原告的原創,因而受著作權保護。被告直接抄襲了這些原創的表達方式,因而構成了侵權。
當這兩個案件擺在一起時,思想/表達二分法就顯現得更為明確。美國的立法也堅持了這種看法。《1976年著作權法》第102節(b)重申了思想/表達二分法,即“對作者的原創作品的著作權保護在任何情形下都決不延伸至任何思想”。伴隨該法發布的美國國會報告對該規定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著作權不阻止他人使用作者的作品中所透露的思想或信息,其目的在于重申在新的單一的聯邦著作權制度的框架內思想與表達之間的基本的二分法未有改變。”
最后需要明確的,是表達不僅僅限于語言。特別在戲劇作品中,表達作品的方式,絕不只限于臺詞。演員的姿勢、場景、服裝甚至于演員自身的外表,都可以構成對于思想的表達——因此,如果在這些方面構成了“雷同”,也將可能構成侵權。1990年的Stewart v.Abend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就作出這樣的判決:“電影可以通過使用戲劇中的‘獨一無二的場景、人物、情節和事件順序侵犯后者的著作權。”應該說,直到今天,這種重視對表達的保護、允許對思想的雷同,仍然是美國著作權法的核心理念。這一畫線標準,早在1930年的尼科爾案和1936年的謝爾登案中,已經有了明確的基調,并且影響立法,直至今天。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