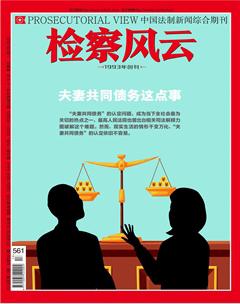快遞送上門怎么這么難
張程
快遞業高速發展本是一件便民、利民的好事,然而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例如最近就有不少網友議論,“自從有了快遞柜,快遞員再也不送貨上門了”。原本送貨上門的快遞服務,緣何因為高科技產品的應用反而上門難了呢?這到底是技術造成的不合理現象,還是因為商業選擇造成的對消費者權益的侵占行為呢?
老大難的“最后一公里”
在快遞行業,小區、樓宇一直以來都被視為快遞行業中配送的痛點和難點,在這“最后一公里”,以往快遞公司都是靠鋪人力來解決,不僅成本高,而且效率低。尤其是隨著近年來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漲,以及各大快遞公司明里暗里不斷的價格大戰,使得“最后一公里”高企的配送成本已經成為許多快遞公司的心頭病。為此快遞公司也在不斷想辦法對此進行優化。
曾經有快遞公司嘗試過利用“服務眾包”的形式,類似于共享汽車的接單模式,利用閑散的社會勞動力來緩解“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難題,但是在飛速高漲的海量快遞包裹面前,這種方式能分擔的負荷十分有限,而且時效性和服務的專業性也得不到保障,同時還會衍生出諸如用戶信息泄漏、用戶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等問題。同時在監管層面,這種“眾包”模式的快遞服務也沒有獲得認可。根據《郵政法》第51條規定,“經營快遞業務,應當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快遞業務。” 2014年采用“眾包模式”的人人快遞由于未取得業務經營許可,在天津等地被叫停。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眾包快遞對于解決“最后一公里”難題的作用還很有限。
不過快遞公司并沒有放棄解決“最后一公里”配送難題的努力,不少企業轉而開始嘗試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來尋求突破,例如使用無人機送快遞。
無人機配送的優點顯而易見,速度快、效率高、人力成本低。國外已經有很多企業在嘗試使用無人機進行送貨,例如國際快遞巨頭敦豪、聯邦快遞等都已經在布局。同時國外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如谷歌、亞馬遜等也都在研發可用于送貨的無人機。國內企業也在積極嘗試使用無人機送貨,如順豐、京東等。從技術層面來看,國內無人機送貨已經能夠實現。2016年6月,京東在江蘇宿遷市順利完成無人機送貨第一單。該無人機為京東自主研發,載重從10公斤到15公斤不等。但是從實際應用來看,要想在城市地區大規模普及無人機送貨還不太現實。首先,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大規模使用無人機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其次,無人機還存在涉及侵犯隱私,入侵私人空間的問題。然后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空域管制的問題,目前申請空域不僅要經過民航部門,還要經過軍事部門,流程復雜,限制因素眾多。最后,無人機的續航時間短,精準度不高等問題都是制約這種方案在城市中應用的重要因素。
在嘗試了諸多方案都沒有找到一種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之后,許多快遞企業開始退而求其次,使用“自提點”這一曲線救國的方式。“自提”在某種意義上有效的解決了一部分“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難題。當用戶不在家,無法當面簽收快遞時,自提點為用戶提供給了一個選擇,即快遞員可以將包裹放在自提點,當用戶有時間時可以自行前往拿走包裹。在自提點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一種與用戶空間距離更近,同時鋪設也更為方便的智能快遞柜終端。人們可以通過手機上接收到的驗證碼信息,在樓下,或者小區里就能自主收取快遞,同時用戶還可以通過快遞柜來寄快遞。
自提點和快遞柜在方便用戶的同時也極大的方便了快遞企業,尤其是奔波在“最后一公里”的終端配送員。以往他們需要爬樓挨家挨戶的送快遞,如果用戶不在家,又實在沒有地方可以代收,快遞員還不得不另外約時間,二次送貨。有了自提點和快遞柜,遇到用戶不在家的情況,快遞員便可與用戶商量,將快遞放在這些自提點。這無疑大大提高了末端配送的效率,方便了快遞員,也為快遞企業節省了人力成本開支。
然而這一對用戶和快遞企業都有益的終端配送輔助解決方案,卻在現實生活中逐漸變了味,許多時候甚至給用戶帶來了困擾。
快遞柜成了“甩手柜”
“以前出于同理心覺得大家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所以基本上快遞員說要放在自提點或者快遞柜我都是同意的。但是現在發展成了,快遞員基本都不問我在不在家就直接把包裹放在了快遞柜,或者自提點,甚至是周末休息時候也是如此。”家住上海松江某小區的毛先生告訴《檢察風云》記者。自從小區里裝了快遞柜,快遞上門已經成了一件稀罕事,無論是工作日還是休息日,無論家里是否有人,快遞都一律被放到了自提點,而且也不再有電話通知,只是短信告知用戶。“現在每天手機都會收到很多的短信息,各種廣告推銷、APP應用提醒,稍不注意,取快遞的信息就會被淹沒,那么就只能等到想起來有快遞這個事的時候才回過頭來看看是不是漏了短信”,毛先生向記者補充道。這種方式給其帶來了不小的困擾。甚至有一次,手機根本就沒有收到提示信息,而快遞卻顯示已經在多天前被簽收。一頭霧水的毛先生還以為是家人代為簽收了,結果在家里找了一圈也沒有找到這份快遞。隨后翻了過去幾天的短信,也沒有看到任何的取件信息。難道是送錯了,送丟了?于是毛先生致電電商客服詢問情況,隔天物流配送人員電話告訴毛先生,這份快遞被放在了自提點,不需要取件碼,憑手機號碼就可以取件,由于其工作的疏忽,忘了給毛先生發短信。這件事讓毛先生十分惱怒,同時又十分無奈,“投訴一個快遞員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包裹還是會繼續放在快遞柜”。
毛先生的情況并不是個案,在網絡上同樣有不少人在抱怨快遞不上門的問題。這種問題在快遞柜、自提點等終端配送輔助解決方案出現之前并不多見。原本便民利民,對快遞企業也大有益處的快遞柜,為何現在就變成了“甩手柜”了呢?
據記者了解,這種情況并不能完全簡單的歸咎于終端配送員的不作為,也與快遞企業的經營策略存在很大的關系。記者從昆山市某區域快遞配送員處了解到,他們平均一天要送兩三百件快遞,這種配送量是快遞站點分配給配送員的。很顯然如果每件快遞都電話溝通、送貨上門,根本就沒辦法配送完。于是不少配送員需要將很大一部分快遞放在自提點以提高效率。隨著末端配送員“效率提高”,于是又有更多的工作量壓在他們身上。如此往復,倒逼配送員對于快遞柜、自提點的依賴程度大大提高。但是顯然這種未經用戶同意直接將快遞放在自提點或者快遞柜的行為,侵犯了用戶的合法權益。
根據2008年頒布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的規定:企業應當將快件(郵件)投遞到約定的收件地址和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快遞暫行條例》第二十五條中也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將快件投遞到約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當面驗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權當面驗收。
根據上述的這些有關管理辦法和條例,顯然消費者有權要求快遞企業將快遞送到指定的收貨地址,且收件人有權要求當面驗收。如今連送到指定地點都難以做到,更遑論當面驗收。
受影響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平時都在家的人,如老人、家庭主婦,以及在家工作的自由職業者。這些人深受快遞不上門的困擾,原本在家就可以收到的快遞,現在要自己下樓自取,有時候一些較重的物品還要去自提點自提。
無心之失,還是有意為之
對于快遞柜變成甩手柜,侵犯用戶合法權益的情況,快遞企業是并不知情的無心之失,還是明知故犯的有意為之?
眾所周知,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紅利的消失,人力成本在過去十年已經上漲了數倍。快遞企業,尤其是末端配送環節,是人力資源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支出是最大的成本支出項目,提高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可以為快遞企業釋放巨大的利潤空間。
從目前一些已經上市的快遞企業公布的財務數據來看,兩方面的信息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快遞柜變成甩手柜。第一,從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來看,無論是直營模式的順豐,還是以加盟模式為主的“三通一達”,單件快遞的收益總體都處在下降趨勢中。換言之,平均單件快遞的利潤率在下降。第二,各大公司中人力成本支出占總營業成本的比重都很大,其中直營模式的順豐尤其如此。根據順豐控股披露的2017年年報數據顯示,人力成本支出占到了營業成本的約三分之二,數額高達380億元。在利潤率下降和人力成本居高不下這一反差明顯的對比中,自然而然會讓企業想要在人力成本上“提質增效”,以增強企業競爭能力。 2015年順豐集團推出豐巢快遞柜,以幫助緩解“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難題,提高末端配送的效率。目前豐巢快遞柜在全國已布設超過7.5萬組,“三通一達”亦在豐巢科技股東行列。
今年5月底,“三通一達”又聯合入股了阿里系菜鳥物流旗下的浙江驛棧網絡科技公司,后者主要業務是致力于解決“最后一公里”配送問題,主要方式是通過鋪設自提點和智能快遞柜提高末端配送效率。
隨著快遞市場競爭格局的基本確立,各大快遞公司經營風格也在改變,從向市場要份額已經很難,因此快遞企業轉向向管理要效益。利用快遞柜等終端設施提升末端配送的效率,減少成本,增厚利潤成為了快遞公司有效的創收手段之一。在犧牲用戶部分使用體驗、合法權益與增加企業利潤之間如何選擇,部分企業是否存在將天平傾向了企業利潤上,恐怕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