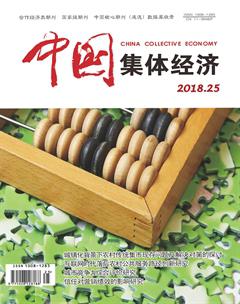公共權力視域下土地流轉中農民權益受損原因分析
謝楚楚
摘要:結合對我國土地流轉中有關農民權益損害的案例匯總和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村治主體的權力遭遇困境是導致農民權益受損的重要原因。繼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稅費改革之后,國家下放政權,對村治主體進行吸納式治理,但又沒有把它納入行政體制,使其最終淪為一個“空殼子”;村民和村社的關系也變得日益緊張,最終村民喪失對村治主體的信任,村治主體權力陷入困境,直接導致村民的權益受損;相應地,在土地流轉中農民權益難免受損。
關鍵詞:土地流轉;權益損害;公共權力;基層治理
1982~2016年,中央所發(fā)布的一號文件幾乎全都聚焦在“三農”問題上,而農村的土地問題是我國農村的核心問題。從我國實行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后,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農村的土地流轉呈現(xiàn)多元化,由此演變的沖突糾紛成為農民反抗維權的重點。農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流轉的主體是農民,而村治主體又是雙重角色的矛盾體,因此,在雙方交鋒下無疑會對農民權益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
一、理論視角
現(xiàn)有文獻歸納農民權益損害的原因通常為:農民自身缺失產權意識;法律政策不完善;土地流轉運行機制不規(guī)范等。在農民自身方面,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均不高,權利意識淡薄,沒有途徑和實力來維權,當達到反抗的心理閾值后,就會采取極端的方式來為奪權。在法律政策方面,現(xiàn)行有關法律存在很多漏洞,農民產權意識模糊,對流轉缺乏充分的了解,很容易在流轉過程中吃虧上當;另一方面基層干部有法不依,濫用權力,利用土地流轉進行權力尋租。土地流轉運行機制方面,農民多為口頭協(xié)議,缺乏正規(guī)的合同流程,流轉價格帶有隨意性,筆者在多次調研中了解到流轉雙方對租金都不滿意。
通過歸納文獻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研究都是從農民自身和制度機制方面尋找農民權益損害的原因,具體的表現(xiàn)在微觀層面上,但都是問題存在的表象,如果進行更深層次的推敲,會發(fā)現(xiàn)忽略了土地流轉中關鍵的參與者——村治主體,應追究其所承擔角色的權力功能。所以本篇論文在充分查閱大量案例和人民網(wǎng)的輿情分析后,結合社會學中的公共權力這一概念,試圖從權力功能出發(fā),對土地流轉中農民權益為何受損進行解讀。在各個網(wǎng)站查閱了幾十個案例后,歸納共通性并抽取典型案例,以村治主體的公共權力這一視角作為邏輯起點。
二、公共權力陷入困境下的土地流轉
恩格斯認為,公共權力在國家產生之前就早已存在,人們借此來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和糾紛。我國公共權力來自于人民的賦予,人民把權力讓渡給某些個體,讓他們作為代表來使公民權利達到最大化。在本文中,村民賦予公共權力給村治主體,村治主體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代表村民管理村莊事務,調動村莊力量,經(jīng)營村莊公共資源。
村莊治理始于20世紀,當時正處于政治動蕩的年代,變革如“家常便飯”般輪番上演,最終結果就是基層社會失范,村莊公共權威缺失,村治主體公共權力被架空并陷入困境。直至80年代上半葉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村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公共權力的真空狀態(tài)才有所好轉。但是自從農村取消收取“三費”后,村治主體與農戶的聯(lián)系日趨疏遠,僅靠收取稅費來維系聯(lián)系的鏈條也被切斷。直接后果就是村治主體入不敷出,機構運轉非常困難;但是國家下派的任務還是要正常完成,為了任務“達標”,村治主體被權力所“俘獲”,更多地開始考慮個人的私利,而忽略了農民的主體權益。
界定了公共權力的定義和梳理我國鄉(xiāng)村基層的權力發(fā)展過程之后發(fā)現(xiàn),村治主體作為村莊經(jīng)營的關鍵角色和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和掌握者,與村民的權益聯(lián)系密切。村社權力是村社中的運作機制,是村民的一種手段型利益,通過有效行使,可帶來直接利益。公共權力陷入困境,得不到有效行使,村民利益將直接受損。本文將結合具有共通性的幾個案例,從公共權力陷入困境的兩種表現(xiàn)來分析土地流轉中農民權益受損的原因,即公共權力的越位和公共權力的缺位。兩種表現(xiàn)都會使村民權益不斷受損,因此,無論哪一項涉利政策進入村莊都會“深受其害”,土地流轉也未能幸免,以至于出現(xiàn)許多損害農民權益的案例。
三、受損原因分析
筆者在最近作為被訪問者,參與了第三次全國農業(yè)普查,從中發(fā)現(xiàn)土地流轉為這次普查的重點。土地流轉已經(jīng)成為未來農業(yè)發(fā)展的基調。近年來,隨著農地市場化的發(fā)展,土地流轉的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關于土地產權的糾紛、扯皮也相繼增多,成為村莊治理的一大新難題。而公共權力作為治理村莊困境的關鍵變量,加以探討有助于分析農民權益受損問題。故本篇將從村集體這一基層主體出發(fā),結合農民權益遭到事實損害的兩個典型案例分析村治主體的權力功能。
(一)村治主體公共權力的越位
長期以來,村民與村治主體形成了一種“委托——代理”式關系。村集體組織作為代理人,本應以村莊利益最大化為前提,可在實際流轉過程中,一旦出現(xiàn)謀利化傾向,便以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為目標,公共權力便難以在正確范圍內繼續(xù)行使。上級下達的任務沒有“達標”,村治主體便會強行介入,以各種手段強迫農民流轉土地,而村民并沒有賦予村治主體這種權力,可見村治主體的公共權力已經(jīng)越位。在農民與村治主體的博弈環(huán)境下,農民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不博已輸”的結果不言而喻。
案例一:灌云縣隆昌村千畝農田卻雜草叢生,村民卻不敢種,因為村干部放了話,誰種了就拔誰的。正在翻建的房屋,如果不同意流轉土地,就說建房超標,發(fā)停建通知和罰款。村支書龔興旺兼鄉(xiāng)規(guī)劃辦主任。某村民不交地,大兒子在縣里是公務員,被村干部叫回來做父親的“思想工作”。最終因擔心兒子前途簽字同意。心急的某村民到地播種,村干部直接來硬的,農戶反抗就會挨打。
從材料中可以看到,村治主體用威脅式的手段強行干預,表明村治主體公共權力的運用已超越其固有范圍,不再是村莊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承載者。另一方面,村治主體不再是簡單的村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行政權力上的延伸;為了完成上面下達的任務,村治主體可謂不擇手段;村支書身兼兩職,利用職務之便行使私權;公務員在黨政權力的壓力下,選擇向權力靠攏,官官相護,紛紛被權力所俘獲。從本質上來看,村治主體的公共權力已經(jīng)越位,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的承包經(jīng)營權已經(jīng)遭受剝奪。
(二)村治主體公共權力的缺位
在村莊治理的實際過程中,村治主體往往把握不到自己的權力邊界在哪里,不知道哪些權力可以行使和如何行使。從國家層面來講,這種權力缺乏法律的支持和認同,沒有暴力機關來對村民的行為進行強制性約束,村治主體的公共權力極易缺位和不到位。
案例二:在山東省汶上縣義橋鎮(zhèn)唐莊村,前幾年村里就把村民的土地集中收回,以每畝地一年1000元的價格進行了流轉,有的建起了養(yǎng)殖場,但如今錢卻遲遲不發(fā),村里的環(huán)境也臟亂不堪。
上述案例提到,土地流轉后,村民的私有財產所有權和流轉收益權已遭受損害。由于村治主體的不作為,造成其角色迷失,沒有利用公共權力來進行引導、監(jiān)督和服務。對于流轉后出現(xiàn)的問題,村治主體采取的策略是不聞不問,逃避推脫;由于公共權力陷入困境,村治主體權力缺位,缺乏權威,甚至被架空,成為“空殼子”,然而它并沒有能力去消化這種不良后果。村治主體形同虛設,獲取不到村民的信任,而這種案例的發(fā)生不會隨著權益收到損害而停止,只會惡性循環(huán)。
四、結論和對策探討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農業(yè)部部長韓長賦明確表示,土地流轉中的重要問題是保護好農民的權益。可見在新的歷史階段,唯有真正讓農戶吃上“定心丸”,農戶的產權得到有效保障,新一輪農村改革才能具有堅實的基礎,農業(yè)現(xiàn)代化進程才能得以穩(wěn)步推進。所以本文結合大量案例中的共同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對造成農民權益損害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從與人民心理和現(xiàn)實空間距離最近的村治主體下手,認為村治主體的公共權力陷入困境,權力的越位和缺位加劇了村治主體形象的瓦解和崩塌,也是造成其喪失民心的“推手”。
盡管現(xiàn)有政策是深受農戶所擁護的,并且相信國家會以人為本,深切地為農民著想,但忽略了對村治主體公共權力的建立和保障,出現(xiàn)某些人“鉆漏洞”和“尋租”的僥幸心理;一旦農民權益出現(xiàn)損害時,由于缺乏對村治主體的敬畏和信任,農民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維護和捍衛(wèi)。因此,重新找回村治主體的公共權力邊界是至關重要的,在國家的行政權力建設中,重構鄉(xiāng)村公共權力與權威,使村治主體找準角色定位,“在其位,謀其政”;國家加強對村治主體的制度法律約束,提高農民的農民的產權意識和權益保障意識,如此,農村治理的實踐困境才會最終有效解決。
參考文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單位:貴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