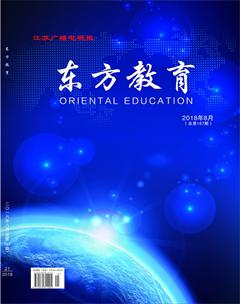僧教育與佛教教育的界定
劉依然
自古以來,教育的種類就很多,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的種類就不斷地增加,尤其在近代民國期間,社會不安,人心散亂,有識之士對于教育有了新的認識:“眾生之苦甚多,教育之法不一……惟佛學全為斷除世間一切有情妄執,佛學之超越尋常如此,于世界人身有絕大之關系,其教育之重要,自非尋常教育之可比矣。”由此可見,守塔認為對于不同的事物教育之法不一,但是為由佛學教育能夠使人們脫離苦難,這是其他教育不能夠比擬的,且鑒于當時殘酷的社會環境,“今何時哉,非所謂物競極烈弱肉強食之時乎……希望從今以后,諸山長老對于佛學與教務兩端極力設法整理之,提倡之。”佛學教育受到了重視。但長期以來,人們常常忽視僧教育與佛教教育之間的差別,因此,筆者在這里對二者做一個界定。
一、僧教育的定義
(一)僧教育的緣起
1、迫于形勢謀求生路的產物
嚴格來講,僧教育是直到清光緒年間才出現的,其產生過程較為曲折,據史料記載:“所謂僧教育,乃指佛學院而言。其起源于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亦即康梁提倡變法維新的那一年。……便引起中日兩國外交上糾紛,經雙方交涉結果,清廷要日本放棄保護中國寺廟,清廷始允許佛教界自興學校,自保寺產,并停止廟產興學運動,這便是開創僧教育的緣起!”
除此之外,還有學僧的記述:
“僧教育這個名稱,起自光緒末年的僧教育會……然而佛教確實因此辦起所謂僧教育來了。”由此可見,僧教育的出現根源于廟產興學運動,由此導致佛教界的抵抗,從而想出來的一種謀求生存的一種手段而已。
2、近代佛教復興的需要
“是故欲得世界之和平,人民能真正自由平等,非從佛法著手不可,而法在人弘,吾人既為佛子,理當代佛揚華,已盡國民之天職也。……此講習佛學與國民有重大之關系也。”太虛法師指出世界各國的佛教僧眾都有嚴格系統的僧教育,然而中國漢地的佛教僧眾卻在渾渾噩噩中消磨時日,如果再不對僧眾進行教育勢必會被淘汰。“日本曹洞宗等規定為僧須具中學畢業之程度再加苦修八年,而后乃可任教師……唯我國漢僧久成散漫無紀凌亂無序之現象,……而反為佛教發展之障礙物,終必受社會之天然淘汰也。”
可端法師認為佛教衰微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還是源于僧眾沒有學問,不明佛教,并進一步認為社會反對的不是佛教而是僧人。“夷考佛教衰頹之由,雖有多端……非反對法,所反對者,惟僧人而已。”面對這樣的現狀,可端法師不忍心看著佛教因此而敗亡“僧眾若無相當學問知識道德,不足以弘揚佛法,不足以維持僧實,不足以保存僧產,端實不忍見僧眾之滅亡,佛教之毀殘,故敢貢此憨直之言。”接著他指出僧教育才是復興佛教的出路,“外感潮流之逼迫,內痛佛法之衰亡,……則教可興,而僧可存。”
嘯巖也認為當前佛教僧眾缺乏道德學問不能夠弘揚佛法:“為僧宜人人講習佛學之所以良由佛法二寶之存歿……不能紹隆三寶為世之福田者而言之耳”。進而他指出若要復興佛教,那就必須興辦佛教講習所開展僧教育“應當如何振興宗教此則非精進勇猛講習佛學不能。故諸長老熱心從教,特立佛學講習所,挑選僧徒而教育之。”清海法師也與以上三位的想法不謀而合,并分析中國日本除孔教外,即以佛教為尊,然而能盛行于亞洲東南部之原因卻非佛教徒勢力所致,實中國歷代帝王崇尚提倡之功。“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最盛于魏晉六朝。而莫衰于今世。今世之所以衰則多由于僧徒之不學,則莫非濫度戒之所以致。”并提出實行僧教育以培養復興佛教的人才“中國僧侶勢力薄弱,而抱厭世主義。為今日計,欲弘佛教,當先厚僧侶之勢力,勢力厚而后我得我行所當為無阻障之患師。”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要弘揚佛教需要增加僧侶的勢力,那就需要僧材。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佛教需要復興那就需要弘揚佛法的僧才,故而開辦僧教育迫在眉睫。
(二)僧教育的界定
由上述可知,在順應佛教復興的潮流的趨勢下,僧教育高僧大德們為喚醒僧眾挽救佛教滅亡的危機應運而生的。對于僧教育的定義,高僧大德們給出了不同的見解。
慧雲法師認為“僧是出家佛徒的集團,僧教育乃僧的教育以及后天的方法陶冶身心,使其發展向上,完成比丘和尚乃至僧伽的工作為定義。”僧教育以“陶冶有舍離假我,把捉真我的出家佛徒,……宜宣傳法音以利蒼生耳。”他又指出由寺中出資廣立小學,僧俗兼收而設僧教育會主管,并不是僧教育,他認為所謂辦小學是推廣教育,則此乃僧伽所做的社會教育事業,若謂由僧伽做社會教育的事業,可包括在僧教育目標的度一切眾生中,然此既是目標,乃辦理僧教育的根據即根據此目標而用種種方法使出家佛徒刻苦修習以完全比丘和尚乃至僧伽的工作。“若吾不知他們從何處定此名義,將辦理小學包括在僧教育目標的度一切眾生中,則陶冶比丘或和尚的教育將僧伽所做的事業(教育事業,社會事業等)相混淆。”換言之,縣教育會或省教育會乃是推廣教育的執行者。若然則推廣僧教育的執行者方能稱之為僧教育會。廣設小學等是僧伽所做的社會教育而非僧教育,此乃由于當事人不明教育更不明僧教育,惟知掩耳盜鈴。”
葦舫法師認為“以出家眾為主體的僧教育和在家眾為主體的佛學教育而兼僧教育”。除此之外,近代學者李明在其研究生論文《民國時期僧教育研究》中給僧教育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僧教育,主要指有僧伽的參與的教育活動,在教育活動的過程中,僧伽無論是作為施教者、受教者、抑或是主辦者、參與者,都應該被包含在僧教育的范圍之內。”
根據以上論述,諸位高僧與學者為僧教育所做出的解釋各有側重,筆者擬在前人的基礎上嘗試對僧教育做出一個新的定義:所謂僧教育,主要是指在光緒末年佛教僧眾為了抵抗廟產興學自保寺產而尋求的生存之路,且在高僧大德領導和有識之士的推動下,為弘揚佛法復興佛教而培育的德學兼備的僧才創辦的教育事業。
二、佛教教育的界定
佛教教育與僧教育相比,其所包含得范圍更加寬廣。葦舫法師曾指出“佛教自身即是教育,這是因為釋迦牟尼佛……即得步步向上,日見光明,達到真善美的解脫自在境界。”那么,從佛教的字面來解釋的話,“佛”指的是“覺者”,佛又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世尊。“教”是指教導、教育的意思。因此,我贊同葦舫法師所言“佛教自身即是教育”的說法即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
佛教教育教育內涵包括了無盡無邊的事理,時間上,它講過去、現在、未來;空間上,它講我們眼前的生活一直推演到無盡的世界。所以它是教學、是教育,不是宗教;它是智慧、覺悟宇宙人生的教育。
大體而言,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佛教教育不僅包括叢林制度中傳統的對于僧眾進行的教育、佛教四眾開辦進行佛法弘化的社會教育機構,還包括在家二眾所做的佛教教育,隨著時代的演進,佛教教育還包括綜合大學中所開設的佛學課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