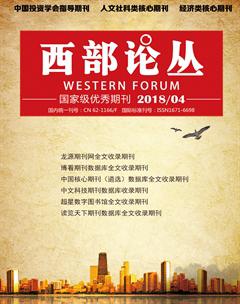試析福澤諭吉對功利主義自由觀的繼承與發展
姚惠鑫
【摘 要】 福澤諭吉是中日學術史上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脫亞論》一文中充滿了對亞洲各國的蔑視態度,充分顯現了其功利主義思想的特質。《脫亞論》中,福澤反復強調為了日本國之自由獨立,需脫離亞洲,這與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義基本一致。但是穆勒的功利主義,旨在實現全人類最大的幸福為目的,而在福澤看來,明治時期的日本已經遙遙領先于亞洲諸國,實現本國之獨立,亦是為本國謀最大幸福,即便運用何種手段也不為過。殊不知,福澤的這種“功利主義”,誠然為日本文明發展帶來莫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更是埋下了日本今后地位更迭的禍患。他雖繼承了功利主義思想,卻并未秉承功利主義的理念,為實現人類的最大幸福做出貢獻。
【關鍵詞】 脫亞論 自由觀 功利主義
一、穆勒功利主義的核心及辯證關系
19世紀的西方,處處充斥著進步思想潮流,各種改革思潮不斷涌現,民主自由風氣擴散開來。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1806年出生于倫敦,其父為著名功利主義哲學家詹姆斯·穆勒,自幼受其父親的嚴格教育,穆勒在數學、邏輯學、政治經濟學等領域頗有造詣。由于早期在學術上的訓練,穆勒在少年階段就已擁有比大學畢業生還要豐富的學識,而與之相比更重要的是穆勒形成了一定的思辨能力,這種能力對于他今后在思想領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在穆勒的哲學思想當中,尤為世人所熟知的是功利主義及自由論。功利主義,是一種以實際功效或者利益作為其道德標準的倫理學說。穆勒在《功利主義》一書中的第二章寫道:“功利道德所基于的“‘生活理論,那就是追求快樂、擺脫痛苦是人唯一渴望達到的目的”。由此可見,功利主義的核心便是以實現“最大幸福原則”作為重中之重,幸福和福祉是評價人類行為、政策和法律的標準,這種觀念亦被稱作“幸福觀”。穆勒的功利主義幸福觀同邊沁不同,邊沁主張幸福是可計量的,對功利或利益的追求有利于幸福總量的增加,個人幸福量的增加促使社會幸福量的最大化成為可能,即行為者自身最大的幸福,側面體現出了其學說核心——利己主義。而穆勒則認為人的幸福感有量和質之分,以追求“質”至上,并且對邊沁的學說進行了一些修正,他將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強調非行為者自身的幸福即與行為者有關的“所有人”的幸福才是“最大幸福”。可見,穆勒的功利主義學說不以個人利益和幸福作為行動的出發點,而是以人性至上為標準,實現全體人民的幸福才是功利主義的最基本原則。
本文重點討論功利主義與《脫亞論》之間的關系,其中除了涉及到福澤諭吉對穆勒功利主義學說的實踐評說之外,還會對正義和道德這兩種理念進行闡釋。支撐功利主義學說的骨架,離不開對“最大幸福原則”及道德原則的充分理解,而在追求幸福的基礎之上,穆勒又提出了一種阻礙幸福實現的因素——正義,由此展開了幸福——道德——正義的辯證過程,同時以上這些原則亦是功利主義的重要論證。此外,穆勒的功利主義思想是建立在助益于人、為他人謀求幸福的基礎之上的哲學觀念,與自私自利、不擇手段的功利做法截然不同。因此,穆勒的功利主義與正義這一對辯證關系在理論上毫無沖突可言,甚至可以說基于功利主義之上的正義才是整個道德的主要組成部分,具有強大的道德約束力。
二、功利主義性質的“自由觀”
(一)“自由觀”的產生背景——“朝貢體制”的顛覆
研究日本史,我們不難發現古代時期的中日兩國維持了上千年的朝貢關系,雖然目前史學界對這一時間概念尚有異議,但是自兩漢以來,日本就已經向中國的朝貢體系逐漸靠攏,中日兩國間的朝貢體制開始出現萌芽。至隋唐時期,朝貢貿易達到鼎盛階段,兩國互派使者,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貿易、社會文化,日本統統吸附到本國來并加以改造,成為具有獨自特色的國風文化。南宋初期,中國國內動亂不斷,中日之間沒再繼續外交活動,但民間貿易頻繁,佛教交流達到空前的盛況。明朝時期,政府實行“海禁”,在勘合貿易當中,日本獲利眾多,而中國卻情愿通過不平等的朝貢關系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地位。長達百年的這種“畸形”關系,在日本明治維新后徹底瓦解。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由外而內的選擇吸附型國家,中國是一個單向性輻射狀向外傳播的國家。18世紀至19世紀,工業革命取得重大成果,資本主義的優勢顯現出來,習慣于效仿他人優點的日本認識到封建體制必須改變,由此開始明治維新,企圖稱霸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不僅在“機器”領域進行變革,同樣吸納了西方的民主思想,福澤諭吉作為早期的留洋學者,認識到西方思想的進步性,在日本大肆宣揚民主理論,并在《通俗國權論·通俗民權論》一書中提倡人民加強自身獨立性,不可過度依賴政府,才是解決困境的路徑。這種言論同樣可以在《脫亞論》當中找到影子。《脫亞論》前半部分福澤大篇幅地論述了國家民主獨立的重要性,認為西方文明的廣泛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并強調“國家為重,政府為輕”,只有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才能在亞洲開創出一個新格局。《脫亞論》后半部分內容則是對以上言論的事實論證,福澤將中國和朝鮮歸為“面對文明不思進取、頑固守舊、留戀陳規舊習”的國家,同這種國家為伍,只會阻礙日本文明的進步。字里行間充滿對亞洲各國的鄙夷態度,談及《脫亞論》的實質,與其說福澤諭吉宣揚民主獨立的思想,不如說是福澤煽動日本人民及政府早日與亞洲斷交的冠冕堂皇的說辭。
與此同時,中國正值清朝末期,國力衰微,長達數百年的閉關鎖國狀態已經將中國與世界拉開了一定距離,正是這種“未出世”的狀態,使日本這個骨子里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漸漸“膨脹”起來,借發揚西方文明,并自詡為亞洲“文明先鋒”帶領中國等國家打開亞洲市場這一托辭,堂而皇之地對亞洲各國進行侵略。由此可見,《脫亞論》中所鼓吹的自由文明理論,完全是為日后發動戰爭所設立的“特定理論”。可以說,朝貢體制的顛覆,將中日兩國的政治制度徹底區分開來,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封建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在“機器”領域還是思想領域,似乎毫無優勢可言。
(二)福澤諭吉對穆勒“功利主義自由觀”的繼承
談及穆勒的“自由”思想,離不開對其功利主義的理解。他的功利主義,是建立在邊沁功利主義學說之上,又對邊沁的學說加以修正,形成了獨特的功利主義觀。功利主義的核心內容如前所述,是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作為一切行為目的的準則,認為只有符合最大多數主義的功利主義原則,才是評判是非善惡的標準。明治時期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們主要吸收了19世紀西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的構成等近代文明理念,并傳授給了日本國民,其中較著名的便是福澤諭吉。他一生有諸多思想與文明相關的著作,在《勸學篇》的第三篇中,福澤指出:“生當今世,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余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起來,進而保衛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福澤認為,致力于解放人民思想,提倡個體獨立,從而達到國家獨立的思想主張,才是維持日本長盛久安之計。而日本文明的落后,恰是封建勢力壓制國民思想導致的后果,若想擺脫這種局面,必須要營造出獨立自主的氣氛,這種“功利主義自由觀”被福澤大力追捧,亦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贊同。
三、結語
開篇業已提及功利主義是一種以利益作為其道德標準的學說。所以說無論通過何種方式去實現這種利益,都可稱之為是“功利主義”的行為。福澤在《脫亞論》中先闡述了西方文明的先進性,進而搬出“脫亞入歐”的理論宣言,提倡個人獨立、國家獨立,言辭中充滿對亞洲的蔑視。在《脫亞論》之前,福澤已經出版《文明論概略》、《勸學篇》、通俗國權論、通俗民權論等等,從國家教育上升到政治制度、思想領域,無外乎就是提倡他的西方文明史觀,主張廢除舊有體制,建立新體制。福澤的種種言行,無疑繼承了功利主義的思想,但是他是否真的像穆勒所說的那樣,是否遵循功利主義的核心——最大幸福原則了呢?其實,追求自由是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本分,但如果追求的是建立在他國人民痛苦之上的自由,這種違背人道主義的做法是不值得為世人所推崇的。
【參考文獻】
[1] 福沢諭吉.「脫亜論」[M].1885年.
[2] 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M].New York: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24.
[3] 筑後則.王鐵軍[譯].明治初期日本關于近代文明的三大爭論[J].日本學者論壇.2007年.
[4] 梁君.論穆勒的自由觀及其啟示[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