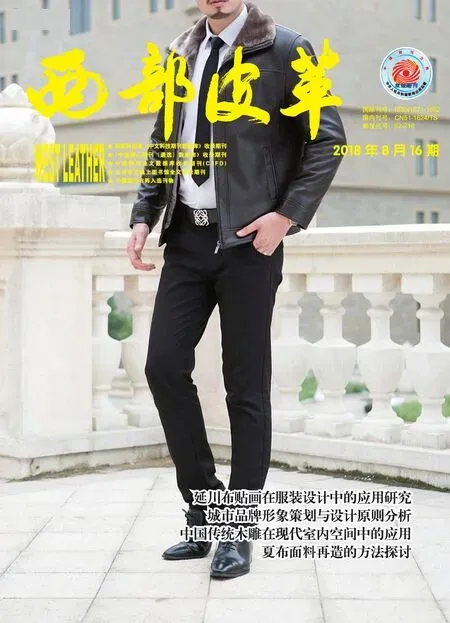政企關系對產能過剩的影響
左亞明
(廣西大學商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0)
1 文獻綜述
我國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產能過剩判斷指標體系,盡管產能指標體系不夠完善,但是并不妨礙學者對于產能過剩的成因和化解方式的研究。因此國內外關于產能過剩研究常用的指標就是產能利用率,而產能利用率最早是源于美國的五家機構提供的產能利用率的衡量數據,其中大部分機構是采用調查統計的方法進行衡量和測算,雖然使用調查的方法得到的數據真實可靠性較高,但是這種方法的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也相對較高。而近幾年產能利用率的測度方法也逐漸的完善豐富起來,包括峰值法、成本函數法、前沿面分析法和協整方法等。而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在所有可用的資源都使用的前提下,以這個企業的最大產出的比例作為衡量產能利用率的指標。對于產能過剩的成因,以林毅夫等(2010)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不完善,而且對某些新興的行業存在不成熟的認知,但是一旦有一些企業在這個領域進行了投資,并且獲得了相應的收益,企業企業就會在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盲目的進行追隨性投資看,由此在投資上將出現“潮涌現象”,并導致產能過剩。也有學者王文甫等(2014)認為地方政府這個有形的手在市場中進行了過多的干預,才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本身是政治人士,所以他們會比較關注自身的晉升或者政治上的利益得失,由此會引發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也會導致政府對于企業的盲目支持,由此導致大量“僵尸企業”的產生,這些也都會加速產能過剩的發生和惡化(周黎安,2004)。總之,這一類學者都認為是政府的干預導致的產能過剩,他們認為政府的干預降低了企業進行信貸融資的門檻,并且在稅收和補助方面進行過度的支持,給了企業即使在績效很低的情況下也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得以存活。因此本文就從政府角度出發,研究政企關系對產能過剩的影響。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一直是市場經濟大環境下學者們進行經濟研究的熱點,也是企業在面對調查問卷時候的一個敏感性話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依賴市場還是依賴政府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而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實際是由于市場上資源的配置不合理導致的,而地方政府過度干預又導致了市場上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所以說到底還是因為政府的過度干預(鞠蕾,高越青,王立國,2016)。有的學者在運用博弈均衡分析企業決策的時候,對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選擇,最后指出在政府實行嚴謹的無差別的政策的時候,偏向于“找市場”(江三良,2005),但是前提還是把政府的政策進行了限定,說明政府的政策對企業還是有很大程度的影響力,這就使得企業必須與政府搞好合作關系,在不損害企業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順應政府的政策的實施。企業在日常的經營活動中,為了避免政府的過度干預或者不正當的干預,會采取一些收益較低較保守的政策,這就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本文為了驗證這一觀點,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政企關系加重了產能過剩的發生
3 實證
本文選取的數據是世界銀行企業營商環境數據庫WBES中的2012年中國調查數據,針對中國的調研涉及2009-2011年25個大中城市2700家企業,其中能夠對產能過剩進行準確衡量的企業有1657家,為準確評價政企關系對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提供了可能;且該數據中詳細記錄了企業與政府之間建立聯系所使用的時間,有助于本文對政企關系進行數據上的量化,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數據上的支持。
3.1 計量模型的設定及變量的選取
3.1.1 計量模型的設定。本文的核心部分是政企關系對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y1=conj+industryj
y2=βgov1cj+conj+industryj
模型中被解釋變量yi(i=1,2)指的是企業的產能利用率,解釋變量gov1c為政企關系;Con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企業市場競爭力,企業年齡,企業員工的規模。還增加了一個虛擬變量即企業所在的行業下標j代表j企業,β為估計參數值。
其中第一個模型是零模型,只加入了被解釋變量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和控制變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政企關系這個自變量,其中被解釋變量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和控制變量保持不變。
其中,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本文使用了工具變量的方法對解釋變量進行了相應的處理。因為政企關系本身就受到很多其他變量的干擾,因此為了消除共線性,以及消除本身存在的嚴重地區差異的弊端,將政企關系這個變量取城市的均值,得到新的政企關系變量gov1c。
3.1.2 變量的選取
(1)因變量的選取。本文采用企業的產能利用率(capacity)作為因變量的衡量指標。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采用的是企業在所有可用的資源都使用的前提下,這個企業的最大產出的比例,企業產能利用率越高越說明企業存在產能過剩的可能性較小;相反企業產能利用率越低就說明企業存在產能過剩。
本文將企業產能利用率作為企業產能過剩的衡量指標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現實生產中有關企業產能過剩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企業的產能利用方面,因此直接考慮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和企業的產能產能過剩更具有針對性與現實意義;二是本文數據采用的是世界銀行的跨國數據,考慮到同一層面的可比性,我們采用中國這個國家被調查企業都披露的產能利用率,以此來增加論文數據的普遍性與可比性。
(2)自變量的選取。本文的核心自變量是企業與政府的關系(gov1c)。
政企關系(gov1c)采用的是高管處理政府監管要求所花費的時間占每個工作周的比例。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企業對于政企關系這個詞語是比較敏感的,因為如果企業公開承認其余政府之間的關系較為密切,公眾就會對該企業的合法經營性以及高官的經營能力進行懷疑,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銷售率;此外銀行也會重新考慮是否貸款給企業或者考慮給企業的貸款額度。
(3)控制變量的選取。企業規模(lnemploy)采用企業職工人數取對數來衡量。企業職工人數越多,表示企業的規模越大。
企業的年齡(lnage)采用企業成立的年長取對數衡量。以該企業作為控制變量的原因是企業存活的時間越長,企業在產品創新和改革上的需要越迫切,企業在新增投資上的需要就會越急切,就越發的需要從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獲得相應的貸款,這一系列的都會引發企業的產能過剩,所以選取該指標作為企業重要的控制變量。
企業市場競爭力(compete)采用的是企業的主要產品在主要銷售市場進行銷售時,企業的主要產品所面對的主要競爭對手的數量。
企業所在行業(industry),將其作為在虛擬變量進行分析。選取該指標做控制變量的原因是企業進入或退出某一行業比較難,企業的發展空間跟整體行業發展趨勢具有很大的聯系。
3.2 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選取是的是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問卷中中國的數據,根據數據顯示,中國的企業一共有2700家參與調查,但是由于本文使用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參與了這個問題的回答,其中能夠對企業本身進行產能利用率衡量的企業有1657家,占中國全部企業的61.37%,并且存在政企關系的企業占據了所使用數據樣本總數的61.37%,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比例,為本文的數據提供了可靠性。
為了判斷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對變量進行了Person 相關系數分析,數據分析發現政企關系企業與產能利用率是負相關的。通常而言,如果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在0.8以上,則證明變量之間存在這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會嚴重影響到回歸結果的準確性。但是分析發現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3以下,說明各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較小,不會影響到實證結果的準確性。
3.3 實證結果分析

表1 政企關系的回歸結果分析
表1是回歸結果的分析。第一列(1)空模型模型一,只加入了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其中控制變量包括企業的年齡、企業的市場競爭度、企業的規模。三個控制變量都與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
首先,企業經營年限的實證結果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經營的時間越長,會促使企業提高自身的產能利用率,就越不會發生產能過剩。原因可能是因為企業在市場上的長期穩定經營,使得企業有了不可替代的市場份額,因此企業不會擔心其生產的產品存在滯銷的問題。
其次,企業的市場競爭度的實證結果顯著為正說明企業在該主要銷售市場的競爭者數量較多的時候,企業會通過產品的創新或者服務的創新來提升企業在該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通過技術的革新來改善產品的生產流程和銷售渠道,充分利用企業的現有資源,由此提高了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從而緩解了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最后企業的員工規模的實證結果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的規模促使了企業提高了產能利用率,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大量的員工投入和技術的支持,使得企業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自然不會存在資源的浪費問題。
第二列(2)是在模型一的基礎上加入了政企關系,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企業與政府的關系越密切,企業的產能利用率越低,即政府管制加重了產能過剩的發生,該結論與假說相一致。
4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對政企關系對產能利用率的實證研究發現,政企關系提高了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即加重了產能過剩。本文的貢獻在于理清了政企關系對產能過剩的影響,便于政府采用相應的正確的措施來緩解產能過剩的發生。比如:減少企業高官的盲目投資,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較少政府的過度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