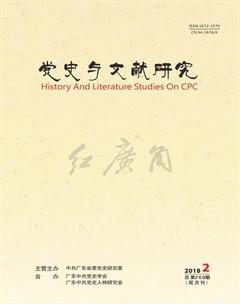中央蘇區(qū)女紅軍的群體形象與精神世界
【摘 要】“女紅軍”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特殊的女性群體,是近現(xiàn)代中國革命運(yùn)動(dòng)的重要組成部分,她們實(shí)現(xiàn)了以往女性所無法實(shí)現(xiàn)的“社會(huì)人”的權(quán)與責(zé)。那么,“女紅軍”與中國傳統(tǒng)女性的精神氣質(zhì)有何不同?她們的精神風(fēng)貌究竟如何?本文以“中央蘇區(qū)女紅軍”這一特定群體為例,從“社會(huì)性別”①的視角,揭示她們在蘇維埃社會(huì)里的群體形象與精神世界,以期揭示“紅色娘子”結(jié)構(gòu)性形象中的精神風(fēng)貌。
【關(guān)鍵詞】中央蘇區(qū)女紅軍;社會(huì)性別;社會(huì)活動(dòng);精神世界
【中圖分類號】K263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2-3570-(2018)02-0056-08
在傳統(tǒng)印記中,戰(zhàn)爭的確不是女性的主戰(zhàn)場,盡管古今中外,戰(zhàn)爭往往與女性密不可分。“女紅軍”群體形象的出現(xiàn),是社會(huì)歷史使然。筆者以為,“社會(huì)性別”視角給予女性研究以新的理論依據(jù)和思維方向,更利于從特定歷史時(shí)期“社會(huì)人”的角度把握和了解特定的女性群體。基于此,本文試圖從客觀事件、女性自身的體驗(yàn)出發(fā),去探究和展示曾給我們以“男性化的話語、男性化的打扮、男性化的性格”印象的女紅軍的精神世界。鑒于材料和學(xué)識(shí)所限,本文僅以“中央蘇區(qū)女紅軍”為研究對象。中央蘇區(qū),就是“中央蘇維埃區(qū)域”的簡稱,從核心地帶看,主要包括贛西南蘇區(qū)與閩西蘇區(qū),即西界贛江,北接贛撫平原,南鄰贛粵邊的九連山脈,東達(dá)閩西九龍江。近代社會(huì)劇變、中央蘇區(qū)等是本文述及的“女紅軍”所處的特定歷史時(shí)期與社會(huì)區(qū)域。
一、 革命激情下的狂熱、剛烈與樂觀
中央蘇區(qū)女紅軍群體性地參與社會(huì)活動(dòng):她們勇敢地舉起了槍桿子,她們火熱地參加生產(chǎn)運(yùn)動(dòng)和“支紅”“擴(kuò)紅”活動(dòng),她們積極地加入自我教育的行列,她們活躍地投入全新的文藝生活當(dāng)中,她們更過上了顛沛流離的家庭生活。革命的火種點(diǎn)燃了蘇區(qū)女性空前的社會(huì)活動(dòng)熱情,這種高漲的“紅色精神”,激發(fā)了她們狂熱的革命激情,展現(xiàn)了她們的剛烈稟性和直面艱苦的樂觀性格與革命情懷。
(一)革命激情蕩漾下的狂熱
在近代新思潮和革命形勢的啟蒙與沖擊下,中國知識(shí)女性的性別觀念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變動(dòng)。女性自身認(rèn)識(shí)變動(dòng)的一個(gè)方面,就是她們對于自身是“社會(huì)人”認(rèn)識(shí)的覺醒。如鄧穎超(天津人)、蔡暢(湖南人)、曾志(湖南人)等知識(shí)女性從不同省份進(jìn)入中央蘇區(qū)。她們作為女性參與革命隊(duì)伍的先驅(qū),是革命的宣傳者和教育者。中央蘇區(qū)當(dāng)?shù)氐呐裕缳R子珍(江西人)、康克清(江西人)、鄧六金(閩西人)、吳富蓮(閩西人)等,作為本地突出的女性革命參與者,紛紛響應(yīng)革命的號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她們從故鄉(xiāng)走向他鄉(xiāng),開始了參與革命事業(yè)的艱辛歷程。
在革命的洪流中,這些來自不同地區(qū),有著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女革命者,有一個(gè)明顯的共同特征,即擁有狂熱的革命激情。
1928年2月,曾志在郴州蘇維埃政府工作。當(dāng)時(shí)整個(gè)湘南的革命形勢喜人,以教員夫人①身份深居簡出的她也按捺不住了,狂熱地卷入激情的土地革命之中。她在后來所著的回憶錄中這么寫道:
面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我熱血沸騰,再也坐不住了。我從一個(gè)深居簡出的不為人知的教員家眷,一下成為拋頭露面的知名人物。我還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長的頭發(fā)又剪短了,脫下旗袍,換上了男學(xué)生裝,扎著紅腰帶,有時(shí)頭上裹著塊紅頭巾,背著紅纓大片刀,看起來十分威武神氣,人稱“紅姑娘”。
我經(jīng)常帶領(lǐng)一批農(nóng)民自衛(wèi)軍去抄地主豪紳的家,分掉他們的浮財(cái),打開糧倉救濟(jì)貧苦的農(nóng)民,群眾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那時(shí)我身上有著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龐然大物太可恨。工農(nóng)革命軍攻城時(shí),國民黨部隊(duì)就是依仗這城門樓阻擋革命軍進(jìn)城,這樣的地方應(yīng)該毀掉它。
于是,一陣熱血沖動(dòng),我一人抱來一堆干草,把二樓給點(diǎn)著了。本來這樣讓它往上燒就行了,可那時(shí)沒經(jīng)驗(yàn),熱昏了頭。我又跑上三樓去點(diǎn)火,當(dāng)我從三樓下來時(shí),樓梯已著火,險(xiǎn)些下不來。
當(dāng)我狼狽地從著火的門樓里跑出來時(shí),一頭撞見朱德和一大群圍觀的群眾,朱師長不解地問我怎么回事。我說:“這個(gè)城樓太可惡!妨礙革命,我把它給燒了。”
奇怪的是,朱師長竟沒說什么,只是很慈祥地笑了笑走了。
當(dāng)時(shí)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積極投身革命,他們也同樣是走極端。這些男女學(xué)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nóng)村,開展宣傳發(fā)動(dòng)工作,晚上回來卻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gè)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
不過他們并不是現(xiàn)在所說的流氓,他們既不喝酒,也不賭博,只是在國民黨封建壓迫下感到壓抑,渴求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們以為現(xiàn)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開了。
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知道此事后,大發(fā)脾氣:“這還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男女都不分開了。……這些人也是在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fā)現(xiàn)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
嚇得這些年輕學(xué)生再也不敢胡作非為了。②
曾志的這段回憶雖不是發(fā)生在中央蘇區(qū)的事情,但它體現(xiàn)的是同時(shí)期黨的一個(gè)工作區(qū)域里革命者的心態(tài),反映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政權(quán)下的人們對于革命的認(rèn)識(shí)。
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蘇維埃政權(quán)在確立之初,其革命領(lǐng)導(dǎo)者和革命民眾,存在著革命認(rèn)識(shí)上的種種誤區(qū),也出現(xiàn)了狂熱、蠻動(dòng)和偏激的行為。可舉例為證:
過去杭武團(tuán)內(nèi),由于太平觀念、和平觀念怕發(fā)展自我批評、怕發(fā)展思想斗爭,在有些地方,養(yǎng)成了一種浪漫腐化的習(xí)慣。他們提出“打破封建”、“男女平等”的口號,弄得在開會(huì)時(shí),一路來的時(shí)候就男男女女,扳頭拉頸;會(huì)后,即男找女,女找男,三個(gè)五個(gè)、男男女女共睡一床。少先隊(duì)下操做蛇脫殼、脫褲子,接塔等。假使上面事情誰怕做、誰不愿做、誰就是“封建”,就要受處罰,甚至開除隊(duì)籍。因?yàn)檫@樣來“打破封建”,使得一般青年婦女怕來下操開會(huì),有些群眾反對下操開會(huì),以至反對“反對封建”“男女平等”,對革命不滿。同時(shí)反對革命派別則乘機(jī)來作反革命宣傳(如說共產(chǎn)共妻等),企圖引導(dǎo)群眾反對革命,反對共產(chǎn)黨和青年團(tuán)。①
這類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究其原因,主要是革命初級階段和時(shí)代背景的局限使然。首先,中央蘇區(qū)革命工作剛開始時(shí),投入革命的人們是心緒紛亂激昂的。尤其是女性,她們第一次從傳統(tǒng)禮教的牢籠中解脫出來,有如脫韁的野馬,肆意馳騁,盲目地施行革命的“利器”。她們的行動(dòng)是果敢的,但她們沒有考慮所作所為的意義,更沒有考慮由此產(chǎn)生的不良影響。于是,曾志會(huì)刻意地打扮自己出眾的“男裝紅娘子”形象,拿起紅纓大片刀,意氣風(fēng)發(fā)地抄地主、打土豪。年輕男女學(xué)生們會(huì)不分男女而同睡。
其次,近代的新思潮雖然喚起了女性尋找自身解放的意識(shí),但此時(shí)《婦女雜志》《女星報(bào)》等新女性知識(shí)的宣傳并沒有真正深入社會(huì),尤其是中下層社會(huì),故此,女性追求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打上效仿男性、不分性別行為的烙印。曾志在決定由扮演教員夫人角色變?yōu)楦锩鼞?zhàn)士時(shí),會(huì)刻意脫下旗袍、以“男裝”包裝自己,年輕女學(xué)生會(huì)把“男女不分開”等同于“男女的平等”。這些表明,她們都缺乏女性社會(huì)化中的女性自我意識(shí)。
(二)剛烈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
在中央蘇區(qū)革命事業(yè)發(fā)展和鞏固過程中,紅軍女戰(zhàn)士巾幗不讓須眉,表現(xiàn)出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康克清在回憶伍若蘭②犧牲時(shí)談到:
一九二九年,伍若蘭參加在江西尋鄔縣圳下的阻擊戰(zhàn)——戰(zhàn)斗開始時(shí),她一直同朱軍長在一起,她能雙手打槍,經(jīng)常帶著兩支短槍。她和朱軍長一起掩護(hù)部隊(duì)突圍,因?yàn)樗麄冏咴谧詈螅獾綌橙说陌鼑跊_殺途中,被敵人機(jī)槍打中……她當(dāng)時(shí)身負(fù)重傷,后被敵人發(fā)現(xiàn)。敵人上來抓她。被她一槍一個(gè)連著打死好幾個(gè)。但因傷重,只能趴在地上打,被敵人從背后上來按住,奪下她的槍。她躺在地上同敵人拼死搏斗,被打得頭破血流……過了幾天,敵人從俘虜中查出了她是朱德的妻子伍若蘭,叫她供出紅軍內(nèi)部情況和行動(dòng)計(jì)劃,供出當(dāng)?shù)毓伯a(chǎn)黨的情況。她一字不露,反把敵人痛罵一頓。敵人對她動(dòng)了多種酷刑,但她堅(jiān)貞不屈。敵人看到無法使她屈服,就在二月十二日,將遍體鱗傷的伍若蘭綁赴贛州衛(wèi)府里刑場處決。她在臨行前還忍住疼痛,高呼革命口號,使圍觀的群眾流下眼淚。③
吳富蓮也是凜然就義:
一九三○年,如火如荼的工農(nóng)革命浪潮,吳富蓮成為上杭縣水口區(qū)官莊村的積極分子……一九三六年,吳富蓮?fù)镜郊t四方面軍后,擔(dān)任了女子先鋒團(tuán)的政治委員。她在一次戰(zhàn)斗中負(fù)傷,被馬鴻逵匪徒俘獲。狡猾的敵人對這個(gè)紅軍女指揮,用盡了威逼利誘的手段,先是詐稱其他被俘人員都已投降,又以官位利祿相誘,但吳富蓮?fù)窘z毫不為所動(dòng),只是輕蔑地一笑置之。敵人的兇相露出來了,惡狠狠地用馬刀對著她,脅迫她投降,吳富蓮?fù)緢?jiān)貞不屈,大義凜然,她向敵人宣布:“作為一個(gè)革命者,犧牲是早料到的!④
康克清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有一次受周恩來之命去檢查贛江邊上的一個(gè)碉堡工事。康克清到達(dá)工事以后,發(fā)現(xiàn)那里的游擊隊(duì)、少先隊(duì)、赤衛(wèi)隊(duì)?wèi)?zhàn)斗力不強(qiáng),工作被動(dòng),便在游擊隊(duì)隊(duì)長的要求下,決定第一次親自指揮戰(zhàn)斗,在整個(gè)過程中,她表現(xiàn)了十足的豪氣:
“康同志,你是總部派來的,見過世面,打過仗,請你指揮我們打一仗,可以嗎?”
他的話對我有些突然。我雖說經(jīng)歷過不少大小的戰(zhàn)斗,可是還從未指揮過戰(zhàn)斗。轉(zhuǎn)念一想,沒有誰天生就會(huì)打仗,還不都是在實(shí)戰(zhàn)中鍛煉出來的。眼前這場戰(zhàn)斗又非打不可,隨即答應(yīng)下來。
“好吧!我們大家共同打這一仗。你們一定要按照我的指揮行動(dòng)。”
……
“打了這個(gè)勝仗,管教白狗子兩個(gè)月不敢過贛江!”后來,有人因此把我稱作“紅軍女司令”……①
上述三個(gè)例子,給了我們兩個(gè)方面的認(rèn)識(shí):其一,中央蘇區(qū)女紅軍敢于自我犧牲、敢于斗爭、敢于承擔(dān)責(zé)任,她們的氣魄和勇氣都是卓絕的;其二,中央蘇區(qū)女紅軍有著“革命應(yīng)不畏犧牲”的共同信念。伍若蘭、吳富蓮的寧死不屈,康克清的慨然策戰(zhàn),既是蘇維埃革命的需要,也是蘇維埃革命精神熏陶的結(jié)果。
(三)樂觀的革命精神
在中央蘇區(qū),黨的領(lǐng)導(dǎo)人很注重文藝活動(dòng)對黨的政治綱領(lǐng)和斗爭方向的宣傳和引導(dǎo)作用。女性是文藝活動(dòng)的主要?jiǎng)?chuàng)造者和傳播者,從正規(guī)培訓(xùn)的藝術(shù)團(tuán)體、有組織的節(jié)日慶典演出,到艱苦生活中的即興演唱,無不時(shí)刻、到處洋溢著女性藝術(shù)的天賦和熱忱,體現(xiàn)著女性特有的柔韌之中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她們的這種精神內(nèi)蘊(yùn),不僅使他們熱情地投入艱苦卓絕的革命生活,鼓舞了中央蘇區(qū)的所有人員,而且也塑造了中央蘇區(qū)女性生機(jī)勃勃的光輝形象。
在蘇區(qū)正規(guī)藝術(shù)表演的培訓(xùn)和實(shí)踐方面,做出卓越貢獻(xiàn)的女干部是李伯釗②。作為革命根據(jù)地文藝工作的開拓者之一,她多才多藝,創(chuàng)作并演出了許多活報(bào)劇、話劇、歌舞:她參加演出了《黑奴吁天錄》《最后的晚餐》等戲劇,以建設(shè)和改造農(nóng)民的世界觀;演出《為誰犧牲》等戲劇,以改造改編到紅軍中的國民黨士兵的世界觀和生活習(xí)性。她參與創(chuàng)建和指導(dǎo)工農(nóng)劇社、藍(lán)衫團(tuán)戲劇學(xué)校(后稱高爾基戲劇學(xué)校)、中央劇團(tuán)等正規(guī)文藝團(tuán)體,為工農(nóng)紅軍的文藝活動(dòng)做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正如她為工農(nóng)劇社社歌作詞所倡言的:
我們是工農(nóng)兵戰(zhàn)士,藝術(shù)是我們的武器,
為蘇維埃而斗爭。
暴露舊社會(huì)的黑暗,顯示新社會(huì)的光明。
我們是工農(nóng)兵戰(zhàn)士,藝術(shù)是我們的武器,
為蘇維埃而斗爭。
工農(nóng)劇社社歌強(qiáng)調(diào)為蘇維埃而斗爭,申明工農(nóng)劇社服務(wù)于蘇維埃政權(quán)的宗旨。其時(shí),中央蘇區(qū)的“紅色戲劇”創(chuàng)作興旺,演出頻繁,深入廣大群眾。盡管演出條件艱苦,但革命樂觀精神下的辦法總遠(yuǎn)高于困難:
演出時(shí)沒燈光,演員就把松樹枝放進(jìn)鐵絲網(wǎng)里點(diǎn)燃,創(chuàng)造了舞臺(tái)照明用的“松光”;演員化妝沒有油彩,就用紅紙泡水、參和豬油當(dāng)化妝品使用,用木炭當(dāng)眉筆;樂器不夠,他們就上山抓蛇,用蛇皮做二胡。到前線演出時(shí),演員們自帶武器,隨時(shí)準(zhǔn)備參加戰(zhàn)斗。③
同時(shí),工農(nóng)劇社等蘇區(qū)藝術(shù)團(tuán)為革命事業(yè)所做出的宣傳、改造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李伯釗在回憶蘇區(qū)文藝生活時(shí)這么描述:
我記得最重要的一個(gè)戲是“為誰犧牲”,扮演的有錢壯飛,有我,還有胡底。內(nèi)容寫一個(gè)白軍被紅軍俘虜,發(fā)給遣散費(fèi)回家。在這之前他老婆不堪國民黨壓迫已逃到蘇區(qū)。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見老婆。她不愿意回家,對他說回家只能給白軍當(dāng)炮灰,而紅軍打仗,是為了田地,最后這個(gè)白軍參加了紅軍,情節(jié)很曲折,故事也很悲慘。把兩萬多人集中在云集區(qū)、關(guān)倉下、九堡三個(gè)地區(qū),每天三場為他們演出,這個(gè)戲演到哪里,哭到哪里,只要演戲,下雨天有人看,場場有人看,場場哭。收到了很大的效果。④
在節(jié)日慶典中,蘇區(qū)女干部除了忙于基本的個(gè)人工作事務(wù),還積極籌辦節(jié)日里的文化娛樂活動(dòng)。曾志回憶在井岡山時(shí)的文藝活動(dòng)片斷:
我到醫(yī)院(中井總醫(yī)院)不久,正趕上過新年,為了讓傷病員高高興興地過年,我們在中井前面的半山坡,用木料搭了個(gè)臺(tái),舉辦了一個(gè)新年娛樂晚會(huì)。除傷病員外,周圍的老百姓有很多人來看熱鬧。當(dāng)時(shí)革命歌曲不多,主要是沒有人編寫,因此只好唱一些北伐時(shí)的歌曲,例如像《打倒列強(qiáng)除軍閥》一類的歌,本地戰(zhàn)士唱了當(dāng)?shù)氐纳礁琛V饕墓?jié)目是演戲,戲是自己編的,演一些土豪劣紳怎么欺壓窮人一類的戲。因?yàn)槭沁^新年,不能光演憶苦的節(jié)目因此也穿插著一些逗樂的節(jié)目。我扮演了一個(gè)很厲害的老太婆,虐待媳婦,待人兇狠,最后沒有好下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在娛樂的同時(shí)也受了教育。①
一方面,女干部的樂天與細(xì)心安排,使得戰(zhàn)士們在節(jié)日里能有充實(shí)歡娛的時(shí)刻;另一方面,女干部們的熱忱奉獻(xiàn)與擔(dān)當(dāng),對安定軍心、教育和團(tuán)結(jié)民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蘇區(qū)艱苦戰(zhàn)斗的婦女,在火熱的戰(zhàn)斗歲月里,時(shí)刻洋溢著女性天然的生活美感。蔡暢回憶了江西蘇區(qū)婦女的生活片斷:
江西婦女還組織起擔(dān)架隊(duì)、運(yùn)輸隊(duì)、看護(hù)隊(duì)、洗衣隊(duì),直接支援戰(zhàn)爭。她們不斷把糧食、鹽、菜、槍支彈藥,運(yùn)上前線;再把傷員運(yùn)回鄉(xiāng)里治療護(hù)理;前方打了勝仗,她們就興高采烈地把戰(zhàn)利品運(yùn)到后方來。在江西蘇區(qū),無論大道上、小路間,都可以看到她們同男子一樣奔忙,身后常常灑下一串串悅耳的革命歌聲。②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從中央革命根據(jù)地進(jìn)行戰(zhàn)略轉(zhuǎn)移。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各個(gè)方面軍的女紅軍依然展現(xiàn)著突出的革命樂觀精神,在行軍轉(zhuǎn)移、救護(hù)運(yùn)輸、前線作戰(zhàn)中無不起著強(qiáng)大的宣傳鼓舞作用。
1934年冬,中央紅軍來到湘桂邊境準(zhǔn)備攀登老山界。這座高峰海拔2000公尺以上,行軍非常艱難。女戰(zhàn)士危拱之通過改編鳳陽花鼓戲來激勵(lì)紅軍戰(zhàn)士們:“紅軍強(qiáng),紅軍強(qiáng),千難萬險(xiǎn)無阻擋;行軍路上揍老蔣,北上抗日打東洋。咚咚鏘,咚咚鏘。”許多戰(zhàn)士都被這朗朗上口的歌曲所吸引,邊走邊哼,以解除連日翻山越嶺帶來的疲憊之感。
李堅(jiān)真等女戰(zhàn)士長征途中自編自唱,鼓舞部隊(duì)斗志,過金沙江時(shí),她們唱道: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拉手來心連心
階級姐妹團(tuán)結(jié)緊
不怕敵人百萬兵③
考察中央蘇區(qū)女紅軍在革命政治、軍事文化生活里的這些實(shí)例,我們清晰地感受到:同樣的革命生活、同樣的戰(zhàn)爭苦難,蘇區(qū)的“紅色娘子”以女性所特有的細(xì)膩、對生活天然的熱忱和敏感的體悟,展示出催人向上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譜寫和述說著紅色蘇維埃的精神之歌。
二、革命激情與女性氣質(zhì)糾結(jié)的精神苦痛和情感變異
在革命戰(zhàn)爭中,女性的革命激情是空前高漲的。但是,中國傳統(tǒng)女性對家庭、情感、孩子的顧念和深愛,女性所特有的細(xì)膩和柔情,在很大程度上與革命事業(yè)中所需投注的精力及顛沛流離的革命生活有著很大的沖突,從而在革命女性身上折射出革命激情與女性氣質(zhì)糾結(jié)的精神苦痛和情感變異。
(一)苦痛——來自革命斗爭和行軍生活中不穩(wěn)定的婚姻生活
由于革命工作需要,許多女干部常常和丈夫異地工作,或者盡管工作在同一地方,但由于工作環(huán)境所迫,過著尷尬的婚姻生活。為此,她們必須忍受難以煎熬的精神苦痛。
曾志回憶了她在中央蘇區(qū)時(shí)期艱難的婚姻生活:她先是在對戀愛毫無準(zhǔn)備之際,迫于輿論和夏明震結(jié)婚。不久,夏明震為革命犧牲了。之后,曾志和蔡協(xié)民結(jié)合,但因?yàn)楦锩ぷ餍枰瑑扇私?jīng)常分分合合,加上蔡過于重視曾志而使她產(chǎn)生精神重負(fù),終于使得兩人走向分手。不久,蔡也犧牲了。再以后,曾志和陶鑄結(jié)合,雖然兩人深深相愛,但革命的特殊生活仍然使曾志籠罩在苦痛的婚姻生活之中——
一九三三年的三月,上海中央局來了個(gè)通知,叫陶鑄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陶鑄當(dāng)時(shí)是不可能知道王明的意圖的,但他知道將要和我分手了。
在此之前,我們這對假夫妻還真沒有象樣地廝守在一塊。我到福州后已懷孕,接著生孩子,坐月子,這期間又受處分搬出了機(jī)關(guān),單獨(dú)住在互濟(jì)會(huì)。陶鑄也經(jīng)常下鄉(xiāng)巡視,我們難得呆在一起。而現(xiàn)在孩子剛送了人,身體剛復(fù)原,卻又要分手了,也不知何時(shí)才能再相聚,我們彼此心中都有無限的依戀。
陶鑄臨行前,在一個(gè)旅館租了個(gè)房間,我們象真正的夫妻那樣,恩愛相依,共同度過了十天幸福的“蜜月”。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在旅館門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難分難舍。
剛開始時(shí),我每周能收到陶鑄從上海寄來的兩封信,信雖簡短但充滿熱烈的感情。來了四五封后,突然就斷了消息。我每天翹首等待,等啊,盼啊……①
彭儒②敘述了在蘇區(qū)結(jié)婚前后的景況:
我們結(jié)婚時(shí),既沒有房子,也沒有床和被子,暫借了傅穆姐姐的房間,更談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婚后,我仍然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我也沒好意思把這事告訴她。過了兩天,正人去找我,克清覺得奇怪,說“這是怎么回事啊?”正人高興地告訴她:“我們不久前已經(jīng)結(jié)婚了。”克清裝著生氣的樣子,輕輕地打了我一下,說:“你這個(gè)小鬼,這么大的事也不告訴我一聲。”說得我的臉都紅了。③
曾志和彭儒的回憶,都說明了在中央蘇區(qū)革命的日子里,夫妻的分分合合、居無定所都給正常的婚姻生活帶來了不便與苦痛。此外,愛人間別離的思念之苦、彼此安危掛念的焦灼,也給蘇區(qū)女干部帶來了無盡的精神苦痛。
同時(shí),蘇區(qū)與外界間的隔離,使得消息往往滯后或斷絕,這也導(dǎo)致蘇區(qū)女性遭受不少情感的磨難。以賀子珍為例,她深愛著毛澤東,在她不確定楊開慧是否已為革命犧牲時(shí),與毛澤東戀愛并結(jié)婚了。在剛結(jié)婚的幾年里,她保存著一個(gè)已收拾好的、可以隨時(shí)帶走的布包,原因是如果楊開慧來了,她隨時(shí)可以離開。1929年,毛澤東率領(lǐng)紅四軍下山打擊敵人,留下彭德懷、滕代遠(yuǎn)的紅五軍和王佐領(lǐng)導(dǎo)的32團(tuán)守衛(wèi)井岡山時(shí),賀子珍曾經(jīng)決心留下來不走,與他們一起堅(jiān)持井岡山的斗爭。她的動(dòng)機(jī)之一是:她已知道,楊開慧犧牲僅是誤傳,毛澤東下山后可能與楊開慧重新恢復(fù)夫妻關(guān)系。④聯(lián)系以后的歲月里,賀子珍為情所困、為情而癡狂的事實(shí),不難理解善良、用情專一的賀子珍在與毛澤東擁有共同生活的歲月里,還在忍受著情感世界里的深重磨難!
(二)苦痛——來自無法承受的母性之愛
為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jù)地,紅軍的流動(dòng)性很大,革命工作的任務(wù)超常繁重, 環(huán)境異常惡劣。女紅軍生下的孩子不可能留在部隊(duì),只能送給當(dāng)?shù)乩习傩眨蛘呤撬突乩霞摇榇耍t軍,尤其是女紅軍中的女干部,絕大多數(shù)經(jīng)歷了革命工作與母愛難以兩全的沖突,在她們的情感世界里,留下了永遠(yuǎn)無法抹去的遺憾和傷痕。
在賀子珍日后的回憶錄里,反映出革命工作與母親角色的沖突,造成了她無法愈合的傷痛。王行娟根據(jù)賀子珍的回憶錄,寫了以下這段話:
毛澤東是個(gè)大才不拘小節(jié)的人,他可以對一個(gè)普通老百姓的命運(yùn)落淚,但他不一定理解自己的妻子默默無聞的奉獻(xiàn)與犧牲,體會(huì)到一個(gè)女人十年生六個(gè)小孩子從精神到肉體的痛苦。他用不生育或者少生育的延安有才干的女干部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賀子珍,又會(huì)覺得她終日圍著孩子、炕頭轉(zhuǎn),婆婆媽媽,嘮嘮叨叨,目光短淺,毛澤東同賀子珍一吵架,就說她‘你政治上落后‘你思想不進(jìn)步,這些都深深地刺傷了賀子珍的自尊心。賀子珍賭著一口氣要上抗大學(xué)習(xí),要去蘇聯(lián)學(xué)習(xí),這不能不是一個(gè)原因。①
這段話旨在分析賀子珍與毛澤東婚變的原因,但它同時(shí)也反映了作為一名紅軍女干部與多產(chǎn)的母親的矛盾,這兩種身份難以很好地結(jié)合為一體。作為一位合格的母親和領(lǐng)袖的妻子,她失去了成為優(yōu)秀革命者的機(jī)會(huì);而如果全力地投入革命當(dāng)中,作為合格母親的角色又必然丟失。為此,賀子珍做出了出走的痛苦選擇,也為這選擇,賀子珍又陷入了終身無法挽回的情感和精神苦痛之中。
曾志在其回憶錄里,也多次反映了身為母親和女革命者的矛盾:
那段日子(一九三一年),我邊工作邊帶孩子,緊張工作之余,享受著難得的天倫之樂。但好景不長……原來我們還沒有到廈門時(shí),廈門中心市委急需經(jīng)費(fèi),聽說我們剛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組織決定,已將孩子‘送給一個(gè)叫葉延環(huán)的同志。葉延環(huán)的家是有名的中醫(yī),而且還暗地里做些大煙生意,比較富裕。他結(jié)婚四年未有生育,很想領(lǐng)養(yǎng)這個(gè)孩子。黨組織已預(yù)收了一百塊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如今要送人了,今生今世難說再見到,我的心情也是難以言喻的。②
時(shí)隔一兩年(1933年),曾志再次生子,卻又不得不送人——
由于當(dāng)時(shí)自己的處境并不好,加上身體狀態(tài)極差,這第三個(gè)孩子也象前兩個(gè)孩子一樣,在生下來的第十三天,就不得不送了人。當(dāng)時(shí)我總認(rèn)為,一個(gè)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應(yīng)該一心撲在工作上,不該花那么多時(shí)間和精力去帶孩子。現(xiàn)在看來這種思想確實(shí)太偏激了。③
曾志關(guān)于為黨組織賣子、為工作送子的回憶,都體現(xiàn)了女革命者和母親角色兼顧的兩難。時(shí)隔多年,革命成功以后,這些曾經(jīng)的蘇區(qū)女紅軍干部都表現(xiàn)了異常的苦楚和對孩子的深深歉疚。
鄧穎超第一次懷孕以后,因工作忙,又怕影響了周恩來的工作,便自作主張把孩子流產(chǎn)掉了。為此,鄧穎超落下了病根,再也無法生育。撇開精神的苦痛不說,單單是對身體的摧殘,也足見革命工作與母親角色難以同時(shí)兼顧。
由于革命工作和母性角色的沖突,蘇區(qū)女紅軍干部中還出現(xiàn)了把孩子當(dāng)成包袱的現(xiàn)象。
1936年4月,康克清在接受海倫·斯諾的采訪時(shí)說:“我不想生孩子,我要保持健康的軍人體格。”同時(shí),在康克清回憶錄里,她的內(nèi)心獨(dú)白卻是:“我喜歡孩子,也很想有個(gè)孩子。但怕有了孩子影響事業(yè)。”④
在蘇聯(lián)養(yǎng)傷和學(xué)習(xí)時(shí),賀子珍因喪失愛子,久久不能自拔。一次,她問蹇先任是否為第一個(gè)死去的孩子而難過時(shí),蹇先任說:
我的孩子死了以后,我沒有時(shí)間想念他。那時(shí)戰(zhàn)爭環(huán)境很殘酷,我得把全部精力用在干革命上。在我工作的時(shí)候,我就忘掉了孩子。另外,如果一個(gè)女同志婆婆媽媽,整天想著孩子,要被別人瞧不起,不給分配工作的。孩子的死去,對我是一種解放,我就不用為孩子分心了。①
康克清和蹇先任的話語反映出,為了革命事業(yè)的需要,女紅軍干部們接受了孩子是革命事業(yè)累贅的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與傳統(tǒng)女性母性情感相沖突時(shí),要么引發(fā)女干部兩難的痛苦,要么便是女性母性的變異——不愿意要孩子,或者成為缺失“母性”的母親。
(三)變異——性別意識(shí)的淡薄
女紅軍打破了傳統(tǒng)的女性觀念,她們以“社會(huì)人”的姿態(tài)積極投入革命洪流當(dāng)中,在階級斗爭與革命事業(yè)的糾結(jié)中,在男性領(lǐng)袖引導(dǎo)方向的過程中,女紅軍的性別意識(shí)是淡薄的。
行動(dòng)上,她們參加紅軍,以“紅色娘子軍”的形象作戰(zhàn);她們積極參加生產(chǎn),破除了傳統(tǒng)的觀念;她們積極參與擴(kuò)紅、支紅的工作。為著與廣大勞苦男性一樣的階級苦難,而不是為著“女性群體”的利益,她們大打土豪劣紳。女干部的政治話語是階級化的,她們言必稱自己是舊社會(huì)的受害者;她們的打扮是男性化的,她們沒有區(qū)別于男性戰(zhàn)士的服裝;性別意識(shí)是淡化了的,她們從沒有區(qū)別于男性的生活要求。
女性性別意識(shí)的淡化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女性性別意識(shí)的缺失和由此而來的對男性行為的絕對認(rèn)同與效仿。以危秀英②為例,她在回憶紅軍行軍時(shí)說:
回憶起來,那時(shí)天天行軍打仗是很艱苦的,我們處處跟男同志一樣,甚至比他們還要多干許多事。一樣的行軍后,我們要趕到前面駐地,別人休息了,我們還要招呼掉隊(duì)的同志。在外表上,我們把短頭發(fā)全塞在軍帽里,男同志也很少顧及我們是女同志,或者根本忘記了我們是女同志。露天宿營,我找個(gè)地方,和衣往地上一躺就睡著了。遇到夜里下大雨,我就找三個(gè)男同志,四人背靠背站著睡。沒有雨傘和油布斗笠時(shí),任大雨淋得一身濕透,大家照睡不誤。③
危秀英還在訪談錄中說:
在整個(gè)革命生涯里,我一共負(fù)過三次傷。第一次是在江西吉安,剛參加紅軍時(shí)。去打仗,子彈從我的頭皮上穿過去,沒達(dá)到骨頭里面,我只是拿了一塊布包著頭。我拼命要參加毛澤東和朱德的紅軍,因?yàn)榧t軍是窮人的大救星,只有參加紅軍才能為我爸爸媽媽報(bào)仇。那時(shí)代我不曉得什么是怕,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dāng)女的看。男的能打,我也能打。我跟著那些男孩子一起打仗。④
“紅軍是窮人的救星、參加紅軍能給父母報(bào)仇”的樸實(shí)思想和觀念,體現(xiàn)了廣大勞苦婦女參加工農(nóng)紅軍革命的初衷是為了解除苦難本身,而并沒有謀求女性個(gè)體解放的女性意識(shí);在這種為解除“受壓迫的苦難”而斗爭的歷程里,女紅軍忘卻了男女生理的、社會(huì)的一系列界限。在她們的精神領(lǐng)域里,革命——打仗是第一要素的,是最具號召力的。在這個(gè)意義上說,階級革命與婦女運(yùn)動(dòng)結(jié)合在一起,并超越了婦女運(yùn)動(dòng)本身。
(李雪華,歷史學(xué)碩士,福建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