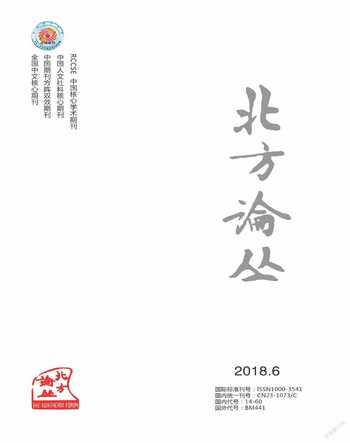周的史詩:《大雅》“五詩”的敘事特質
鄭曉峰
[摘要]《大雅》“五詩”集中體現了周的史詩或詩史的敘事性質。既有史的因子,又有詩的想象成分;既用韻文,又夾雜著神話與故事傳說,是詩化的歷史。對照亞里士多德史詩的定義,中國式史詩帶有強烈抒情色彩的敘事性、片段組接的完整性,以及精神意識中的民族性,是歷史的詩化。《大雅》“五詩”是在時間鏈條上,隨著地理空間的轉換,組接成周族發展史上波瀾壯闊的歷史瞬間,成為這個民族在夢境里、廟堂上、祭壇中無數次被喚起的集體的精神原型。
[關鍵詞]史詩;《大雅》五篇;敘事特質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6-0058-05
“史詩”的概念最初是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的,在第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章中涉及有關史詩的評述,現撮要如下。
亞氏將史詩與悲劇、喜劇等相提并舉,認為史詩的情節也應像悲劇的情節那樣,按照戲劇的原則安排,環繞著一個整一的行動,有頭,有身,有尾,這樣才能像一個完整的活東西,因這種完整的結構而帶給我們審美的快感。史詩應該不像歷史那樣按照時間順序那樣結構,然而,幾乎所有的史詩詩人都成為編年史家,荷馬就是個例外,并不把戰爭整個寫出來。史詩采用敘述體,是敘事詩,并且用“韻文”模仿的藝術,分為簡單史詩、復雜史詩、性格史詩和苦難史詩。史詩里必須有“突轉”“發現”與苦難。史詩比較能容納不近情理的事,一樁不可能發生而可能成為可信的事,比一樁可能發生而不可能成為可信的事更為可取。綜合亞氏對史詩的界定,可以看出史詩應該具備完整的結構,能容納不近情理的事,情節中要有“突轉”“發現”與苦難等內容,用“韻文”,能帶來的審美快感,可以有一定的編年體結構,規模宏大。亞氏側重在情節角度開掘史詩的內涵。馬克思則把歌謠、歷史傳說和神話(詩神繆斯)視為史詩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這是標志史詩的本質要素[1](p.224)。亞氏“不近情理的事”近似于馬克思所說的神話與歷史傳說,用“韻文”略似于歌謠。
比對這些標準,可以見出:從詩的體制看,《詩經》中的任何單篇都無法和《荷馬史詩》相比,但是,以韻文的形式講述本民族起源時期的神話和歷史傳說,《詩經》中還是有些篇目頗符合史詩的品格的。
陸侃如認為,《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五篇合起來,可成一部雖不很長而亦極堪注意的“周的史詩”[2](p.31)。若是“周的史詩”,勢必涉及周民族的起源神話、歷史傳說,《大雅》五篇無疑為此提供了大量的文獻支撐。下面結合其他文獻材料,簡單勾勒周民族的發展史,見出《大雅》五篇的“史詩”敘事特質。
一、“厥初生民”:周民族的起源
維柯說:“在一切民族中神諭都是用詩來答復祈求者。因此我們發現到這種凡俗智慧的奧義都隱藏在神話寓言里。在這方面我們窮究到后來哲學家為什么重新發現古人智慧的強烈愿望,以及他們在什么場合里把自己的隱藏的智慧塞進寓言故事里去。”[3](p.32)一切民族都是富有詩性智慧的,用詩來傳達神諭,記錄民族的起源史。用詩記錄的神話寓言,充滿著古人的詩性智慧。卡希爾說:“一個民族的神話不是由它的歷史確定的,相反,它的歷史是由它的神話決定的。”[4](p.6)“生民”就是生人,《生民》即用詩的形式載錄了周民族的起源神話,這個神話進而決定了“它的歷史”。《生民》全詩八章,前二章寫了后稷出生的神話: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災)無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周民族的始祖后稷是上帝與姜嫄所生的,姜嫄郊禖求子,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到郊外踏到上帝的大拇指印而心有所感,于是懷胎十月,頭胎生子很順利,產門未破未裂,沒有什么災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鄭《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征,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正義》引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王肅又引馬融曰:“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5](pp.1264-1249)朱熹說:“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訴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6](p.190)陳奐也說:“此承上章言姜嫄可禋祀上帝,而上帝亦將安樂其禪祀,居然生子,謂生后稷也。”[7](p.3)綜合幾家觀點來看,神話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體化,姜嫄安然產子原因在于上帝安樂接受姜嫄禋祀的結果。這段起源神話里充滿詩性之思,隱喻著周民族起源的秘史,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轉換的觀念折射。
從事農業生產的部族,皆尊社神與稷神。社指土地之神,稷指百谷之神。周民族“郊祭”后稷,因為“稷勤百谷而山死”,是“有功烈于民者”,所以按照圣王制定祭祀禮節的原則看,“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扦大患則祀之”。后稷以死勤事,繼承烈山氏之子柱“殖百谷百蔬”的事業,得到后代的祭祀,“故祀以為稷”[8](pp.154-158)。這也就表明當時是農業社會,《生民》第四五六章重點強調“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的具體做法。除去田間雜草,選擇良種播種,吐芽含苞,茁壯長高,顆粒飽滿。農業豐收,于是在有邵安家。《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西周之國,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臺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后稷推廣上天降下的百谷良種,遍地收獲秬子、秠子、糜子、高粱。糧食滿倉,豐收之時,后稷創立了祭祀之法,感恩上帝的護佑,讓上帝歆享來自祭品的香氣。這些內容表明后稷是農神,在周民族農業社會的發展初期,為之做出巨大貢獻,因而會得到后代的祭贊。
《周禮·春官·大司樂》在列舉祭祀的樂舞時,提到在祭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與先祖之外的祭祀先妣的樂舞,例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鑊,以享先姚”。鄭玄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9](p.685)從周民族單獨設閟宮祭祀先姚姜嫄和尊后稷為始祖的這些情況看,這反映了周民族初始階段恰恰經歷由母系氏族發展到父系氏族的過程。結合農業社會的背景,男子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漸趨凸顯的實際情況,可以說,后稷恰恰就是處在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轉折點上,是周民族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
二、“自西祖東”:周民族的遷徙
后稷在“有邵”安家立業,“邰”的地望,據《說文》說“邰”是“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其母姜嫄即有邰氏之女也。《毛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但《史記·周本紀》卻說舜“封棄于邰”。無論封者是堯還是舜,總之,后稷“即有邰家室”。據《漢書·地理志》載為漢代右扶風斄縣,斄、邰音同通用,“周人作邵,漢人作斄”,古今字不同而已。“《渭水注》渭水自武功來,東徑斄縣故城南,舊部城也。后稷之封邑矣”。“《一統志》,故城今武功縣西南。吳卓信云,康海《武功縣志》,古邰城在武功縣八里,漢邵城在縣西南三十里”[10](p.47)。“邰”的地望,確切說,應在今陜西武功、扶風間。
《公劉》記誦了一件大事就是將都城由邰遷到豳。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毛傳》:“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于豳,而有居民之道。”《正義》對此詳加解釋:“后稷封于邵,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于邵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后,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于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斗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于漢屬右扶風為構邑縣,則是中國之地。”[5](pp.1303-1306)由此看來,從后稷到公劉從沒有遷徙過,一直居于邰地。在公劉時代,始遷豳地設立館舍。“篤公劉,于豳斯館”。這個“館”在《綿》中說的更為具體,“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鄭《箋》:“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5](p.1306)建館當由這種卿官處理。先立室家,后來設立嚴正的宗廟,統稱為“館”。由此,可以推知,周代的宗法制可能在公劉時代已經開始,在公亶父時代漸趨定型。
《綿》則記誦了在周民族遷徙史上,另一位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公亶父,將都城由豳遷到岐山,定都周原。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直父,陶復陶兄,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麥及姜女,幸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茶如怡。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茲。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自西租東,周爰執事。
古公亶父經過崔述的解釋,當為公亶父。崔述曰:“《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11](p.165)這樣公宜父就與公劉、公非、公叔祖類一樣,其后公季亦與之貫通一致。公亶父遷都岐山,岐山的地望,按《漢書·地理志》記為“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其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渭水注》記載:“橫水出杜陽山,為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大巒水,俗稱小橫水,通為岐水,徑岐山西,又屈徑周城南,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東人雍水。雍水自雍來,東南合橫水,又南徑中亭川合杜水,又徑美陽縣西,人渭……《一統志》,故城今武功縣西南。”[10](pp.48-49)鄭《箋》在解釋“綿綿瓜貶”時,也提到周民族遷徙至據此岐山前的情況,“后稷乃帝嚳之胃,封于邵。其后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綿綿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自于沮、漆也”[5](p.1148)。至此,公亶父東進路線圖初步形成。從豳地(構邑縣)出發,渡過徑水,向西南行,越過乾縣的梁山,過杜陽川,沿著漆水南下,再向西折,沿渭河西行,定局在扶風北、岐山一帶[12](p.45)。從《公劉》到《綿》,由部遷豳,再遷岐,是什么原因促成周民族的一再遷徙,成為困擾學術界的一大難題。
《正義》解釋《公劉》是因為躲避夏人之亂而遷居豳地的。至于《綿》公宜父遷都的原因,據孟子說“太王事獯鬻”。以皮幣、犬馬、珠玉侍奉狄人,皆不得免。為避災而遷都。當然,我們在文本中可以找到內證,“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皆筑城垣之事”,但僅從避敵這一點上解釋兩首詩的遷都問題,顯然還是不夠的。《公劉》開篇有“匪居匪康”,鄭《箋》:“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這種解釋法與《生民》中“不寧”“不康”釋為上帝安樂其禋祀相類。朱熹也解釋為“不敢寧居”。楊寬據此認為:“他的遷都的行動,是積極的,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振興周族,鞏固和擴大這個新建的國家。”[13](p.29)這從詩本身可以看到這一點,遷都豳地,發現京師田野形勢好,定居建新房,“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靚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豳地地勢平坦,水源充沛,開荒種地,“徹田為糧,度其夕陽”。我們再看,《綿》詩中亦有發展生產的詩句。“周原膴膴,堇茶如飴”“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周原是一個天然黃土農業區,土地肥沃,生長的苦菜如飴糖。《說文》:“堇,草也,根如芥,葉似細柳,蒸食之甘。”茶,即苦苣。開荒種地,丈量天地,一片繁忙的景象。楊寬的分析還是比較寬泛,李亞農的觀點則更為具體,周民族自西而東的遷徙與殷自東往西的遷徙一樣就是為了爭奪黃土層地帶,而由黃土層的邊緣走向中心[14](pp.6-22)。加之,原居住地的多年耕作,土地板結等原因帶來農作物的大量減產,亟須開拓新的土地,這無疑拉動了整個民族遷徙的步伐。
李亞農在分析了周民初諸民族的分布后,尤其是系統分析了周族分封子弟諸侯國的地望,大體都集中在主要的黃土層地區,進而得出這一結論很有啟發性。基于此,《正義》中提到的“平西戎”或可這樣理解,在殷商之時,羌、狄實力都比較強,周民族可能被羌族壓迫而依附狄人,進而或可認為它本身就是戎狄。若此,就不存在平定之說,故婉轉說成“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
伴隨著攫取物質利益的腳步,精神層面的掌控也在繼續。張光直先生提出一個極富創意的解釋,提出用政治的因素來解釋三代都城的遷徙。“王都屢徙的一個重要目的——假女口不是主要目的——便是對三代歷史上的主要的政治資本亦即銅礦和錫礦的追求”,“從這個觀點來看三代,則三代中第一個朝代夏代崛起于晉南,第二個朝代商代之自東往西,及第三個朝代周代之自西往東的發展趨勢,就都很快地顯露出來嶄新的意義”[15](pp.122-123)。青銅器是政治斗爭的必要手段,誰掌握青銅器,誰就擁有了通神的手段,誰就是天下精神的實際掌控者。筆者以為,周民族東進的遷徙路徑,恰恰表明了周民族在物質與精神方面操控天下的決心,當然,實現的過程必然充滿著血與火的艱辛。
三、“萬邦之方”:周王朝的建立
周民族定都岐山周原后,土地肥沃,膏腴千里,株馬厲兵,蓄勢待發,著手進行一系列的兼并戰爭。從季歷的開疆拓土,到武王定鼎中原,前后用去了三代人的時光。在《皇矣》《大明》中,清晰地展現了周民族兼并戰爭的歷程。
《皇矣》記述了太王(公宜父)定居岐山后,打退來犯的串夷(《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受命既固”的史實;次敘王季“其德克明”而“王此大邦”,“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承先祖遺德,傳位文王的史實;末述文王伐密伐崇,成為“萬邦之方”的史實。
關于太王(公亶父)的功績,除了上文提到的內容以外,更重要的便是“居岐之陽,實始剪商”(《魯頌·閟宮》)。這種奠基的作用,非同尋常。
關于王季的功績,《古本竹書紀年》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16](p.9)《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從中可以見出王季對西北鬼方的征伐,克敵制勝的戰果輝煌;另外,這也標志著在武乙時期,周民族的軍事勢力達到使大邦殷震驚的程度。較之武丁時期,周民族的發展進步是異常顯著的。殷商武丁時代的確是其強盛時期。在卜辭中,有武丁曾命人伐周的記載。貞:令多子族暨犬侯璞周載王事(《合集》6874);癸卯卜:其克災周,四月(《合集》20508);惠御伐周(《合集》22294)。殷商派人監視周及羌人,說明周民族的力量在當時實在是難以和殷商抗衡。從武丁到武乙,經過祖庚、祖甲、馮辛、庚丁殷商等四代國君的統治,周民族與之既對抗又服從,最終具備了使殷商震驚的軍事力量。到了文王時代,先后對外用兵,按《尚書大序》說:“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同年被紂囚禁,五年被釋,克耆(即黎),六年伐崇,同年稱王。”詩歌在寫作時,從選材角度看,常抓典型材料。如伐密伐吠夷(即串夷)伐崇,其他則略而不寫,可以見出作者的選材之功。《文王有聲》:“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文王在攻克崇后,沿著渭水向東,遷都到豐。《說文》:“鄂,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即今陜西西安西南灃河中游西岸。文王在去世的前一年完成伐殷的戰略部署。
《大明》從文王出生寫到武王出生,都強化了父母的美德善良,才會生此賢良。最后重點介紹了牧野之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鋪排介紹了牧野之戰的三軍,威武雄壯的姿態,以及一舉擊潰殷商大軍,取得勝利的情況。在這個黎明時分,天上出現了“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的奇異景象,周武王率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與商紂王的70萬大軍鏖戰牧野,攻占朝歌,殷商王朝徹底覆滅。
按照《史記》所載,從始祖后稷起,至周文王,共巧代。15代顯然不能窮盡從虞夏之際的后稷到文王之間漫長的歷史。這份歷史明顯帶有詩性之思,是詩性的歷史,也并不完全是在確指的時間、確定的空間中探討完全真實的歷史,但這畢竟是帶有人類早期童年生活印象的歷史。《詩經》這組周民族史詩恰恰就是如此,選材集中在周民族發展史上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六位英雄帝王身上,凸顯了他們帶領周民族人民篳路藍縷,夙興夜寐,艱苦奮爭直至走向輝煌的創業歷程。既有史的因子,又有詩的想象成分;既用韻文,又夾雜著神話與故事傳說,具備史詩的本質要素。然而,黑格爾卻說:“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因為他們的觀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從有史以來最早的時期就已形成一種以散文形式安排得井井有條的歷史實際情況,他們的宗教觀點也不適宜于藝術表現,這對史詩的發展也是一個大障礙。”[17](p.170)在黑格爾看來,中國人的觀照方式常“采用專門著眼實體的觀照方式”,宗教觀點中強調人與神的關系,在中國早期作品中二者還不是真正理想的關系,只有人的行動,而無神的行動,在藝術表現力上顯得枯燥而無生機。加上在詩歌敘事中還沒有大量的“節外生枝”,“只是用枯燥的散文方式,把某一系統的神話故事順序排列在一起,從世界和神的起源說起,往下一直說到一些英雄和王侯的家譜,結果使古代神話核心蒸發消散掉,同時使出自夢境的幻想奇跡,以詩的辭藻和形式,表現為寓言式的格言,其主要任務在于宣揚一些關于道德和人情世故的教訓”[17](p.171)。這是黑格爾對中國“史詩”存在的問題進行的批評,錢鐘書也認同黑格爾的說法,直接指出:“中國沒有史詩,中國人缺乏伏爾泰所謂‘史詩頭腦”中國最好的戲劇詩,產生遠在最完美的抒情詩以后”[18](p.532)(《談中國詩》)。即使中國的“史詩”雖不是黑格爾所說的嚴格意義上的史詩,但是,中國式“史詩”還是符合黑格爾給史詩下的定義:“‘史詩在希臘文里是Epos,原義是‘平話或故事,一般地說,‘話要說出的是事物是什么,它要求有一種本身獨立的內容,以便把內容是什么和內容經過怎樣都說出來。史詩提供給意識去領略的是對象本身所處的關系和所經歷的事跡,這就是對象所處的情境及其發展的廣闊圖景,也就是對象處在它們整個客觀存在中的狀態。”[17](p.102)對照史詩的定義,中國史詩帶有抒情色彩的敘事性、片段組接的完整性,以及精神意識中的民族性,這些史詩要素還是能夠保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錢鐘書僅側重在抒情詩的視角看中國詩,缺少對詩歌敘事性的分析,所得結論還是不周延的。
據此可以說,《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是在時間鏈條上,隨著地理空間的轉換,以如同電影剪輯般的畫面組接成周民族發展史上波瀾壯闊的歷史瞬間,定格了一段真實而鮮活的周民族童年的記憶,“不再是教科書上的白紙黑字,而是以立體、豐富、具象化的方式跨越漫漫歷史長河,擁有歷久彌新的生命力”[19](p.8),成為這個民族在夢境里、廟堂上、祭壇中無數次被喚起的集體的精神原型。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3][意]維柯.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4][德]恩斯特·卡希爾.神話思維[M].黃龍寶,周振選譯.柯禮文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5]李學勤整理.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朱熹.詩集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7]陳灸.詩毛氏傳疏:卷24[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8]徐元浩.國語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2.
[9]李學勤整理.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0]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崔述.崔東壁遺書·豐鎬考信錄:卷1[M].顧頡剛編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陳全方.早周都城歧邑初探[J].文物,1979(10).
[13]楊寬.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4]李亞農.西周與東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5][美]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增訂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16]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逸周書古本竹書紀年[M].濟南:齊魯書社,2010.
[17][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8]錢鐘書.錢鐘書散文[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19]王源.中國傳統文化的具象化傳播:原創性電視節目發展的新路徑[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