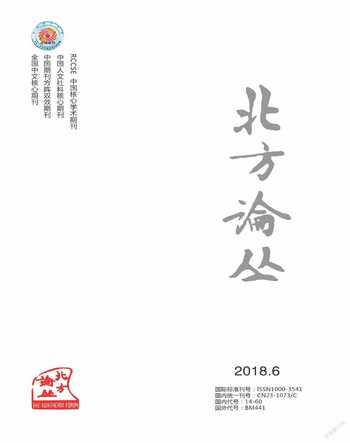軍隊與羅馬帝國邊疆經濟開發
王鶴
[摘要]羅馬軍隊是羅馬帝國邊疆行省經濟開發的重要力量。帝國時期,大量軍隊集中駐扎萊茵河、多瑙河、不列顛等邊疆地區,促進了當地農牧業和制造業的發展,有利于羅馬特有的農業經營方式——維拉體系的傳播。羅馬軍隊在西班牙、不列顛等行省的礦產資源開發中也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關鍵詞]羅馬軍隊;邊疆經濟;維拉
[中圖分類號]K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6-0120-04
羅馬帝國時期,萊茵河、多瑙河和不列顛邊境是三個重要的邊疆地區。2世紀早期,特別是哈德良羅馬帝國的歐洲邊界逐漸確立。漫長的邊境線的形成,以及石制要塞和堡壘的修建,表明羅馬帝國對外政策由進攻轉為防守。大量軍隊長期駐扎在羅馬邊境地區,對當地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伴隨著羅馬征服而帶來的稅收、租金的征收,以及大量軍隊駐扎在邊境地區所帶來的巨大需求,導致了邊疆經濟的深刻變化。
一、羅馬軍隊與邊疆農牧業和制造業的發展
萊茵河邊境包括北部高盧和上、下日耳曼行省,是羅馬帝國初期邊疆防守的重點。公元20年,萊茵河地區駐扎著8個軍團,加上輔軍總人數達到10萬。哈德良時期,沒有延續養父圖拉真對外征伐的策略,邊境地區以防御為主[1](p.175)。多瑙河地區駐扎著10個軍團。101年時,增至13個軍團。哈德良不列顛北部邊境是帝國西北部的重要邊睡,2世紀時,當地駐軍人數約有3萬人。大量軍隊在帝國邊境地區長期集中駐扎,給當地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同時也給當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市場和機遇。“對邊境地區的首要需求是發展農業生產力,供養當地的羅馬軍隊。”[2](p.46)每個羅馬士兵每日需要約850克的口糧,以及肉、奶酪、蔬菜、橄欖油、酸酒和鹽等食品。出于方便運輸和降低成本考慮,許多軍需物資來自于軍營和堡壘周邊地區。在不列顛行省,自公元43年以來,4個羅馬軍團駐扎在不列顛南部的切斯特、約克與北部的哈德良長城之間。相對于該島的人口和資源而言,不列顛占領軍的規模和人數相當龐大。據估計,不列顛軍隊每年需要約53萬蒲式耳的谷物,用作士兵口糧和牲畜飼料,這相當于大約6萬人生產出的剩余產品[2](p.53)。為此,羅馬帝國政府著手開發當地資源來滿足這一需求。公元60-140年,羅馬政府對不列顛東南部沼澤地進行了大規模開發。至哈德良時期,共計約50萬英畝的土地得到利用,以滿足羅馬駐軍對谷物的大量需求。羅馬軍隊的出現和帝國大型工程建設對當地農業生產產生了影響,不僅使大片土地得到開墾,還引進了新的作物品種,如面包小麥,甘藍、豆子、蘿卜、大頭菜、胡蘿卜、李子、蘋果、櫻桃和胡桃等等。諾森伯里亞和洛錫安東部地區的谷物生產和家畜飼養業顯著增長[3](p.726)。在哈德良長城以南約32千米處的昆布蘭平原,發現了眾多農場遺址,主要集中在羅馬不列顛駐軍基地,如卡萊爾和科布里奇周邊地區,當地駐軍無疑是最重要的消費群體。當地肥沃的土地、由羅馬駐軍提供的保護和軍事市場,以及靠近軍事公路的交通便利,促進了不列顛北部邊境農業的發展。在羅馬帝國初期,不列顛行省主要依賴進口產品供應當地駐軍。從1世紀早期起,不列顛開始出口谷物和牲畜,到4世紀中期,甚至可以向萊茵河邊境駐軍供應糧食了[4](pp.6-9)。
羅馬軍隊對動物產品,如皮革、牛肉、馱畜、戰馬等的需求促進了邊疆地區畜牧業和家畜飼養業的發展。西北部行省的羅馬駐軍以牛肉作為主要肉食來源,這一飲食習慣促使當地生產者擴大養牛規模[5](p.109)。2世紀末3世紀初,由于不列顛行省谷物產量的逐漸提高,再加上當地駐軍對肉食需求的增長,羅馬政府放棄了不列顛東南部的沼澤地開發工程,該地區由發展農業為主轉為發展綿羊和牛飼養業。在多瑙河等地區,大型牧場逐漸取代了之前居主導地位的小型家庭農場。在萊茵河邊境以北、以東的北歐平原地區,牛產量的增長也與當地軍隊的需求有直接關系。公元2-3世紀,日耳曼北部地區的鄉村殖民點菲德森·沃爾德(Feddersen Wierde)的畜欄數量從98個增長到443個,表明了當地家畜飼養業的發展。在荷蘭的德·霍登(De Hordern)的巴達維亞人定居點中,草地的增長和谷物產量下降表明,1-2世紀時,當地經濟模式從農業向家畜飼養業轉變[4](p.11)。
羅馬軍隊的到來還成為邊境地區手工業發展的催化劑。軍隊對某些產品,如紅紋陶、玻璃器皿、紡織品等需求刺激了當地制造業的發展。高盧等行省迅速增加生產,其產品逐漸在質量和數量上超過了意大利。2世紀時,原有的意大利制造業中心逐漸衰落。羅馬西部行省的手工業大多集中于邊疆地區,形成了以軍團或大型輔軍基地為中心的市場區。羅馬征服之前,不列顛威爾士地區基本處于“無陶時代”。1世紀中期,羅馬軍隊人侵不列顛后,當地駐軍所需的優質陶器最初主要從意大利本土或地中海地區進口。2世紀中期,不列顛行省用來盛裝無花果和橄欖的羅馬陶瓶數量逐漸減少甚至消失,這或許與這一時期羅馬駐軍人數減少有關。另一種解釋是,這表明不列顛行省逐漸實現了“經濟獨立”,當地生產的灰陶和其他類型的粗陶開始廣泛流行,取代了地中海進口產品[3](p.732)。
在某些羅馬西部行省,釀酒業的發展也與羅馬軍隊有關。葡萄和橄欖是地中海地區特有的兩種經濟作物,是希臘羅馬文明的重要象征。“橄欖油絕對是一種地中海產品……它在其生產區域以外,即在邊境軍隊,以及羅馬和羅馬化精英的食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3](p.657)。葡萄酒和橄欖油是羅馬士兵的標配食品,“葡萄種植業的重要性與將酒納入到邊境軍團士兵口糧中有關。橄欖油也是如此。這種需求的增長是對(非洲)馬格里布農業開發的重要原因之一”[3](p.659)。軍隊需求促進了邊疆駐地釀酒業和葡萄酒貿易的發展。里昂成為萊茵河地區酒類貿易中心。來自意大利、高盧南部和西班牙的葡萄酒在此沿羅納河而上,運往萊茵河和北海地區,主要供應當地駐軍。在羅訥河右岸,羅馬時期建立的老兵殖民地——貝特雷(Baeterrae)發展成為著名的大型葡萄酒市場,延續至今[5](p.253)。在西班牙行省,軍隊“通過鼓勵農業生產來為軍團提供食物,通過進口葡萄酒……刺激了西班牙經濟”[6](p.65)。羅馬士兵對當地生產的克爾特啤酒也十分喜愛,促進了這種啤酒從一種自行消費的家庭釀造飲料,逐漸向由專業啤酒作坊生產的用于銷售的商品轉變。
二、羅馬軍隊與邊疆維拉體系的傳播
伴隨著羅馬征服,以及邊疆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羅馬特有的農業管理方式——維拉(vil-la)體系開始向邊疆地區擴展。維拉最初是指羅馬上層階級擁有的鄉村地產,公元前2世紀,開始在意大利流行。一般說來,維拉往往與周圍的農場(fundus)緊密聯系在一起,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主人居住的帶臥室、餐廳和浴室的居住區,雇傭工人和奴隸生活的農場工人區,以及用來儲存和加工谷物、酒和油的生產區。某些大型維拉如同一個羅馬城鎮,設施齊全,有的還裝飾著精美的馬賽克、雕像和壁畫。意大利傳統維拉以奴隸勞動為主,由高級奴隸進行管理,同時還有許多受過專門訓練的奴隸擔任管家、會計、木匠等,或從事釀酒、制陶、建筑等勞動,整個維拉體系盡可能做到自給自足。維拉不僅具有經濟功能,同時還具有文化內涵和社會意義[7](p.231)。對于上層羅馬人來說,維拉既是主人的居所,也是農業生產單位,更是生活方式的展示和身份的象征。公元1世紀,維拉逐漸向西班牙、高盧、日耳曼、多瑙河等行省擴展,在安敦尼王朝時期達到頂點。不列顛作為最后并人羅馬帝國的行省之一,到2世紀時也出現了大量的維拉式莊園。在帝國邊境地區,維拉成為當地農業生產和管理的中心。為了適應邊境地區特殊的環境,邊疆地區維拉與意大利傳統維拉相比,在形態和功能上發生了較大改變。邊境維拉以農業生產功能為主,其設計和規劃注重安全性和工作效率,而不是為了舒適或炫耀。馬賽克、壁畫等裝飾較為少見,浴室的設計和規模也以實用為主。邊疆地區維拉所采用的勞動力類型也有別于意大利傳統維拉,更多地使用自由勞動者進行生產。邊疆維拉中有很多分成制的佃農,他們租用維拉中的生產設備和役畜,將一部分谷物交給維拉主人,剩余產品歸自己所有。維拉的生產活動使羅馬邊疆土地得到迅速開墾。“早期帝國的維拉在從生存農業向面向市場的鄉村經濟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8](p.116)
傳統觀點認為,行省維拉的興起與向羅馬軍團退役老兵分配土地有關,認為這些維拉主人是退役的羅馬士兵。其依據是,有的維拉所使用的房瓦是由軍隊生產,并帶有軍團的印記,如萊茵河上游的蘭芬伯格(Lanfenburg)的維拉所使用的房瓦,是由駐扎在溫多尼撒(Vindonissa)的第21和第11軍團所生產。但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多數維拉主人是當地居民,擁有土地和財富,參與當地城鎮政府的管理,這些維拉是他們在鄉村的居所。當地居民采用了羅馬化的生活方式,接受了羅馬的經濟管理制度[9](p.71)。盡管如此,維拉在行省與邊疆地區的傳播與推廣仍與軍隊密切相關。首先,維拉興起的前提是和平穩定的環境,以及對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剩余產品的大量需求。“軍隊使‘羅馬和平和隨之而來的經濟繁榮成為可能。這是羅馬人帶給古代世界最好的禮物”[10](p.550)。而維拉是“安定的環境,經濟穩定的產物,也是羅馬文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的表征”[11](p.34)。羅馬軍隊維護的“羅馬和平”,以及當地駐軍所帶來的持續而龐大的供應需求,促進了維拉在羅馬邊境地區的繁榮和擴展。維拉主人充分利用邊境周邊地區大量尚未開發的土地,以及羅馬駐軍提供的軍事市場等有利條件,廣建維拉,使之成為羅馬人開發邊境地區土地的一種流行方式。當地人口中的上層競相校仿,進一步促進了維拉制度在邊境地區的推廣和傳播。其次,羅馬軍隊在邊疆地區的長期駐扎,吸引了大量的移民人口。“大規模的意大利移民和殖民計劃,慷慨的土地分配,使得新來者成為當地人口的主人,從而加速了羅馬化的進程,以及維拉體系的成長”[11](p.60)。羅馬帝國初期,萊菌河一多瑙河邊境建立起來,大量的軍事和平民人口被吸引到軍事要塞周邊地區,如阿昆庫姆、布里蓋提奧、卡努圖姆、文多波納等地。一些羅馬移民和羅馬軍隊退役老兵及其后代獲得了羅馬國家授予的土地,或個人出資購買當地的土地,成為農莊的主人[12](pp.326-330)。維拉體系的傳播和推廣是行省和邊境地區農業羅馬化的標志之一。邊境地區維拉的大規模興建表明,行省當地上層積累了大量財富,投資于維拉之上,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生活水平。維拉制度的優勢在于其生產能力巨大,具有很高的靈活性和較強的適應性。維拉管理體系的運用充分開發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潛能,促進了邊境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還傳播了羅馬人的農業、加工業和生產管理等方面的技術和知識。“維拉主人使他們的土地成為邊境地區農業的學校。無論如何,維拉在邊境農業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p.48)。
三、羅馬軍隊與礦產資源開發
羅馬帝國時期,“貨幣經濟最后終于通行于全帝國,甚至在那些以前從未用過貨幣的地區也以貨幣作為交換手段,因而增加了對珍貴金屬的需求,尤其是白銀。于是羅馬政府努力接二連三地把礦區并人帝國之內,并以較前更為有效的方式予以組織”[12](p.486)。帝國初年,大多數行省的礦山和采石場成為帝國的財產。這些礦山提供了為軍隊制造武器的鐵,以及用于鑄造貨幣的金、銀和銅等金屬。
行省采礦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羅馬軍隊密切相關。邊疆駐軍在礦產資源的勘探、開采、監督和保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資源開發過程中,羅馬軍隊主要負責監督奴隸和被判強制勞動的罪犯采礦,或者提供高標準的工程技術支持,如大型引水橋的測量和修建,偶爾也直接參與礦山開采,如塔西佗曾提到,克勞狄時期,羅馬軍隊在日耳曼行省的瑪提烏姆開發銀礦[13](p.335)。帝國早期,因奧古斯都的貨幣改革,西班牙成為羅馬帝國最重要的采礦區域。“在元首制的大部分時間里,西班牙行省提供了帝國所需的幾乎所有貴金屬及其他金屬。至公元1世紀末,黃金的年產量達20000英鎊,白銀產量為8噸”[14](p.192)。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人“世界文化遺產”的西班牙拉斯梅德拉斯(Las Medu-las)遺址,留下了羅馬人公元1-2世紀時大型采礦活動的遺跡。該遺址是羅馬帝國時期最大的露天金礦,年黃金產量約為24千克。羅馬人采用了水準儀、折光儀等簡陋的儀器,挖掘豎井和隧道,利用水力采礦技術,從礦石沉淀物中提取黃金。其中一條隧道連續保持0.21%的微小傾斜度,綿延長達143千米。從開采技術的精湛程度來看,不可能沒有軍隊的參與。
在不列顛行省的威爾士地區,石材的開采和鉛工業的起源與當地駐軍密切相關。在位于卡利恩的軍團遺址中,砂巖、板巖、大理石、巴斯石等石材被廣泛應用于堡壘的修建,以及士兵墓碑、石棺等的制作中。鉛是羅馬軍隊廣泛使用的一種重要金屬,主要用于制造輸水管道,或制作日常物品如砝碼等。公元49年,羅馬軍隊在不列顛行省沿海平原開采鉛和銀,在當地發現了帶有軍團印記的鉛制品[15](p.62)。在威爾士,幾乎所有的軍事遺址都發現了使用鉛的證據,在卡利恩要塞的作坊中發現了大量鉛礦生產的廢棄物。羅馬軍隊還最早對南部威爾士地區的煤炭資源進行了開發,在卡利恩遺址中發現了用來冶煉鉛和鐵的煤炭的遺跡[16](pp.185-188)。在羅馬軍隊的監督和控制之下,利用其所帶來的先進的開采技術和儀器設備,羅馬帝國政府對西班牙、不列顛等行省的礦產資源進行了系統、有效的開發和利用,對于羅馬國家貨幣的鑄造,羅馬帝國貨幣經濟的運行,以及羅馬軍隊軍餉的支付和行省賦稅的征收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間接促進了邊疆行省建筑業、手工業等行業的發展。
羅馬軍隊在帝國邊疆地區的長期駐扎,給邊疆經濟帶來深刻變化,如農牧業和制造業的發展,維拉體系的傳播,礦產資源的開發等等。這一系列變化“使當地公社與羅馬的經濟和政治關系日益密切”[17](p.129),加速了邊疆地區與帝國中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有利于帝國經濟的穩定和繁榮。
[參考文獻]
[1]張曉校.羅馬近衛軍史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2]Steven K.Drummond,Lynn H.Nelson,The Western Frontiers ofImperial Rome[M].New York,London,1994.
[3]Walter Scheidel,Ian Morris,Richard Saller(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4]Sue Stallibrass and Richard Thomas(eds.),Feeding the RomanArm3:The Archaeology of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 NW Europe[M].Oxbow Books,2008.
[5]Malcolm Todd(ed.),A Companion of Roman Britain[M].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6][法]維克多·沙波.羅馬世界[M].王悅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7]劉津瑜.羅馬史研究入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8]Leonard A.Curchin,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 Com-plexity,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 Provincial Hinterland[M].New York,2004.
[9]Maureen Carroll,Romans,Celts and Germans:The German Prov-ince of Rome[M].Tempus Publishing Ltd,2001.
[10]G.A.Harrer,Rome and Her Subject Peoples[J].The Classi-cal Journal,Vol.14,No.9(Jun.,1919).
[11]Graham Webster(ed.),The Roman Villa: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12][美]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M].馬雍,厲以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13][古羅馬]塔西佗.編年史[M].王以鑄,崔妙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4][英]約翰·瓦歇爾.羅馬帝國[M].袁波,薄海昆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15]R.F.J.Jones,The Roman Military Occupation of North-WestSpain[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6),1976.
[16]Paul Erdcamp(ed.),The Roman Army and Economy[M].G.C.Giben,Publisher,Amsterdam,2002.
[17]Simon Keay and Nicola Terrenato(eds.),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M].Oxbow Book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