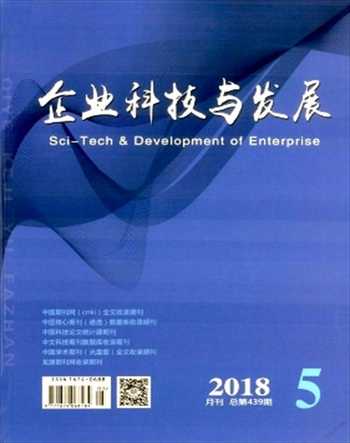湖北省出口企業生產率研究
周麗
【摘 要】目前,關于生產率悖論的研究中以省為研究對象的比較少。文章選取湖北省1998—2007年共60 659個樣本為研究對象,運用LP方法測算出全要素生產率,驗證出口與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湖北省出口企業不存在生產率悖論,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明顯較高;非國有企業的生產率高于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外資企業的生產率高于非外資企業的生產率。
【關鍵詞】生產率悖論;出口企業;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F279.2;F752.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0688(2018)05-0037-03
0 引言
Melitz模型在壟斷競爭市場中引入生產率差異,并得出結論:出口企業的生產率高于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得到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驗證(Helpman et al,2004;Aw et al,2007;Tomiura,2007;Becker & Egger,2009)。但是李春頂(2010)、湯二子等人(2011)、曹馳(2015)運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數據進行測算卻得出了相悖的結論,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即中國存在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悖論”。學者們試圖解釋“生產率悖論”的存在機理。湯二子等人(2012)驗證了30個行業的生產率,得出生產率悖論確實存在且越來越普遍,在加工貿易行業尤其明顯。盡管這些研究對出口企業“生產率悖論”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但不同學者所用的計量方法不同,得出的實證結果也不同。目前,以省為范圍進行研究的文獻較少。由于地理原因及歷史原因,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之間差異較大,限定研究范圍更有利于確定生產率悖論是否存在。湖北省逐年增長的出口額背后是出口企業的不斷發展。湖北省的出口企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筆者選擇湖北省規模以上企業作為研究范圍進行研究,探索湖北省出口企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
1 生產率測算方法的選擇
生產率是指全要素生產率,反映了總產出中不能由投入要素所解釋的剩余部分。企業的異質性體現在同樣的資本和勞動的投入,但由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管理水平、制度環境及對制度環境的把握能力不同,則產出不同。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很多,主要分為參數方法和半參數方法。這些方法有的適用于宏觀總量分析,有些適用于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分析。在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初期,由于數據限制,通常運用總量數據分析國別或者省際生產率差異,而忽略了企業個體的決策反應所造成的模型內生性問題。但是隨著工業企業數據庫出現后,研究的重點逐漸轉移到運用更為精細的企業層面的數據。在測算方法的選擇上特別注意模型內生性的問題,以避免得出錯誤的結論。
最早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是從估計生產函數開始的,使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C-D生產函數)。該方法適合宏觀研究,不適合企業層面的研究,因為它不能解決模型內生性的問題。Marschak and Andrews(1944)提出由于生產決策的同時性,企業會根據最大化生產的原則實時地調整投入,相對于固定資產的投入而言,勞動投入的調整更為方便,因此這種測算方式會高估勞動力的彈性系數α,低估資本投入的彈性β。殘差項與回歸項相關,OLS估計的結果會產生偏誤。比較常用的TFP=Ln(Q÷L)-s Ln(K÷L)是C-D方法的衍生方法,許多學者在根據這種方法測算TFP時直接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有些甚至是國外學者的研究。不同樣本估計出的s是不同的,這種直接引用其他學者測算的s進行TFP測算會導致測算出的TFP值不準確。
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了基于一致半參數估計值方法(簡稱OP方法)。OP方法假設企業根據當前生產率狀況做出投資決策,選用企業的當期投資作為不可觀測的生產率沖擊的代理變量,但企業投資受包括歷史投資在內的許多因素的影響,不完全是生產率沖擊引起的,并且企業不一定會每年追加投資,OP方法會損失當期投資為零的企業樣本。
針對OP方法損失數據的問題,Levinsohn-Petrin(2003)提出了LP方法,也是一種半參估計方法。在滿足條件的情況下,LP方法能提供對企業層面生產函數的一致估計。針對投資額為零的問題,該方法將當期投資這個代理變量改為中間品投入這個指標,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正好有這個指標的統計。因此,本文選擇LP方法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計。
2 生產率的測算
2.1 數據來源與描述
本文數據來自于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湖北省企業的數據。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數據已更新到2013年,但工業增加值2008—2013年的數據缺失,無法用LP方法計算全要素生產率。本文基于如下原則進行了樣本的整理:①為了使實證結論可靠,我們只選用仍在正常經營的企業,對于停業、籌建、撤銷及其他經營狀態的企業予以刪除。由于數據限制,2001年、2002年、2005年這3年的經營狀態數據缺失,所以選用湖北省企業數據。②因為2004年的出口額指標數據缺失,所以我們假定企業出口具有連續性,2003年、2005年出口的企業在2004年也出口,對缺失數據進行了填補。③我們運用會計恒等式對所有缺失值盡可能地予以恢復和保留樣本,刪除了指標嚴重不全的樣本。最終我們得到了60 659個觀察值,其中出口企業觀察值為6 610個,占總觀察值的10.9%。從地區分布來看,荊州和武漢兩個城市的總樣本量和出口樣本量均占絕對優勢。荊州和武漢兩個城市的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數量較其他城市有明顯優勢。從地級市層面看,荊州和武漢的國有企業占比并不高,但外企占比較高。從各年的數據來看,湖北省工業企業數量逐年遞增,國企所占比例逐年迅速減少,從1998年的79.68%降到2007年的9.69%,這與我國加強民營企業經濟的相關政策緊密相關。外資企業數量也逐年增長,外企占比有所增長。從出口企業樣本來看,湖北省出口企業逐年遞增,國有企業所占比例逐年迅速減少,從1998年的56.92%降到2007年的8.01%,這與總樣本變化一致。外資企業數量也逐年增長,占比有所增長。比較總樣本和出口樣本發現,出口企業樣本中的國有企業的比例低于總樣本,但外資企業比例明顯較總樣本高。
2.2 主要統計指標
本文選擇5個指標運用LP方法對60 659個觀察值進行測算。LnY_add是總產出,由工業增加值的對數表示。ln_material是中間品投入,由中間投入品的自然對數表示;LnK是資本,由固定資產合計的自然對數表示;LnL是勞動投入用從業人數表示,由于“從業人數”指標數據缺失嚴重,所以根據“本年應付工資總額(貸方累計發生額)”指標的數據及湖北省平均工資的數據計算得出各企業的“標準人數”作為替代。一般企業在應對調查時可能少報企業職工人數,筆者認為運用“本年應付工資總額(貸方累計發生額)”指標的數據及湖北省平均工資的數據計算得出各企業的“標準人數”更符合實際。Lnage表示企業年齡,由統計年度減開業年度指標后取對數獲得。
2.3 LP方法測算結果
我們運用LP方法進行測算,結果見表1。
我們選擇LP方法計算了樣本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通過計算得出勞動的彈性α=13.415 59%,資本的彈性為β=19.585 49%。
3 生產率悖論檢驗
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是否比非出口企業高呢?本文使用SAS軟件對湖北省出口和內銷企業的60 659個樣本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為了驗證結果的可靠性,選擇Levene's檢驗方差齊性。分析結果得出模型高度顯著,說明企業是否出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顯著。但是,模型顯著是以方差齊性為前提的,如果方差不齊,則得出均值有差異的結果是不可靠的。通過擬合發現,該樣本并不服從正態分布,因此選擇Levene's檢驗檢測方差齊性。方差齊性的假定檢驗結果表明,使用Levene's檢驗P值為0.212 5,所以在不同水平下觀測結果的方差無顯著差異,此時的均值差異才有意義。結果顯示,在方差齊性的前提下,出口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均值為6.66,顯著大于內銷企業的均值6.11。分樣本進行驗證發現,非國有企業的生產率高于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外資企業的生產率高于非外資企業的生產率。分年份驗證發現,企業生產率隨年份波動,說明宏觀經濟對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定的影響,驗證過程在這里不再贅述。此外,本文還驗證了行業因素對生產率的影響,結果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各行業的均值和方差及其兩倍方差線可以清晰地看出,有的行業具有均值較高且方差波動幅度小的特征,而有的行業正好相反,不僅均值小,方差波動也大。雖然本文方差齊性檢驗未通過,不能排除樣本選擇帶來的偏誤,但因為本次選擇的樣本量較大,因此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研究發現生產率最高的兩大行業為A7(石油和天然氣行業)、A16(煙草行業),生產率最低的兩大行業為A11(其他采礦業)、A12(木材采運業),方差波動也大。
4 結語
本次選取湖北省1998—2007年的數據,共60 659個樣本觀察值,研究湖北出口企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得出結論如下:湖北省出口企業不存在生產率悖論,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明顯高于非出口企業,并且非國有企業的生產率高于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外資企業的生產率高于非外資企業的生產率。分年回歸發現,企業生產率隨年份波動,說明宏觀經濟對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定的影響。分行業研究湖北省企業生產率發現,有些行業生產率均偏高且方差波動偏小,有些行業的企業則生產率偏低且方差波動偏大。發展生產率高且方差波動小的行業更有利于湖北省經濟平穩發展。
參 考 文 獻
[1]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ndustry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11:1695-1725.
[2]Fare R,Grosskop S,NorrisM,et al.Productivitygrowth,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s in industrialized courttries[J].American EconomicReview,1994(84).
[3]Marschak J,W Andrews.Random SimulataneousEqu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J].Econ-ometric,1944,12(3):143-205.
[4]蔡昉.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J].中國社會科學,2013(1):56-71,206.
[5]魯曉東,連玉君.中國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估計:1999—2007[J].經濟學(季刊),2012(1):541-557.
[6]張家勝.湖北省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5,21:112-114.
[7]黃勇.湖北省農業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與效率變化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3(8):99-102.
[8]程惠芳,陸嘉俊.知識資本對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14(5):74-187.
[9]范劍勇,馮猛,李方文.產業集聚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J].世界經濟,2014(5):51-73.
[10]楊汝岱.中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J].經濟研究,2015(2):61-74.
[11]龔關,胡關亮.中國制造業資源配置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J].經濟研究,2013(4):4-15,29.
[12]王杰,劉斌.環境規制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的經驗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4(3):44-56.
[13]朱學紅,曾旖,豐超.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產業異質性、區域差異及空間布局優化[J].商業研究,2016(5):1-8.
[14]劉仁伍.浙江省銀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與美、德、韓的比較[J].浙江金融,2012(1):4-8.
[責任編輯:鄧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