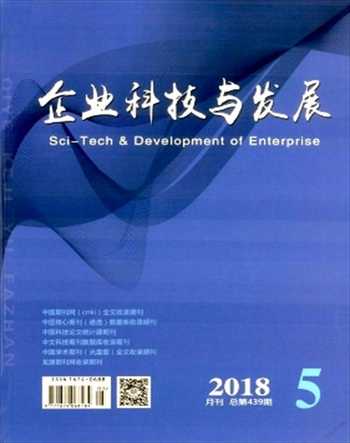論游戲操作畫面的作品屬性及其類型
吳雷
【摘 要】判定游戲操作畫面的作品屬性時,應將其特性和作品的定義進行結合,分析其是否具有獨創性和可復制性。在判定游戲操作畫面是否構成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時,不應對攝制的技術方式進行限制,而應考察其本質特征。若其符合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本質特征,能夠形成連續的活動畫面,則可將其視為電影或類電影作品進行保護。
【關鍵詞】電子游戲;游戲畫面;電影作品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688(2018)05-0127-02
1 問題的提出
近幾年,我國電子游戲產業迅猛發展。與此同時,由電子游戲所引發的產權糾紛也隨之大量出現。游戲屬于科技發展的產物,其組成往往較為復雜且通常具有雙向互動性,這亦導致在對游戲操作畫面的屬性進行認定時,存有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2個方面:{1}游戲操作畫面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2}如果游戲操作畫面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又屬于哪一種作品類型?比如,在“耀宇案”中,法院認為游戲比賽畫面并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①;而在“網易案”中,法院則認為游戲操作畫面屬于作品,且屬于電影或類電影作品②。鑒于此,上述問題確有研究之必要。
2 游戲操作畫面的作品屬性
依據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對“作品”所下的定義③,判斷游戲操作畫面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時,具體需要從以下2個方面進行考量。
(1)游戲操作畫面的獨創性。獨創性是作品區別于其他人類勞動成果的核心要素,只有具有獨創性的外在表達才是作品[1]。從兩大法系的融合趨勢來看,獨創性的認定主要包括2個方面:一方面是作品為作者獨創構思而成,另一方面是作品需體現作者一定的創作高度。人們認為,獨創性與藝術或美學價值、作品的形式、主題是否新穎并無關聯,僅與作品的內容是否首創有關[2]。因此,判斷游戲操作畫面是否具有獨創性,需對畫面內容進行考察。
通常而言,游戲玩家在操作過程中,所顯示的游戲畫面并非預先設定的文字、圖片、視頻等元素的簡單重現,而是處于不斷變化的動態畫面。以往游戲設定簡單,玩家只能在既有的設定內進行操作,且無論其操作如何多樣,整個游戲畫面局限于游戲創作者事先預設范圍內。對于此類游戲,如美國法院所言,玩家不能自由控制屏幕上呈現的畫面順序,亦不能創造出他自己想要的畫面順序,玩家只能在游戲設定的有限順序中選擇其一[3]。因此,對于此類游戲操作畫面,應當按照游戲固有畫面判斷其是否具有獨創性。而游戲固有畫面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學術及實務界并無太大爭議。
隨著游戲產業的發展,現今的游戲互動性和自由性增強,玩家能夠自由創造一些人物形象或游戲場景,這亦導致不同游戲玩家顯示的臨時游戲畫面會有所不同。在“耀宇案”中,法院就以此為由否認游戲畫面的作品屬性。可事實上,雖然不同操作會導致游戲臨時界面存在差別,但游戲通常具有統一的故事線索和主線人物,實質部分的情節、角色、畫面和音樂等都會反復出現,玩家在操作過程中并不會對游戲整體畫面的內容要素起到任何實質性附加效果,因此并不會對游戲畫面的獨創性認定產生影響[4]。在美國,這被稱為“重復畫面”標準,游戲聲音和畫面實質性部分的重復出現符合視聽作品的保護要求,游戲玩家的操作并不會使游戲畫面不符合版權的保護條件[5]。綜上所述,從游戲操作畫面的內容來看,無論是哪種游戲類型,游戲操作畫面均具有獨創性。
(2)游戲操作畫面的可復制性。可復制性是指著作權法上所稱的作品,可以被人們直接或者借助某種機械或設備感知,并能夠以某種有形物質載體進行復制。在“耀宇案”的判決中,法院認為,玩家操作所形成的動態畫面,系進行中的比賽情況的一種客觀的表現形式,比賽過程具有隨機性和不可復制性,比賽結果具有不確定性,故比賽畫面并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該判決錯誤地將“可復制性”等同于“確定性”,即只有過程與結果均確定的作品,才具有可復制性,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實際上,可復制性的核心在于“能夠被感知”和“能以物質載體復制”,后者實為前者服務。因此有學者認為將“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解釋為“能夠被客觀感知的外在表達”較為合理[2]。現有技術條件下,對游戲操作畫面進行錄制和復制并非難事,很多游戲中自帶錄制功能,即能允許游戲玩家自由錄制進行傳播。美國司法實踐中,亦承認游戲畫面的可復制性[6]。因此,雖然玩家的操作不同,游戲過程和結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整個游戲畫面通過屏幕皆能被外界所感知,并且能夠以技術手段進行復制和傳播。綜上所述,游戲操作畫面具有可復制性。
3 游戲操作畫面的具體作品類型
從世界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游戲畫面通常被視為視聽作品予以保護。但我國《著作權法》并未采用“視聽作品”的概念,而是參照《伯爾尼公約》的規定,采用“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結合《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第十一項關于“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所下定義來看④,判斷游戲操作畫面是否屬于電影作品或類電影作品,需從以下2個方面進行考量。
(1)游戲操作畫面作品類型不受攝制技術方式的限制。隨著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電影的拍攝不再局限于專業拍攝裝置的攝制行為,而是使用電腦進行合成制作。這些利用新型技術制作的影視作品與傳統的電影作品欣賞效果一致,并無太大區別。若在判定是否屬于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時,將其限定于特定技術手段上,將會導致大量利用新型科技合成制作而不是以傳統方式攝制的作品無法被歸入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范疇,客觀上縮小了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范圍。因此,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編寫的《伯爾尼公約指南》指出,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定義無需考慮制作它的“工藝方法”[7]。可幸的是,我國司法實踐已注意到上述變化。在“壯游案”中,法院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著作權客體也會發生變化,對此應當依據實質因素對作品進行分類。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應是對創作方法的規定,而不只是制作技術的規定⑤。因此,基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判斷游戲操作畫面是否構成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時,不應對攝制的技術方式進行限制,而應考察其本質特征。
(2)游戲操作畫面可作為電影或類電影作品進行保護。著作權法主張“思想表達兩分法”的原理,其基本含義是著作權法不保護思想本身,只保護思想的表達。因此,作品的本質在于表現形式而非思想,判斷作品的本質特征應從表現形式入手[8]。在“壯游案”案中,上訴人認為,從表現形式上來看,網絡游戲不存在如類電影般的故事情節、豐富場景,而且畫面不固定,是玩家按照游戲規則通過操作形成的動態畫面,過程具有隨機性和不可復制性,故網絡游戲畫面不屬于類電影作品。對于此類主張,將畫面的固定性作為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表現形式,以游戲操作畫面的隨機性和不可復制性來否定其類電影作品屬性,實質上并未對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表現形式形成正確的認識。從我國《著作權法》對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定義來看,此類作品的表現形式在于連續活動畫面組成,這亦是與靜態畫面作品存在差異的特征所在。故畫面的固定性并非“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本質特征,判斷游戲操作畫面是否屬于電影或類電影作品,關鍵在于其是否形成連續的活動畫面。但如前文所述,雖然玩家的不同操作會導致游戲臨時界面存在差別,但這些界面的總體畫面、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音樂等內容都是相同的,且這些不同的連續活動畫面,并未脫離原有的游戲設置。故游戲操作畫面是唯一固定還是隨著玩家的不同操作而變化,并不能成為認定其與電影或類電影作品的區別因素,滿足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本質特征的游戲操作畫面,可以作為電影或類電影作品進行保護。
4 結論
判定游戲操作畫面作品屬性時,需從以下2個方面進行考量:獨創性和可復制性。從獨創性來看,無論是哪種游戲類型,其操作畫面皆具有獨創性;從可復制性來看,雖然因為玩家的操作不同,游戲過程和結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整個游戲畫面通過屏幕皆能被外界所感知,并且能夠以技術手段進行復制。判定游戲操作畫面是否屬于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時,主要考察其是否符合“連續活動畫面”的本質特征,而不應對攝制的技術方式進行限制。在現有法律對游戲操作畫面作品類別未作明確規定的前提下,若其符合電影或類電影作品本質特征,則可將其視為電影或類電影作品進行保護。
注 釋
①詳見(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91號民事判決書。
②詳見(2015)粵知法著民初字第16號民事判決書。
③《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
④《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著作權法和本條例中下列作品的含義,(十一)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
⑤詳見(2016)滬73民終190號民事判決書。
參 考 文 獻
[1]吳漢東.知識產權法新論[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82.
[2]梁志文.數字著作權論——以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為中心[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131.
[3]崔國斌.認真對待游戲著作權[J].知識產權,2016(2):3-18.
[4]王遷,袁鋒.論網絡游戲整體畫面的作品定性[J].中國版權,2016(4):19-24.
[5]凌宗亮.網絡游戲的作品屬性及其權利歸屬[J].中國版權,2016(5):23-26.
[6]馮曉青.網絡游戲直播畫面的作品屬性及其相關著作權問題研究[J].知識產權,2017(1):3-13.
[7]劉波林.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指南(1971年巴黎文本)[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5.
[8]盧海君.“電影作品”定義之反思與重構[J].知識產權,2011(6):18-25.
[責任編輯:陳澤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