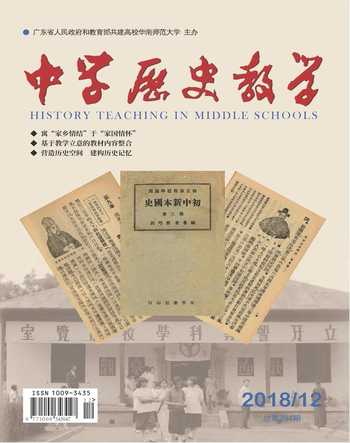營造歷史空間 建構歷史記憶
盧曉華
空間是構成整個歷史敘事必不可少的基礎。要使歷史更貼近事件的原始存在狀態,便應該在空間維度上進行編排和創造,賦予歷史事件一種空間性的結構。[1]相對于歷史時序,教師較缺乏營造歷史空間引領學生體悟歷史的策略,故對于學生而言,存在于教科書中的像“奧斯威辛集中營”那樣的封閉歷史空間,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一堆無法想象的數據,以及上百萬個沒有名字的死難者。這不利于建構符合倫理、真實而深入人心的歷史記憶。那么如何復原歷史空間,讓學生的歷史記憶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筆者以“奧斯威辛集中營”一課教學為例加以說明。
一、營造歷史空間,解讀“集中營”的概念
奧斯維辛是納粹集中營的縮影,那么什么是“集中營”呢?教科書的表述是:集中營是法西斯實行暴力統治的重要工具。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執政后就開始建造集中營,用來監禁反對納粹政權的人。二戰爆發后,德國在占領區大量建立集中營,用來關押和虐殺戰俘、猶太人和抵抗分子。[2]這個定義的缺陷在于容易給學生造成印象:集中營只和納粹相聯系。事實上,它包含更大的歷史空間:前蘇聯有“古拉格”、國民黨有“渣滓洞”、美國有“日裔集中營”、智利有“尊嚴殖民地”、還有柬埔寨、烏干達、波斯尼亞等地上演過的人道主義災難。因此,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先不呈現蒼白的,限制學生空間想象力的文字定義,而通過地圖、照片給學生認識的鋪墊,由形象思維逐步向抽象思維過渡。
師:呈現德國納粹集中營分布圖1和奧斯威辛集中營及周邊環境圖2(略)。圖1反映出什么歷史信息?奧斯威辛集中營位于哪個國家?根據圖2并結合教材指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主要組成部分及其功能并分析納粹選址的原因。
從圖1可知,奧斯威辛集中營并非納粹最早建立的集中營,也不是唯一的一座集中營。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集中營像癌癥擴散到歐洲大陸,侵蝕著歐洲文明的肌體。從圖2比對教材可知,為了更隱蔽、高效率地殺人,納粹選擇既交通便利又不引人關注的小鎮附近開闊地帶建立集監禁、勞役和滅絕三種功能為一體的、規模巨大的人間地獄。有了地圖的空間界定,學生就有了方向感,這時可呈現集中營內部照片細觀。教科書已配有“一位幸存者參觀遺址”、“集中營的圍墻與電網”、“巨大的分式焚尸爐”三幅照片,可再挑選幾幅能集中反映集中營的殘酷和荒謬的照片。比如集中營納粹頭子赫斯把原本在達豪集中營使用的標語“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刻在了奧斯維辛入口處的大鐵門上方,多么具有反諷和欺騙的意味,在集中營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由;還有集中營生存狀況照片,在狹小空間中人像螻蟻般蜷縮在一起,活得毫無尊嚴。與地圖相比,歷史照片更能讓學生的思緒定格在一個瞬間,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構建一幅幅歷史畫面。為了讓這幅歷史畫面有聲,教師還可以引入歷史當事人的回憶,營造一個有回聲的歷史空間。教科書只回放了一段施害者的聲音,即納粹集中營頭子黨衛軍突擊隊隊長魯道夫·赫斯回憶說:“我戴著防毒面具,親自觀看殺人過程。在擁擠的囚禁室內,只要把‘旋風B'(固體毒劑)扔進去,死亡就降臨了。只聽到一陣短暫的、透不過氣來的叫喊聲,然后一切就結束了。”[3]我們從中看到了納粹的冷血猙獰,但這是不夠的,怎么能讓廣大集中營受害者失聲?教師有必要為學生補充受害者的聲音:
材料1:一個新來者很少被接納,我并不是說作為朋友,而僅僅是作為普通難友;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老資格(三四個月就算是老資格了)表現出激怒,甚至敵意。人們嫉妒“新來的”,因為他似乎仍舊帶著一點家的味道。……在第一天,新人被人們取笑,成為各種殘忍惡作劇的對象,無疑,在集中營里存在著退化,引導人們歸于原始行為。
——(意)普里莫·萊維:《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材料2:凱爾泰斯說,他不是不會寫“一位紅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著口紅和手槍”那類的流行小說,但他不寫,只寫奧斯維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記中寫道:“我聽到有人說我寫這個話題已不合時宜……然而近來,我再次震驚地意識到,其實任何東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興趣,唯有‘奧斯維辛神話。”
——余澤民:《凱爾泰斯為什么只寫奧斯維辛?》
普里莫·萊維是意大利作家,亦是化學家和奧斯威辛174517號囚犯。他的回憶能讓學生知道集中營里的另外一面,本該相濡以沫的難友們卻相互敵視,正是集中營讓人變成了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寫作偏執,無疑是源于他14歲經歷的集中營苦難,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止于電網內的苦難,他不僅講述他所經歷的奧斯維辛,而且預言人類將要經歷的奧斯維辛。1945年,集中營被摧毀,但柏林墻拔地而起,冷戰時期的東歐人被統統關進一座謊言集中營。從這個角度講,凱爾泰斯的奧斯維辛文學超越了其他奧斯維辛題材的作品,其價值在于,他從更高的角度看奧斯維辛,不僅控訴,而且剖析,警示未來。營造有圖、有實物、有人的歷史空間為深入解釋歷史現象準備了前提條件。學生只有在心靈受到震撼,認知出現沖突、知識感覺不足時才能充滿學習的欲望,有效地參與到課堂中,參與更高層次的“頭腦風暴”。
二、置身歷史空間,反思“奧斯維辛”的現象
德國哲學家特奧多·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他是說,浸淫在“私密、自負的凝思之中”的詩人找不到文字來表現奧斯維辛機械式、無靈魂和工業性的殘忍。另外,詩歌是一種創造美和愉悅的過程,用來描述大屠殺不合適。[4]詩人或許找不到語言來表現“奧斯維辛”,但歷史教學需要學生用正確的觀點解釋大屠殺現象。為此,筆者組織學生討論,形成以下二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觀點一:都是希特勒的錯;觀點二:德國人是邪惡的民族。針對這些觀點,筆者呈現以下材料:
材料3:反猶太主義偏見不是對大屠殺發生的充分解釋。只有當對猶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見,成為變態的時候;只有當它將對個別猶太人的仇恨和對整體猶太人強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結合起來的時候,我們才可能開始對大屠殺建立因果的關系。對猶太恐懼癥在德國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進行提問,也是重要的。……在1933年之前,歷史的記錄并不支持滅絕猶太人的意圖。……正是戰爭和可怕的戰敗結果,打開了政治極端主義的泄洪閘門,給頑固的納粹精神提供了養分,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態的反猶太主義。……在1933年到1939年間,這種滅絕猶太人的猶太恐懼癥成了國家發起的東西,它在這六年內的目標就是剝奪德國猶太人在德國的公民權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另外幾百萬猶太人歸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從而進入到實際的種族滅絕階段。
——(美)克勞斯·費舍爾:《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
材料4:世上沒有危險民族,有的是危險的情境,這既不是自然法則或歷史規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結果。當然,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歷史因素的影響,但后者并不起決定性作用。
——(荷)伊恩·布魯瑪:《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
材料5:大屠殺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嗎?它是不是德國歷史本身的自然進化,因而可以歸之于德國人的某種特殊品質?它是歐洲社會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部分嗎?它是啟蒙的失敗,甚至是文明和人類的失敗嗎?如同這些對大屠殺的偉大故事的調查——無論關注的焦點是意圖還是德國性、歐洲性乃至人類性——所表明的,公認的事實并不足以保證唯一的最佳解釋。然而,承認解釋的多樣性,并不是認可對于公認的野蠻事實的所謂修正主義否定,而是表明,這些事實可以得到承認。“大屠殺”這個術語本已經是一種復雜的解釋,它在表明偉大的故事的同時,也表明一種道德判斷。
——(美)伯克霍福:《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
設問:為什么“不能用罪惡的領導層所犯下的罪行來指控整個民族?”是什么樣的歷史情境導致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發生?對希特勒的歸罪有何意義與局限性?為什么要“承認歷史解釋的多樣性”?
對于思維盲點,學術觀點的引介有助于學生拓展思路,多角度地解釋復雜的歷史現象。對希特勒的歸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義,因為只要發生了人道災難,以“不知情”“不直接過問”“下面的人辦壞了事”這類借口來為最高領導人開脫責任,都是不能接受的。[5]當然,大屠殺主要還是源于制度之惡。極權統治誘發、利用和加強人性中的陰暗和殘酷,而人性中的陰暗和殘酷又在這樣一種統治秩序中極度放大了極權的制度之惡。[6]奧斯維辛和納粹的“最終解決”代表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卑劣的行為。納粹犯下的罪行讓世人認識到,只要足夠冷血,一群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先進技術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齷齪之事。丑惡的事實就擺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發現它的價值。
三、走出歷史空間,警惕歷史悲劇的重演
奧斯維辛的幸存者普里莫·萊維指出:“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開始否認人類的基本自由和人們之間的平等,你就開始向集中營體系邁進。而這是一條難以止步的道路。”[7]萊維的話富有啟迪:20世紀生產力發展,科技飛速進步,但人類的道德并沒有顯著提升,制度的缺失導致人性中惡的釋放。當人性之惡難以遏制時,科技與嚴密的管理往往發揮著助紂為虐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奧斯威辛也是現代工廠體系在俗世的一個延伸。不同于生產商品的是: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終產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單位量被仔細地標注在管理者的生產表上,而現代工廠體系的象征——煙囪——則將焚化人的軀體產生的濃煙滾滾排出。還有現代歐洲布局精密的鐵路網向工廠輸送著新的“原料”,現代社會可以使不道德行為變得更合理。大屠殺是歷史的,也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悲劇,因為它不僅殺戮了600萬無辜的民眾,也因為它粉碎了自古以來的道德禁忌,毀滅了西方對理性規范法則的信仰,以及發現客觀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8]
大屠殺不應該消解在語言學或者統計學性質的一種抽象之中。抽象是不負責任的,而人類卻是負責任的。人類的元素一直是敘述的中心,因為只有采取這樣的方式,大屠殺才能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獲得重大的意義。[9]記住過往,是現世的人們對過往的人們所負有的義務。喪失了歷史記憶,也就沒有歷史正義可言。[10]因此,學生不應該把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記憶只停留在知識層面,停留在應付考試,博取高分上。奧斯威辛集中營應該成為他頭腦中一個永久記憶的空間,這個空間警示他不能忘記制度與人性的關系。每當他看到有關大屠殺的影像、小說、展覽及其他媒體形式時,他那塊記憶空間便會活躍起來,他應該為自由地生活在當下而慶幸;他應該能理解史學家甚至民間人士不遺余力地收集大屠殺證詞的工作;他應該對任何名義的專制保持警惕;他有責任自覺地參與維護和優化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正如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指出:“活著的人重新建構死去之人的生活,便成了歷史;而這樣做是為了活著的人。因此,歷史生發于思想著的、痛苦著的、行動著的人探索過去而發現的現實利益之中。”[11]對奧斯維辛的記憶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并為實現社會正義而努力。
【注釋】
[1]龍迪勇:《歷史敘事的空間基礎》,《思想戰線》2009年第5期。
[2][3]陳梧桐主編:《選修6世界文化遺產薈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0、112頁。
[4](荷)伊恩·布魯瑪:《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7頁。
[5][6](英)勞倫斯·里斯:《奧斯維辛:一部歷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16頁。
[7]轉引自張秋:《歷史的人質》,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10頁。
[8][9](美)克勞斯·費舍爾:《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11-12、10頁。
[10](以色列)阿維夏伊·瑪格利特:《記憶的倫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3頁。
[11](法)雷蒙·阿隆:《歷史意識的維度》,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