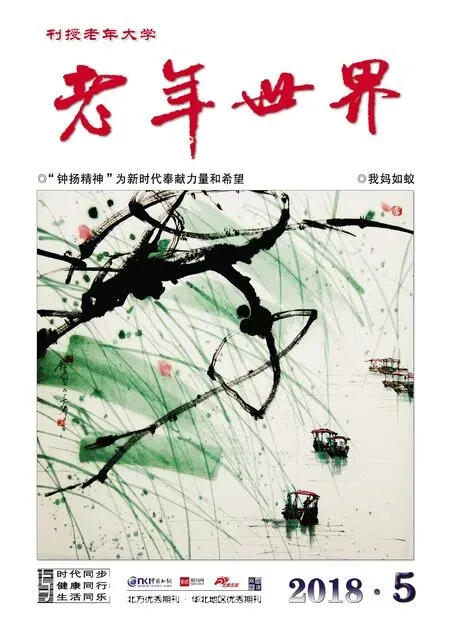老校長竇伯菊的幾件往事
徐新民
人老念舊,逢年懷人。這幾天經常在腦海里浮現出老校長竇伯菊的身影和笑臉。
和竇校長在一起,無論是當面受教,還是在會場一角聆聽她講話,甚或是遠遠地看見她在校園與偶遇的教師交談,你都會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還記得,竇校長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講話,是在2008年,內蒙古師范大學慶祝改革開放30年暨77/78級校友返校紀念大會上。在那次聚集了一大批杰出校友的慶典上,她笑容滿面,稱贊這些校友是師大的驕傲,叮囑他們要常回家看看!那語氣,那神情,就是一個老母親在對常年在外又即將登程的孩子們的叮嚀。
那是十年前,竇校長現在已是80高齡。
就是在這次紀念活動之中,得知了不少和竇校長有關的事情。其中最能展現她精神品格的是錄取張曉山。張曉山是胡風的兒子,那時在土默特左旗插隊,報考了內蒙古師范學院中文系。在錄取政審中,不少人主張,胡風的兒子,堅決不能錄取。當時“胡風反黨集團案”還沒有平反。時任教務處長的竇伯菊和中文系書記謝春明力排眾議,認為胡風的問題不應該牽連他的兒子。這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從極左思潮束縛中解脫的情況下,是要擔極大的政治風險,承受巨大的思想壓力的。但竇伯菊表現出了巨大的勇氣和超乎常人的見識。

竇伯菊
她當科研處長時曾規定,老師們到科研處辦事,辦公室工作人員要起身相迎,禮貌讓座。這成為許多老教師常常感念的話題。后來,竇伯菊當了校長,也把校風建設當作重要工作,在全校大會上多次強調,令人印象深刻。
當年開學初和學期末常常要開全校教職工大會,那時我還是工作不久的毛頭小子,在師大校刊工作。在一次全校會議的報道中,我寫道“在長達兩小時的報告中,竇伯菊校長強調……”
竇校長事后見到我,和藹地解釋說,剛開學,要講的事太多!說完臉上還有些歉意,這讓我惶恐不安。我在校刊工作五年,經常與竇校長接觸,她從來都是和顏悅色的。我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他對哪個下屬發過火。倒是我們這些不知輕重的毛頭小子對她時有不恭。
竇校長是1951年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來到內蒙古的。記得是在1985年前后吧,北京師范大學校友會內蒙古分會要開會。當時,竇校長是會長,我任秘書。我向會長提出要從校友會費里支錢辦會,當時會長批給的經費多于所需。我半開玩笑同時也很不客氣地說,您是花慣大錢的人。竇校長卻笑著說,那你節約著花,多余的剩回來。
當然,竇校長也有批評人的時候。我在校刊工作五年后,調到中文系教書。過了兩年評講師,因教學年限不夠受阻。在遇到竇校長時,我不免有些抱怨,說了些在校刊吃虧之類的昏話。竇校長當即正色道,不要忘了校刊還培養了你。幾年后我才知道,多年主持學校職稱評定工作,教學、科研等方面一直突出的竇校長,自己卻一直沒有申報教授,她說她不愿和一線教師爭指標。直到退休,她這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研究生仍然是副教授。這使我十分慚愧。
不止一次聽說,她會在校園里與熟識的女教工拉家常,并且會把自家做的泡菜與人分享;她會給家在外地的年輕孕婦準備好全套的嬰兒服;困難時期還曾把自家少得可憐的白面和每人每月憑票供應的肉拿來蒸好包子送給產婦;忙起工作來,常常不能給孩子做口熱飯;地震預報時,全校師生在第一時間聽到她在廣播中指揮調度,而她的兩個女兒只能跟著鄰居行動。沒有哪個母親不愛自己的孩子,但作為校長,竇伯菊選擇把對孩子的愛強壓心底,而把學生和同事們時時刻刻放走心頭,她把滿腔的慈愛奉獻給了更多的人。
我記述的都是平凡瑣事,這并不意味著竇校長僅僅是個和善而平庸的領導。其實,竇校長在任抓了不少大事,學風建設、教風建設、教學科研……所有這些都是她重點專項。她在任時提出的“獻身、求實、團結、奮進”校訓,已成為內蒙古師大人的共同志向。
她秉持和踐行了北京師范大學“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校訓,她成為母校的驕傲。溫家寶總理曾在北京師大2011屆畢業典禮中講到,竇伯菊校友是支援邊疆,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成長的優秀人才,是師大學生的榜樣。而扎根內蒙古,辛勤耕耘幾十年的竇伯菊也殷殷期望,自己培養的學生也能成為內蒙古師大的驕傲。確實如此,園丁精神,薪火傳承,桃李芬芳,一批批師大學子奔赴內蒙古教育事業的第一線,為家鄉的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
如今,老校長臥病在床,已經與病魔搏斗了數年。我們這些晚輩感懷歲月,銘記師恩,為老校長虔誠祈禱,祝愿她身體健康,吉祥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