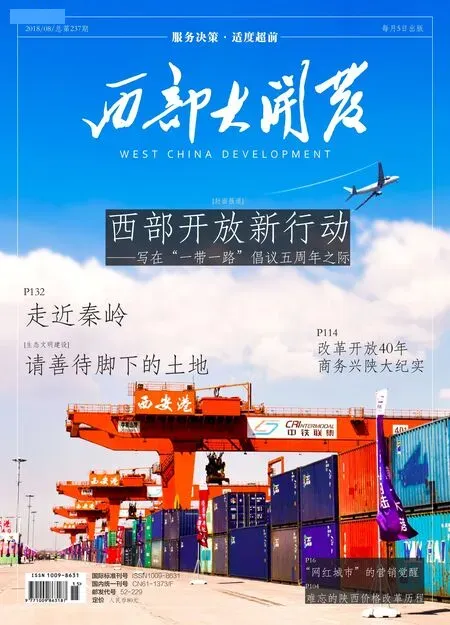還需繼續向縱深發展
——訪“三農”學者、農村電商專家魏延安
文 / 本刊記者 張永軍
記者:2014年農村電商正式興起,您覺得這四年來,農村電商都經歷了哪些階段?最大的變化在哪?現在與初期的面貌有哪些不同?
魏延安:農村電商發展到今天,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農村電商正處在農村與電商的新時代,電商的風口在變,農村的格局在變,農村電商也因時而變。粗略算來,大體經歷了七次流變。
第一次流變,大體在2013年6月至12月,算是農村電商的前傳,城市燒得火熱的電商大戰開始試探性地向農村延伸。這一時期可以稱之為,小荷才露尖尖角,電商從城市向農村的探望。
2013年京東即在山東德州嘗試做了一批合作站,主要針對鄉鎮市場,京東允許配送員脫離公司,以自然人的身份成立合作站,自負盈虧,與京東簽訂排他合同,京東會在配送單價上給予優惠。到2013年第四季度,劉強東提出京東的“渠道下沉”戰略,開始大舉向鄉村挺進。2013年6月浙江遂昌的趕街網首個運營中心搭建完成,設計的業務四大板塊正是今天所有農村電商平臺都差不多沿用,服務體系也是目前被大家普遍采用的“縣有中心村有站”模式。2013年不同方面開展的各類嘗試,為農村電商的興起起到了預熱和探路的作用。
第二次流變,大體在2014年1月至6月,先后有60多家互聯網公司不約而同地在農村掀起了刷墻大戰。這一時期可以稱之為,風雨欲來風滿樓。
農村電商最早的刷墻在2013年就開始了,2013年第四季度京東喊出“既能出國,也要下鄉”的口號后,隨即開始農村刷墻,到2014年3月即在全國100多個鄉鎮刷了8000幅墻體廣告。2014年春天各大電商到農村的刷墻讓一個叫村村樂的公司一度估值10個億。大家都看到了農村未來的電商市場前景,刷墻就是一種摩拳擦掌。這一時期各大電商平臺也有動作,但整體還是業務向農村的延伸,尚沒有明晰的農村電商戰略出臺。
第三次流變,大體在2014年6月到12月,期間農村電商“大事件”緊鑼密鼓發生。可以稱之為,城頭變換大王旗,農村電商戰略紛紛出爐。
例如,2014年6月,京東從河北廊坊市開始,正式向縣域拓展業務;7月,馬云前往浙江麗水,實地考察農村電商平臺——趕街網;8月,商務部會同財政部在8個省開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項目試點,安排中央資金48億元,支持256個示范縣發展農村電子商務;10月,阿里巴巴“千縣萬村”計劃出爐;11月,京東“千縣燎原”計劃推出;12月,蘇寧宣布在縣以下建設10000家蘇寧易購服務站。政策的春風和阿里巴巴、京東、蘇寧的“三國演義”,迅速“吹皺”了農村電商的“春水”,各大電商平臺加大對縣以下的滲透。
第四次流變,大體在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在這整整的一年時間里,各大電商平臺掀起了在農村跑馬圈地的高潮,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各大電商平臺縣鄉站點建設的最新數字。這一時期可以稱之為,千里鶯啼綠映紅,電商下鄉你追我趕。
到2015年底,跑得最快的京東宣布建成600個縣級服務中心,1100個京東幫服務站,招募了12萬名鄉村推廣員;阿里巴巴則建設了10000個農村淘寶服務站;蘇寧建成1500家蘇寧易購服務站。同時,各大電商平臺的策略也開始調整,2015年4月劉強東正式提出京東“3F戰略”,5月農村淘寶2.0版本發布,由原來的依托現有門店建立改為獨立自建門店,蘇寧也在年底將自己的農村電商戰略調整為人才、扶貧、上行、服務等重點領域。也在這一年,因為聯想投資農資電商——云農場引發了農資電商的集體喧囂,農資電商平臺建設紛紛上馬。得到國家大力支持的供銷總社則經過半年的籌備,旗下的“供銷e家”大型涉農電商平臺也于2015年9月底上線。郵政旗下的郵樂網也加快農村電商市場的擴張,到2015年底已經在全國完成11萬個村的覆蓋。加上中國電信的介入,“國家隊”的入場讓農村電商的競爭日趨激烈。

第五次流變,大體從2015年5月開始,一直持續至今。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電商扶貧逐漸成為各大農村電商的主題。
2015年的春天,各大電商平臺的農村爭奪戰繼續延續,但熱度明顯下降,趕街網率先停下了擴張的腳步,電商扶貧接過了電商下鄉的接力棒,繼續引領農村電商前行。2014年12月,國務院扶貧辦首次將電商扶貧列入十大扶貧工程;2015年5月,國務院扶貧辦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甘肅隴南啟動電商扶貧試點;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印發,明確提出實施“電商扶貧工程”;2016年11月,國務院扶貧辦聯合15個國家部委印發《關于促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在一系列電商扶貧政策出臺的基礎上,國務院扶貧辦還先后于2015年、2016年“國家扶貧日”召開電商扶貧論壇,在甘肅隴南召開電商精準扶貧現場會,與蘇寧、京東等電商平臺簽訂合作協議,推動各電商平臺、各貧困地區出臺電商扶貧計劃。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京東、蘇寧、一畝田、樂村淘、郵樂網等電商平臺紛紛出臺扶貧計劃,而一度放棄了電商的騰訊則升級自己的鄉村公益頻道為新的互聯網+鄉村平臺——“為村”,2015年8月公開發布后,到2017年2月全國共有3269個村申請加入。

第六次流變,大體從2017年4月開始,一直持續至今。可以稱之為,風掣紅旗凍不翻,農產品上行成為新焦點。
農產品上行一直是一個焦點,雖然呼聲較高,各大平臺動作頻頻,但整體與基層政府和農民的期待有較大差距。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加強農產品上行。2017年4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連續三天追蹤報道農村電商發展,指出目前的農村電商在工業品下行方面轟轟烈烈,而農產品上行卻提不起精神。電商界及社會各方隨即對農產品上行問題給予空前關注,各大電商平臺也紛紛推出專門的農產品上行計劃。2017年5月,財政部、商務部《關于開展2017年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要“聚焦農村產品上行”。2018年5月,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印發通知,決定2018年繼續開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同時中央財政資金將重點支持農村農產品上行、農村公共服務體系、農村電子商務培訓等三大方向。迄今為止,農產品上行已經成為農村電商發展中政府、平臺、網商和農民共同關注的焦點。
第七次流變,同第六次一樣,大體也從2017年4月開始,一直持續至今。可以稱之為,前度劉郎今又來,農村也趕上了新零售的風口。
2017年春天,京東率先調整自己的農村電商板塊,提出“新通路”計劃;2017年4月,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公開宣布,未來五年要開100萬家京東便利店,其中一半開在農村。作為回應,2017年8月阿里巴巴CEO張勇宣布,阿里零售通將在一年內服務100萬家線下便利店,年內“天貓小店”突破一萬家。阿里巴巴、京東在線下特別是在農村線下的爭奪,拉開了農村電商新一輪競爭的序幕,也是新零售戰略在農村布局的具體體現。今天電商向農村線下門店的滲透,大有“前度劉郎今又來”的感覺,只是內核已經變成了“互聯網+”,農村電商從此進入線上線下一體的新階段。而原來獨自建立的農村電商基層站點也面臨運營上的調整,融合必不可免。
記者:從這七次流變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各類電商平臺在搶占市場中有著激烈的競爭,但這也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商網的融合,最終受益的還是農村和農民。受益有目共睹,問題也突出存在,您認為目前農村電商在發展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魏延安:四年來,農村電商在充滿爭議中艱難探索,在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發展中的問題。較為突出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模式依然不夠清晰。到今天為止,各大電商調整了幾次農村電商模板,但依然不能說完全符合農村實際,也無法就此定型,還需要繼續探索。突出的表現是,短期內難以盈利,許多農村基層站點建立后運營維持困難;一些設計的農村電商業務內容缺乏基礎支持,也缺乏群眾基礎,推廣緩慢;還有大量的農村電商服務體系在政策性補貼結束后,難以進行市場化運營;一些過多的附加功能如在線醫療、網絡金融等還需要電商基礎用戶群的拓展。一些參與農村電商的企業和創業者在初期的興奮后,陷入迷茫和彷徨,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二是農產品上行還需再給力。2016年中國電商零售規模達到5.16萬億元,而現口徑統計下的農產品電商零售僅1589億元,只占3.1%;整體生鮮農產品交易規模約在4萬億元,而目前生鮮零售規模只有914億元,只占2.3%。整體上農村通過電商買回來的遠遠多于賣出去的,電商“逆差”嚴重,成為農村電商最受人批評的“硬傷”。如2015年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零售平臺上共完成消費1517.61億元,同比增長50.39%,為貧困地區節約支出超過150億元;完成銷售215.56億元,同比增長80.69%。雖然這一組數字中,農產品上行速度遠遠快于工業品下行,但因為基數差距太大,短期無法平衡。當然,這一“逆差”不可以從道德角度簡單批判,農產品上行體系的不成熟還需要時日來完善。
三是人才匱乏的局面依然沒有得到破解。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不管是農產品電商還是工業品電商,大家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就是缺少人才。四年過去了,各地的培訓規模有上千萬人次,但依然遠遠不能滿足農村電商發展的需要。仔細分析,大量的農村電商培訓解決了有人知道電商是什么、應該怎么干的問題,但能干得好、而且具有示范帶動能力的優秀人才始終短缺,一些技術含量的專業人才更加緊俏,這也與農村電商服務體系不夠健全有關。

四是農村電商的生態依舊脆弱。農村電商不是一個平臺、一個企業可以獨木成林的,需要電商交易體系的完備、物流倉儲加工等方面的配套,更需要一個十分健全的產業體系支撐。但在大多的縣,完整的農村電商生態迄今沒有形成,一些地方的網絡通信、交通物流還十分落后,電商發展亟需的相關服務缺失,電商發展相當于在荒漠上種樹,成活困難。農村電商各要素之間的協同還十分不夠,各平臺之間各自為政,數據、物流無法有效打通,運營效率難以提升。
五是農民的獲得感還有待提升。雖然農村電商占據著媒體上的主動,經常有連篇累牘的報道,也有很多的專家評頭論足,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作為農村電商最終的受體,廣大農民對于農村電商的感受還不深刻,他們從電商中得到的好處還沒有那么明顯,需要盡快從點到面,讓更多的普通農民感受到電商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改變,特別是在幫助農民網上銷售農產品方面。
反思當前農村電商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特別需要改變過分重視電商而對農村重視不夠的現狀。農村電商未來也不會是獨立的經濟形態,只是在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進程中擔負著先鋒軍和催化劑,未來會成為農村互聯網新經濟也即中央最新提出的農村數字經濟的一部分。農村電商要進一步發展,必須更加地懂農村,懂農業,懂農民,積極地推動電商與“三農”主動的、全面的融合。
記者:那反過來講,就是說,農村電商要成為未來農村互聯網新經濟,成為農村數字經濟的一部分,就要靠一批懂農村,懂農業,懂農民的電商人來實現,那么,結合當前農村電商的實踐和實際,請您談一談,農村電商給農村和人們帶來哪些啟示?
魏延安:我認為,首先正視農村與城市的差別是重要前提。到今天為止,很難說農村電商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依然走在艱難探索的前路上。如果不能正視農村與城市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依然套用城市電商的發展模式,那么農村電商有可能在前進的道路上還要摸索更長時間。一些農村電商平臺迄今沒有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一些農村電商站點還存在長期持續經營的問題,一些參與農村電商創業的年輕人面臨業績的壓力,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對電商十分精通,而對于農業、農村很不熟悉,對農民相當陌生。
其次找到適合農產品上行的路徑是重要課題。在農產品上行的問題上,不是大家不愿意做,而是確實很難做。目前擺在農產品上行面前的現實困難是,如何讓其路徑變得更加通暢和可行。如果套用一般工業品的模板,則農產品做起來十分地艱辛,因為它是有生命的活體,需要保鮮,無法標準化,工業品電商的標準必須帶來削足適履。如果讓電商遷就于農產品,則普通消費者又不滿意。必須找到一條路徑,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農產品的真實生產過程,在理解信任中找到“中庸”的道路。
第三帶動廣大農村群眾的主動參與是重要基礎。好多地方的電商啟而不動,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農民群眾在中間沒有體驗到應有的獲得感,依舊在觀望。那些電商發展比較好的縣,往往呈現出人民戰爭的場景,千軍萬馬,人歡馬叫,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隴南等地的電商扶貧就是這樣,武功、沐陽、碭山等農產品電商大縣也是這樣。反觀一些縣,則只有幾個所謂的龍頭企業和一些創業者參與,始終不能從“盆景”變成“風景”。
第四探索有效的行政推動體系是重要保障。電商在農村,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的農村,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擺在面前的首要困難是思維和理念上的銅墻鐵壁。所以,農村電商出現了很多電商書記、電商縣長和一批網紅干部,這是特定時期出現的特定現象。因為,在一個縣,只有一把手才可以調動足夠多的資源和人力,才有足夠的魄力打開農村電商發展的缺口;只有干部帶頭了,群眾才敢跟得上。當然,農村電商不僅僅是一把手工程,還需要懂得什么時候敢于出手,什么時候又敢于放手。在初期沒有人敢干的時候,要對那些敢于嘗鮮的人及時搭把手,扶上馬,送一程;大家普遍參與進來的時候,政府就要及時松手,讓他們自己闖市場,政府則退到幕后做好規范市場秩序、優化市場環境、提供配套服務等工作。
第五協同電商各方要素是重要手段。各地的實踐反復證明,無論是政府也好,平臺也好,還是大的電商也好,誰都無法獨立完成一個地區農村電商生態的建設任務。協同政府、平臺、電商、傳統企業甚至普通農戶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構建農村電商的生態是成功與否的一個關鍵點。如果能有效協同這些要素,一個縣的電商就有可能發展快一些;如果不能協調這些要素,還是各自為戰,這個縣的電商發展可能就慢一些。
第六培養一批農村電商人才是重要條件。干事興業靠人。能不能有效吸引凝聚一批優秀的電商人才對一個縣的電商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全國有一批書記、縣長能系統并聯系實際地學會電商、一個縣還有一批會懂會干電商的一線干部、每個鄉村還有幾個愿意學習主動參與的電商創業者,則農村電商的發展將會大大加快。

記者:從2015年國務院扶貧辦開展試點至今,電商扶貧已經從一種理念演化為一種共識,也從初期的探索演變為廣泛的實踐。2017年,全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項目已經覆蓋全國499個國家級貧困縣;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實現網絡零售額1207.9億元,高出農村平均增速13個百分點。那么,當前的電商扶貧還有哪些問題需要正視和解決?
魏延安:電商扶貧在政府、平臺、網商、傳統生產主體等多方面力量推動下,蓬勃發展,為脫貧攻堅注入了新動力。當前電商扶貧要解決好四個現實問題。
首先,在理念層面,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開闊視野。不能繼續停留在教幾個貧困戶開網店、搞幾次活動在網上賣幾次農產品這樣的淺表層次上。而是要考慮如何與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與脫貧攻堅的主要目標深度結合的有效措施,以電商來推動就業扶貧、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公益扶貧,與之實現深度融合,避免為電商而電商。
其次,在實踐層面,需要加快破解面臨的一系列困難。電商扶貧面臨的困難,通常包括網絡基礎落后,快遞物流不發達,農產品不標準,人才匱乏等。推動電商扶貧,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打持久戰,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從打基礎的事情開始。如大力加強人才培養,既授人以漁,還要營造漁場,真正扶上馬,送一程;破解快遞物流問題,必須有協同共享理念,抱團取暖,把運營成本先降下來。特別是“手”要伸得再長一些,從賣農產品延伸到改造農產品生產體系,推動供給側改革,打通供應鏈,創新產業鏈,重塑價值鏈。
第三,在評價層面,要突出貧困主體的獲得感。不能把電商扶貧當個筐,什么都往里裝,不能把貧困區域的電商業績等同于電商扶貧的成績;也不能把簡單的電商活動等同于電商扶貧的長效機制,搞一陣風;更不能把空頭支票當做宣傳噱頭,吊群眾的胃口。而是必須聚焦到貧困主體,體現精準要義,讓貧困地區群眾切切實實感受到電商帶來的實惠。檢驗電商扶貧成效好不好,要看有多少貧困農戶因為電商脫了貧,平均到每個農民身上能增加多少收入,對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有什么實實在在的帶動。
第四,在方法上,要注意各方力量的有效協同。政府、平臺、網商、服務商、傳統企業、農村經營主體及貧困戶,是電商扶貧的六支重要參與力量,缺一不可。但從實際情況看,政府各部門、各大平臺、各個網商及服務商之間還缺少有效協商,各自為戰的多,密切協作的少,本來就稀薄的電商要素在貧困地區還相對分散,難以形成合力,也不夠經濟有效。傳統企業、農村經營主體及貧困戶還缺少有效帶動和幫扶,勢單力薄。應加快建立政府引導、平臺開放、各方力量參與的電商扶貧協同機制,進一步提升電商扶貧效率。特別是地方政府,要從系統思維出發,發揮統籌協調作用,積極完善電商生態,引導各方力量擰成一股繩。
總之,當前的農村電商,我們要理性地看,踏實地干。登山的時候,只有低頭才知道自己身處什么位置;遠行的時候,只有回望才知道距離出發已經有多遠。毋庸置疑,農村電商在不長的時間里,已經取得了不曾預想的突破,掀開了互聯網時代農村變革的新序幕,其未來是值得更多期待的。而所有身處其中的探索、創新、挫折,最終都會共同積淀為農村歷史進程中厚重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