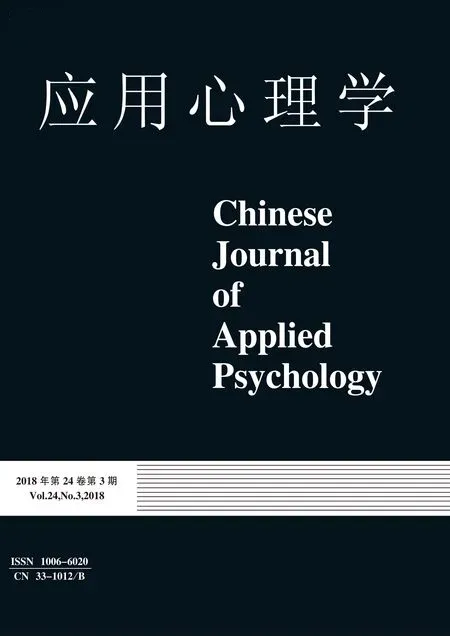完美主義對大學生學業拖延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
*
(1.寧波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寧波 315211;2.浙江省象山中學,象山 315700;3.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合肥 230026)
1 前 言
學業拖延(academic procrastination)是近年來自主性學習領域的一個研究熱點,是拖延在學習情境中的具體表現,指在有限時間范圍內推遲學習任務直到臨近期限才開始進行的行為傾向(Steel,2007)。學業拖延不僅浪費學生的大量時間、失去完成任務的最佳時機影響其學習成就(倪士光,李虹,黃琳妍,2012);這種優柔寡斷的行為傾向也容易使拖延者產生自我懷疑、焦慮、內疚、抑郁等消極情緒體驗并對其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Glick & Orsillo,2015;曲星羽,陸愛桃,宋萍芳,藍伊琳,蔡潤楊,2017)。目前研究者主要關注學業拖延帶來的消極影響,對學業拖延作用機制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龐維國,2010;曲星羽等,2017)。基于此,本文主要對影響大學生學業拖延的相關因素及其作用機制進行了深入探討。
近年來,有關學業拖延的研究主要從個體的認知因素、自我監控、情緒調節、人格特質等方面探討了學業拖延的成因及其影響因素(Glick & Orsillo,2015;Kim,Fernandez,& Terrier,2017)。其中,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是一種追求高標準完成任務且具有自我批判傾向的人格特質(Frost,Marten,Lahart,& Rosenblate,1990)。作為一種人格因素,它與學業拖延的關系近年來開始受到研究者關注(Closson & Boutilier,2017;遲昊陽,趙冉,侯志瑾,林楠,2012)。以往有關完美主義的研究者,大多將完美主義視為單維度的消極和破壞性人格特質(陳陳,燕婷,林崇德,2013)。隨著該領域研究的深入,完美主義的多維度結構觀開始被學者們廣泛接受和認可(Bong,Hwang,Noh,& Kim,2014;Rice & Richardson,2014)。例如Egan等人(2015)發現,完美主義有積極和消極兩種類型,二者有不同的心理特質。我國學者也發現完美主義并不是一個單維的消極心理特質,也存在積極、健康的完美主義者(張斌,謝靜濤,蔡太生,2013;張萌,陳英和,2013)。Sahraee等人(2011)發現,在大學生群體中消極完美主義者和積極完美主義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分別占到調查人數的26%和48%。有研究發現,積極完美主義者有計劃性和組織性,對自身要求嚴格、對任務目標更加主動(Zhou,Wu,Zhu,& Cai,2016);而消極完美主義者則懼怕失敗、自我否認,擔心自己的行為結果無法實現預期的高標準,通常持消極的自我認知傾向(Fletcher,Shim,& Wang,2012)。基于積極和消極完美主義者具有不同的心理特質,本研究將分別探討兩種不同類型完美主義對學業拖延的影響作用。
拖延行為的時間取向模型(Temporal Motivation Theory,TMT)指出,在人格特質(完美主義)對拖延行為的影響過程中,對任務期限的時間知覺和個體的自我概念具有重要作用(宋梅歌,蘇緹,馮廷勇,2015;張順民,馮廷勇,2017)。
時間管理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個體對時間的價值、功能以及運用方面體現出來的一種穩定的心理和行為特征(黃希庭,張志杰,2001)。根據時間折扣理論,個體在進行任務選擇時有低估未來任務價值的傾向,對未來任務傾向于拖延而選擇可以獲得即時回報的當前任務,延緩的時間使未來任務價值折損,從而降低個體完成將來任務的動機(宋梅歌,蘇緹,馮廷勇,2015)。學業拖延正是這種低估未來學習任務價值的體現(韓會芳,李義安,韋嘉,張進輔,2014)。例如,大學生在面對任務選擇時,更傾向于選擇能立即獲得回報的當前任務(如打游戲、購物等),而對未來的學業任務進行拖延。也有研究發現,時間管理傾向能顯著地負向預測學生學業拖延的程度(周永紅,呂催,楊于岑,2014)。由此看來,不良的時間管理傾向可能是學業拖延的風險因素。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積極完美主義者能確立合理的任務目標,對自己的時間管理能力以及在時間統籌方面的信心有較好的評估,更加善于安排和利用時間;而消極完美主義者則盡力避免失敗,通常有較差的時間管理能力和不合理的時間安排(Bong,Hwang,Noh,& Kim,2014;佟月華,陳瑛,2008)。同時也有研究發現,時間管理傾向在大學生成就目標定向對學習投入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黃海雁,許國成,付瑩,2017)。基于以上的研究可以推測,個體的時間管理傾向可能在完美主義對學業拖延的影響過程中起著中介作用。
研究者提出,學業拖延本質上是一種自我調節的失敗或自我控制不良,學業拖延的發生很可能受到個體內部自我調節的影響(龐維國,2010;倪士光,李虹,黃琳妍,2012)。自尊(self-esteem)是個體對自我價值與能力的情感體驗,作為自我概念的重要成分具有評價性意義(Leary,2005;田錄梅,夏大勇,李永梅,單楠,劉翔,2016)。高自尊個體對自己持積極的評價,在生活中較自信、通常聚焦于問題的解決,在學業任務上較少采用回避性策略;而低自尊個體對自身缺乏信心,認為選擇超出能力的任務容易導致失敗,因此會回避困難型學業任務,通過拖延行為進行自我設阻以維護自己的形象(楊文龍,2017)。也有研究發現,良好的時間管理傾向和高自尊均為個體的資源因素,對學業拖延的發生能夠起到緩沖作用(韓會芳等,2014)。李董平(2012)提出的“錦上添花”模型,認為一種資源因素會放大或增強另一種資源因素的有利影響,即一種資源因素高者較之該資源因素低者,其發展優勢更多體現在另一種資源高而非該資源因素低的情況下,這種模式被稱為“保護—保護因子模型”的“促進作用假說”(陳武,李董平,鮑振宙,閆昱文,周宗奎,2015;葉寶娟等,2018)。根據該模型,高自尊大學生相比于低自尊大學生而言,其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保護作用更強。具體而言,當個體自尊水平較高時,隨著時間管理傾向的增加,其學業拖延行為呈下降趨勢;而個體自尊水平較低時,隨著時間管理傾向的降低,其學業拖延行為的下降趨勢減緩,即自尊可能會調節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影響。鑒于以往自尊與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作用研究不夠深入,本研究擬深入探討自尊作為個體的一種保護性因素,是否能夠進一步提升時間管理傾向對大學生學業拖延的改善和保護作用。
綜上,本研究主要探討完美主義對學業拖延的影響,在此基礎上考察時間管理傾向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對該中介過程的調節作用,以揭示完美主義影響學業拖延的過程及其發揮作用的條件,以期為大學生學業拖延的干預提供理論指導。各變量關系的假設模型見圖1。

圖1 有調節的中介假設模型圖
2.1 被試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600名在校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共收回578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為96.3%。其中,男性316名,女性262名;大一174名,大二161名,大三137名,大四106名;年齡在17歲至23歲之間,平均年齡19.76歲(SD=1.63)。
2.2 工具
2.2.1 完美主義
采用訾非和周旭(2006)修訂的中文版完美主義量表,共27個題項,包含條理性、個人標準、父母期望、擔心錯誤和行動疑慮五個維度。其中“行動疑慮”、“擔心錯誤”、“父母期望”和“個人標準”為消極完美主義維度,“條理性”為積極完美主義維度(陳陳,燕婷,林崇德,2013;劉艷麗等,2016)。采用5點計分,1~5分別表示“不符合~符合”。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4,各維度的α系數分別為0.74、0.82、0.76、0.79、0.72。
2.2.2 時間管理傾向
采用黃希庭等人(2001)編制的時間管理傾向量表(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包含時間監控觀、時間效能感和時間價值感三個維度,共44個項目,采用5級評分,得分越高表示個體的時間管理傾向水平越高。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2,各分維度的α系數依次為0.83、0.76、0.84。
2.2.3 自尊
采用王孟成等人(2010)修訂的中文版Rosenberg自尊量表(Chines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該量表由10個項目組成,采用4級評分,1表示“很不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分值越高表明個體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6。
2.2.4 學業拖延
采用趙婉黎(2007)編制的大學生學業拖延量表(College Studen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Scale),包含計劃不足、完成不佳和延遲行動三個維度,共19個項目。采用5級計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總分越高表示被試的拖延程度越高。以往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張斌,蔡太生,2010)。本研究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6,各分維度的α系數依次為0.82、0.75、0.84。
2.3 分析思路
按照Erceg-Hurn等人(2008)的建議,采用Bootstrap法對回歸系數顯著性進行檢驗。該方法無須假設樣本服從某種分布,而是通過對原樣本進行有放回的隨機抽樣來重新構造樣本分布(本研究共構造1000個樣本,每個樣本容量均為578人),獲得參數估計的穩健標準誤及95%偏差校正的置信區間,若置信區間不含零則表示有統計顯著性。
3 結 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本研究在施測時采用匿名、部分項目反向計分等措施進行控制(周浩,龍立榮,2004)。在數據分析時,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進行了共同方法偏差驗證。結果發現,特質根大于1的因子19個,且最大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13.84%,遠小于40%的臨界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
3.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1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積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呈顯著負相關,與時間管理傾向、自尊均呈顯著正相關;時間管理傾向、自尊均與學業拖延呈顯著負相關。而消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呈顯著正相關,與自尊呈顯著負相關,與時間管理傾向的相關不顯著,不滿足中介分析條件,因此不再繼續探討消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的中介作用。此外,學業拖延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t=-3.45,p<0.05,d=0.02)。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N=578)
注:a性別為虛擬變量,女生=0,男生=1;*p<0.05,**p<0.01,***p<0.001,下同。
3.3 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根據溫忠麟等人(2014)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程序,采用Hayes(2013)編制的SPSS宏程序,在控制性別變量的條件下分別以時間管理傾向為中介變量,自尊為調節變量進行模型檢驗。根據假設,本研究僅檢驗中介鏈條的后半段是否受自尊的調節,若回歸方程檢驗既滿足了中介作用,又證明了中介鏈條上的調節效應,則表明研究者提出有調節的中介的理論模型成立(張曄,劉勤學,隆舟,艾婷,2016)。對各預測變量均進行了中心化處理,方差膨脹因子的得分均不高于1.36,這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檢驗結果見表2。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注:模型中各變量均經過中心化處理后代入回歸方程。
如表2所示,方程1中積極完美主義正向預測時間管理傾向。方程2中,時間管理傾向負向預測學業拖延,自尊負向預測學業拖延,時間管理傾向與自尊的交互項對學業拖延的預測顯著。這表明,時間管理傾向在積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之間起中介作用,而自尊在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影響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為更清楚地解釋時間管理傾向與自尊交互效應對學業拖延影響的實質,將自尊按照正負一個標準差分成高、低組進行簡單斜率分析,探討在不同自尊水平上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影響。圖2的結果表明,對于低自尊水平個體,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Bsimple=-0.17,SE=0.03,p<0.05);而在高自尊水平時,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預測作用顯著增強(Bsimple=-0.32,SE=0.05,p<0.01;Bsimple由-0.17增強為-0.32)。這說明,相對于低自尊個體,時間管理傾向對高自尊個體學業拖延的影響作用更顯著。

圖2 自尊對時間管理傾向與學業拖延關系的調節作用
進一步對整合模型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模型擬合程度較好(χ2/df=3.06,CFI=0.94,NFI=0.92,GFI=0.91,RMSEA=0.035),見圖3。其中,積極完美主義顯著負向預測學業拖延(γ=-0.22,p<0.001),自尊顯著負向預測學業拖延(γ=-0.17,p<0.01);積極完美主義顯著正向預測時間管理傾向(γ=0.26,p<0.001),時間管理傾向顯著負向預測學業拖延(γ=-0.16,p<0.01),這表明時間管理傾向在積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時,時間管理傾向和自尊的交互項顯著負向預測學業拖延(γ=-0.20,p<0.01),這說明自尊對時間管理傾向的中介效應存在顯著的調節作用。

圖3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
4 討 論
4.1 時間管理傾向在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之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積極完美主義和消極完美主義分別與學業拖延呈顯著負相關和正相關,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Burns,Dittman,Nguyen,& Mitchelson,2000;劉艷麗等,2016)。進一步對時間管理傾向的中介效應檢驗發現,時間管理傾向部分中介了積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的關系,即積極完美主義既可以直接影響學業拖延,也可以通過時間管理傾向間接影響學業拖延。積極完美主義者通常能夠設置合理的任務目標、追求成功,并從中獲得滿足感,做事具有條理性和組織性(Zhou,Wu,Zhu,& Cai,2016;陳陳等,2013),因此在學習時間的安排上更具計劃性和針對性,能通過合理的時間安排來完成學業任務。已有研究也表明,積極完美主義傾向個體具有較強的時間管理能力,在目標設定、任務計劃、時間統籌等系列活動中展現出良好的自我協調能力(邱芬,季瀏,崔德剛,2010)。由此可見,積極完美主義者能通過合理的時間安排來完成學業任務,學業拖延現象較少。而在消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的關系之間,未發現時間管理傾向的中介效應。可能的解釋為消極完美主義者在面對學業任務時具有眾多不合理的認知信念,如設立不合實際的目標、自我懷疑、對任務失敗的過度苛刻以及從活動任務中較少體會到樂趣等(陳陳,燕婷,林崇德,2013),他們會因過度擔心犯錯而選擇拖延或者回避性策略(Tops,Koole,& Kijers,2013)。因此,消極完美主義者可能因其本身具有的不合理認知信念會直接導致其學業拖延行為的發生,而不需要通過其他中介變量發生作用。
4.2 自尊對時間管理傾向中介路徑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自尊對時間管理傾向影響學業拖延的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應。具體而言,相比于低自尊大學生,良好的時間管理傾向對高自尊個體學業拖延的影響更為明顯,這與以往關于自尊對學業拖延具有保護性作用的研究結論一致(張斌,蔡太生,2010)。自尊作為自我概念的重要成分,是個體對自我價值的整體性評價,影響個體的認知與行為發展(張林,曹華英,2011)。積極完美主義者具有較高的要求和標準,做事具有條理性和計劃性,此時若個體擁有較高的自尊水平,對自身能力和價值都估計較高,在完成任務時就會有更強的時間掌控力,有更為合理的時間安排(邱芬等,2010),而較好的時間管理能力則是完成有時限性學業任務的重要前提。也有研究發現,相對于高自尊個體,低自尊個體具有較低的自我評價,認為選擇超出能力的任務是對自身缺乏價值的確認,傾向于通過拖延來逃避任務,具有較差的時間管理水平(韓會芳等,2014),這也符合學業拖延在本質上是自我調節失敗的觀點。另外,本研究中自尊的調節效應也進一步驗證了“保護—保護因子”模型的促進作用假說,即相對于低自尊的個體,時間管理傾向對高自尊個體學業拖延的作用更顯著。這說明對于學業拖延大學生,可以通過促進其形成積極自我評價、提升自尊水平,從而有效提升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改善作用,從而更好地幫助其有效降低和減少學業拖延行為。
4.3 研究意義和展望
學業拖延是大學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對其學業任務和身心健康均有不利影響。本研究從時間知覺角度揭示了完美主義影響學業拖延的中介過程,并考察了自尊在其中的調節作用,有助于深化我們對學業拖延發生機制的認識,研究結果對學業拖延發生機制的理論構建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另外,本研究的結果對有效預防和干預大學生學業拖延問題也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本研究的發現提示我們要重視學生良好時間管理能力的培養,學校可通過時間管理相關實踐課程來提升學生的時間管理能力,家庭也需要重視學生在成長過程中良好時間觀念的形成。同時,本研究中自尊調節作用的發現,也提示我們要重視對低自尊大學生的心理干預,幫助其對學業與自我形成積極的認知評價,這可能也是一種能夠有效減少學業拖延的方法。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在未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改進。首先,采用自陳量表評估學業拖延,難以考察具體情境下的拖延行為,未來研究可通過設置具體任務情景來探討學業拖延的發生機制;其次,橫斷研究無法得出明確的因果關系推論,未來研究可采用縱向追蹤研究進一步考察和驗證學業拖延的內在機制;最后,本研究無法完全排除可能存在的社會贊許效應,未來研究可采用學生自評與教師同伴他評相結合的方法提高測量結果的客觀性和有效性。
5 結 論
(1)積極完美主義顯著負向預測學業拖延,消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呈顯著正相關;
(2)時間管理傾向在積極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積極完美主義可以直接影響大學生學業拖延,也可以通過時間管理傾向間接影響學業拖延;
(3)時間管理傾向對學業拖延的預測受到個體自尊水平的調節,相比于低自尊大學生,時間管理傾向對高自尊大學生學業拖延的預測更為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