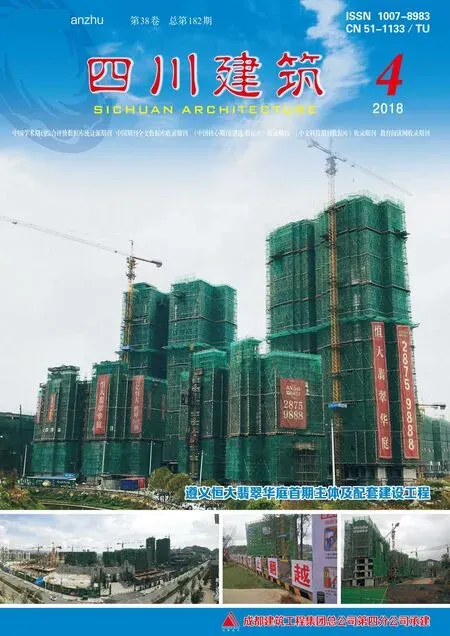社會(huì)空間視角下的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要義解讀
趙婉婷
(西南交通大學(xué)建筑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城鄉(xiāng)規(guī)劃系,四川成都 611756)
城市是一種社會(huì)空間,是資本物化的客觀實(shí)在,這種實(shí)在表現(xiàn)為典型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等要素的聚合,在探討這一對(duì)象的宜居性時(shí)需要充分融入對(duì)社會(huì)空間的關(guān)注與研究。國(guó)內(nèi)對(duì)于宜居城市的內(nèi)涵解讀及評(píng)價(jià)研究較多從宏觀層次出發(fā),更多地考慮城市經(jīng)濟(jì)發(fā)展、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層面的宜居性,對(duì)宜居性?xún)?nèi)涵服務(wù)的核心“人”多而頻繁接觸的城市社會(huì)空間關(guān)注較為薄弱。本文在對(duì)傳統(tǒng)宜居城市內(nèi)涵、評(píng)價(jià)體系等的研究前提下,引入社會(huì)空間理論,嘗試解讀出社會(huì)空間視角下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的要義。
1 宜居城市理論背景研究
1.1 宜居城市的起源發(fā)展及內(nèi)涵辨析
宜居城市這一概念伴隨著人類(lèi)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以及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和發(fā)展被逐步提出、完善,是居民對(duì)美好城市空間生活品質(zhì)的追求,也是城鎮(zhèn)化發(fā)展進(jìn)入高質(zhì)量階段的必然走向[1]。宜居城市概念萌芽于19世紀(jì)末,英國(guó)社會(huì)活動(dòng)家霍華德為解決工業(yè)化造成城市惡劣居住環(huán)境問(wèn)題所提出的“田園城市”構(gòu)想,其發(fā)展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gè)階段(表1)[2]。
宜居城市的內(nèi)涵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變化的概念,既表明人們對(duì)城市宜居性的認(rèn)識(shí)和訴求,也是城市發(fā)展所面臨的階段性問(wèn)題的映射。19世紀(jì)末霍華德等宜居城市探索先驅(qū)認(rèn)為社會(huì)生活豐富,生產(chǎn)生活關(guān)系融洽,環(huán)境衛(wèi)生健康的城市是宜居的;20世紀(jì)60年代“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被認(rèn)為是宜居城市的基本理念,“人本主義”理念指導(dǎo)下的宜居城市建設(shè)逐漸成為該領(lǐng)域的主流思潮;卡塞拉蒂(Casellati)從人本主義視角出發(fā)認(rèn)為,宜居城市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舒適自在的城市;薩爾扎諾(Salzano)以為宜居既是對(duì)當(dāng)下的人更是對(duì)后人的宜居,應(yīng)該關(guān)注到城市發(fā)展的歷史與未來(lái)的銜接;哈爾韋格(Hahlweg)認(rèn)為宜居是對(duì)城市所有居民的宜居,并且應(yīng)給予老人、小孩等弱勢(shì)群體更多的關(guān)注,比如讓他們可以安全、便利地享用公園綠地等城市公共資源;帕萊杰(Palej)則從強(qiáng)調(diào)保留和更新城市中的社會(huì)組織元素;埃文斯(Evans)主張工作地點(diǎn)和住處鄰近,能更多地接觸城市美好的自然環(huán)境,并不以犧牲城市環(huán)境換取高額的收入等。國(guó)內(nèi)學(xué)者任致遠(yuǎn)認(rèn)為宜居就是易居、逸居、康居、安居;李麗萍、郭寶華提出宜居城市是經(jīng)濟(jì)良好,社會(huì)和諧,文化深厚,居住舒適,景觀宜人,環(huán)境安全的城市;張文忠、尹衛(wèi)紅等以為環(huán)境安全,生態(tài)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適的城市是宜居的等等[3-5]。

表1 宜居城市理論與實(shí)踐發(fā)展歷程[1]
由此可見(jiàn),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對(duì)宜居城市內(nèi)涵有著不同的解讀,其核心視角均以“以人為本”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展開(kāi),發(fā)達(dá)國(guó)家學(xué)術(shù)界對(duì)宜居城市內(nèi)涵解讀的關(guān)注呈現(xiàn)出“微觀居住環(huán)境→人居環(huán)境體系→社會(huì)空間問(wèn)題”的脈絡(luò)發(fā)展特征。國(guó)內(nèi)對(duì)宜居城市的內(nèi)涵解讀則更多從城市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文化建設(shè)、生態(tài)宜人、社會(huì)和諧、居住舒適等全面而宏觀的指導(dǎo)層面出發(fā),且較為看重城市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建設(shè)發(fā)展而對(duì)社會(huì)空間層面的關(guān)注欠缺。
1.2 宜居城市理論基礎(chǔ)及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
國(guó)際社會(huì)對(duì)宜居城市的理論探索始于19世紀(jì)工業(yè)革命后期,在城市理想主義運(yùn)動(dòng)的推動(dòng)下,以霍華德“田園城市”為首追求干凈美觀、舒適便利的城市環(huán)境的新興城市建設(shè)模式逐漸發(fā)展起來(lái)。20世紀(jì)40年代,馬斯洛提出“人類(lèi)需求層次理論”進(jìn)一步豐富了宜居城市的理論研究基礎(chǔ),“以人為本”的發(fā)展理論逐漸成為宜居城市建設(shè)的理論核心。1954年,希臘建筑學(xué)家道薩迪亞斯提出“人類(lèi)集聚學(xué)”為宜居城市的理論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學(xué)者們開(kāi)始將城市作為一個(gè)整體從人類(lèi)的住區(qū)元素進(jìn)行廣義、系統(tǒng)的研究即“人居環(huán)境理論”的研究視角,1976年首屆人類(lèi)住區(qū)大會(huì)正式提出“人類(lèi)聚居”概念。1996年伊斯坦布爾人類(lèi)住區(qū)大會(huì)明確了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人類(lèi)住區(qū)研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理論指導(dǎo)意義,其后“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和“以人為本”思想一并成為宜居城市的核心理論基礎(chǔ)[6-8]。21世紀(jì)以來(lái),宜居城市更加關(guān)注城市空間品質(zhì)及城市的公平性,這在21世紀(jì)初大溫哥華地區(qū)、巴黎和倫敦的宜居城市建設(shè)中體現(xiàn)十分顯著。國(guó)內(nèi)對(duì)于宜居城市的理論研究開(kāi)始于20世紀(jì)末,1997年吳良鏞提出以建筑、園林、城市規(guī)劃相融合為核心建構(gòu)城市人居環(huán)境科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框架,成為我國(guó)宜居城市理論研究的開(kāi)端,其后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更多是對(duì)宜居城市的內(nèi)涵和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實(shí)例研究,在理論探索層面進(jìn)展相對(duì)遲緩。
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受宜居城市內(nèi)涵解讀、評(píng)價(jià)對(duì)象以及評(píng)價(jià)目標(biāo)等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一定差異性,通過(guò)對(duì)國(guó)內(nèi)外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的整理研究發(fā)現(xiàn)發(fā)達(dá)國(guó)家宜居城市標(biāo)準(zhǔn)層指導(dǎo)因子更為具體,在選取城市安全度、住房及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等因子之外更加注重對(duì)居民生活質(zhì)量、城市文化環(huán)境、社會(huì)文化氛圍、鄰里關(guān)系、社會(huì)空間生活及公平正義的考量[9],而國(guó)內(nèi)多數(shù)學(xué)者及研究機(jī)構(gòu)所提出的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則傾向于從宏觀層面全局化地考慮指導(dǎo)因子,較少關(guān)注反映社會(huì)空間生活及居民感知層面的宜居性因子。
1.3 理論背景研究小結(jié)
通過(guò)對(duì)宜居城市的起源、內(nèi)涵及理論基礎(chǔ)和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發(fā)展的研究可知,宜居城市的本質(zhì)是適宜人類(lèi)聚居的空間,其核心在于堅(jiān)持“以人為本”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對(duì)社會(huì)空間問(wèn)題的關(guān)注是新時(shí)期宜居城市內(nèi)涵解讀及評(píng)價(jià)發(fā)展的必然走向。率先開(kāi)始宜居城市理論研究及實(shí)踐的發(fā)達(dá)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表明宜居城市內(nèi)涵及理論解讀應(yīng)具有前瞻性,能預(yù)見(jiàn)城市即將面臨的主要問(wèn)題并做好壓力釋放的措施;城市建設(shè)需注重對(duì)“人”主觀需求的考量,在構(gòu)建城市生態(tài)健康物質(zhì)生活環(huán)境的基礎(chǔ)上,突出對(duì)城市社會(huì)空間問(wèn)題、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及空間資源公平性方面的考慮。
2 社會(huì)空間視角的引入
2.1 社會(huì)空間的定義
“社會(huì)空間”的概念誕生于19世紀(jì)末,由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涂爾干首次提出并應(yīng)用,其后來(lái)自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地理學(xué)、城市規(guī)劃學(xué)等研究領(lǐng)域的專(zhuān)家學(xué)者逐漸將其內(nèi)涵進(jìn)行不同層次的分析、解讀,時(shí)至今日由于不同學(xué)科間對(duì)“社會(huì)空間”釋義及內(nèi)涵解讀存在較大差異,以及“社會(huì)空間”一詞的濫用使得其內(nèi)涵定義出現(xiàn)極端多義化的現(xiàn)象。通過(guò)對(duì)社會(huì)空間相關(guān)內(nèi)涵闡釋文獻(xiàn)的研究,將社會(huì)空間一詞的主流釋義歸納總結(jié)如下。
2.1.1 社會(huì)空間是社會(huì)集群占有的地理區(qū)域
以首次提出“社會(huì)空間”概念的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涂爾干以及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芝加哥學(xué)派奠基人帕克、伯吉斯為代表的部分學(xué)者對(duì)社會(huì)空間所進(jìn)行的形態(tài)學(xué)、人類(lèi)生態(tài)學(xué)和文化因素影響層面的研究都前提性地認(rèn)為“社會(huì)空間”即人類(lèi)社群聚集的地理區(qū)域。
2.1.2 社會(huì)空間是個(gè)體對(duì)空間的抽象感知和個(gè)體在社會(huì)中的位置
20世紀(jì)50年代,法國(guó)地理學(xué)家索爾在涂爾干對(duì)于社會(huì)空間的認(rèn)識(shí)上將社會(huì)空間描述為若干個(gè)根據(jù)人們主觀空間感受而劃分的區(qū)域的拼貼,揭開(kāi)了用個(gè)人主觀視角感知社會(huì)空間的思潮序幕。其后有學(xué)者將社會(huì)空間的概念用以表示個(gè)體在社會(huì)中的具體坐標(biāo)位置,尤以20世紀(jì)80年代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布爾迪厄在表示個(gè)體在社會(huì)中具體位置所構(gòu)成的“場(chǎng)域”為甚。
2.1.3 社會(huì)空間是人類(lèi)實(shí)踐活動(dòng)生成的區(qū)域
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家、社會(huì)學(xué)家們是從實(shí)踐論角度探討社會(huì)空間的先行者,其中較為著名的學(xué)者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卡斯特爾、列斐伏爾、哈維和戈特迪納,他們的基本觀點(diǎn)認(rèn)為社會(huì)空間是社會(huì)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是人類(lèi)通過(guò)實(shí)踐活動(dòng)生產(chǎn)的區(qū)域[10]。
由此可見(jiàn),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社會(huì)空間”的認(rèn)知范圍非常廣,它囊括了社會(huì)整體存在形式、生活方式空間體現(xiàn)、空間意義及價(jià)值以及實(shí)體空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等。城市規(guī)劃學(xué)中的社會(huì)空間概念通常被闡述為不同階層的人們集體行為在空間中呈現(xiàn)的形態(tài)特征。我們可以這樣解讀:一切由人的認(rèn)知、生活和生產(chǎn)所占據(jù)的物質(zhì)及非物質(zhì)空間即為社會(huì)空間,城市其本身就是一類(lèi)典型的社會(huì)空間[11]。
2.2 社會(huì)空間理論的主要觀點(diǎn)
對(duì)社會(huì)空間的理論研究散見(jiàn)于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地理學(xué)以及城市規(guī)劃學(xué)等領(lǐng)域,其主流社會(huì)空間理論觀點(diǎn)如下:馬克思認(rèn)為社會(huì)空間是人類(lèi)社會(huì)中的空間它被人類(lèi)實(shí)踐活動(dòng)所創(chuàng)造和改變,城鎮(zhèn)化的過(guò)程即社會(huì)空間的生產(chǎn);列斐伏爾認(rèn)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自然空間因人類(lèi)實(shí)踐活動(dòng)的介入而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會(huì)空間的生產(chǎn),城市是一種典型的社會(huì)空間,不同的社會(huì)性質(zhì)造就了不同的空間生產(chǎn);戴維·哈維立足資本的原始積累揭示了空間在資本體系中的作用[12];城市規(guī)劃學(xué)者認(rèn)為城市空間的社會(huì)學(xué)價(jià)值十分重要,且城市社會(huì)多樣性、城市多元活力需要承載、發(fā)生的空間基礎(chǔ)[13]。
2.3 社會(huì)空間理論的適用價(jià)值
社會(huì)空間理論,顧名思義即研究“社會(huì)”與“空間”之間辯證統(tǒng)一關(guān)系的理論,這與現(xiàn)階段宜居城市建設(shè)所關(guān)注的城市物質(zhì)空間環(huán)境、社會(huì)關(guān)系等問(wèn)題一一對(duì)應(yīng)。在人類(lèi)社會(h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當(dāng)中“空間”愈漸成為重要的研究范疇和競(jìng)相爭(zhēng)奪的資源,城鎮(zhèn)化過(guò)程是空間生產(chǎn)最典型的表現(xiàn)形式,在資本和權(quán)力的誘因作用下這種城鎮(zhèn)化的空間生產(chǎn)大多以犧牲城市弱勢(shì)群體的存在感為甚,背離了宜居城市建設(shè)的初衷,故而我們亟需一種新的出離簡(jiǎn)單物質(zhì)空間規(guī)劃的思路和視角探討宜居城市建設(shè)。社會(huì)空間理論的空間生產(chǎn)其價(jià)值核心在于空間正義,這種正義不僅關(guān)乎城市空間資源的公平分布,同時(shí)也映射生存空間品質(zhì)的提升與優(yōu)化,這與建設(shè)宜居城市的主旨不謀而合。
3 社會(huì)空間視角與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的關(guān)聯(lián)性分析
3.1 社會(huì)空間理論的價(jià)值取向——“空間正義”
社會(huì)空間理論的當(dāng)代價(jià)值取向即追求“空間正義”,英國(guó)新韋伯主義“城市經(jīng)理人”研究者帕爾認(rèn)為空間是城市資源的一種,并帶有與生俱來(lái)的不公平性,城市社會(huì)學(xué)更多的是研究并嘗試削弱這種城市社會(huì)空間資源分配的失衡。縱觀國(guó)內(nèi)外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過(guò)程,都曾經(jīng)歷或正在經(jīng)歷城市經(jīng)濟(jì)資本裹挾城市發(fā)展建設(shè)方向的狀態(tài),以快速交通為導(dǎo)向的大尺度的新區(qū)建設(shè),顛覆性的城中村、老城區(qū)更新改造以及發(fā)達(dá)國(guó)家所經(jīng)歷的城市紳士化運(yùn)動(dòng)等等無(wú)一不體現(xiàn)出“空間資本化”的特征,大量新區(qū)以及推到式重建老城區(qū)的公共空間并未被城市中的所有居民公平享有,之前生活在此的居民因?yàn)楦赂脑旌蟮貎r(jià)地租的上漲無(wú)形中被城市所驅(qū)趕,城市生長(zhǎng)機(jī)理及社會(huì)空間結(jié)構(gòu)被改變,城市社會(huì)空間開(kāi)始出現(xiàn)階層區(qū)隔,這也成為影響當(dāng)前城市宜居性建設(shè)的顯著社會(huì)矛盾。故而,社會(huì)空間理論的價(jià)值取向“空間正義”可以為探索建設(shè)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新型宜居城市提供新的視角和途徑。
3.2 城市社會(huì)空間的研究核心——“空間互動(dòng)”
城市作為一類(lèi)典型的社會(huì)空間具有突出的社會(huì)性和屬人性,社會(huì)學(xué)研究的關(guān)鍵詞是“互動(dòng)”,城市規(guī)劃者的關(guān)注點(diǎn)多為“空間”,探索城市社會(huì)空間的核心要領(lǐng)在于研究“空間互動(dòng)”。城市空間的屬人性體現(xiàn)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人群,人們?cè)诔鞘锌臻g中的互動(dòng)即城市社會(huì)空間視角研究的內(nèi)容之一,而這種豐富多彩的社會(huì)空間互動(dòng)更多的發(fā)生于城市公共空間,楊貴慶曾以社會(huì)生活的“發(fā)生器”形容城市公共空間的重要作用,公共空間的“大眾化”和其催生的社會(huì)生活形態(tài)“多樣化”是這一發(fā)生器的價(jià)值所在。人類(lèi)社會(huì)發(fā)展變化的必然是城鎮(zhèn)化及現(xiàn)代化,在城市社會(huì)空間組分中表現(xiàn)為充分的公共空間。充滿(mǎn)公共空間的城市具有典型的現(xiàn)代性,充滿(mǎn)大眾化公共空間的城市必然是現(xiàn)代化宜居城市建設(shè)的先決條件。新時(shí)代背景下宜居城市建設(shè)理應(yīng)合理考慮城市社會(huì)空間的“空間互動(dòng)”,這是建設(shè)活力型宜居城市的關(guān)鍵所在。
3.3 社會(huì)空間優(yōu)化的重要屬性——“空間共享”
城市社會(huì)空間的優(yōu)化升級(jí)具象體現(xiàn)在城市生活空間品質(zhì)的提升,這同時(shí)也是新型宜居城市構(gòu)建的目標(biāo),通過(guò)“空間共享”的方式途徑合理促進(jìn)城市低效、閑置空間的共享化是優(yōu)化城市社會(huì)空間品質(zhì)的重要方法。社會(huì)空間視野下的“空間共享”是從源頭上擴(kuò)大社會(huì)活動(dòng)發(fā)生器的容積,閑置、低效空間的共享和再利用不僅提高了城市空間的利用率,同時(shí)為更多社會(huì)活動(dòng)的發(fā)生提供了場(chǎng)所支撐,促進(jìn)社會(huì)行為的出現(xiàn),繼而使空間產(chǎn)生新的社會(huì)意義。城市空間的科學(xué)共享即社會(huì)空間優(yōu)化的重要屬性,也促進(jìn)城市宜居性良性發(fā)展。
4 社會(huì)空間視角下的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要義
社會(huì)空間視角下的宜居城市評(píng)價(jià)要義主要圍繞空間正義性、空間互動(dòng)性和空間共享性三個(gè)層面展開(kāi)。
4.1 空間的正義性
4.1.1 資源配置公平化
社會(huì)空間視角下的空間正義首先體現(xiàn)在社會(huì)空間生產(chǎn)過(guò)程及空間資源配置、分布的公平化層面,有別于平均主義,此處提及的空間資源配置公平化是帶有主觀意識(shí)的向有益于社會(huì)弱勢(shì)群體的不平等傾斜[14]。在城市居住、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wù)、商業(yè)服務(wù)、綠地廣場(chǎng)等用地總量指標(biāo)滿(mǎn)足城市規(guī)劃建設(shè)標(biāo)準(zhǔn)的基礎(chǔ)上,合理進(jìn)行空間布局,確保空間資源良好的可達(dá)性及零輻射盲區(qū),加強(qiáng)空間資源舒適化及人群體驗(yàn)滿(mǎn)意度建設(shè),提升城市空間資源的布局宜居度。
4.1.2 公眾參與有效化
宜居城市的構(gòu)建理應(yīng)是政府、市場(chǎng)和社會(huì)三方力量共同作用的良性結(jié)果,公眾對(duì)城市建設(shè)、更新等活動(dòng)的參與是社會(huì)作用力的有效表征。過(guò)度以資本或權(quán)力為導(dǎo)向的空間生產(chǎn)及資源配置導(dǎo)致城市社會(huì)空間結(jié)構(gòu)被陡然改變,社會(huì)空間結(jié)構(gòu)上人群分異、區(qū)隔愈漸明顯,社會(huì)活動(dòng)多樣性降低,宜居度減弱[15]。這也暴露出社會(huì)力量介入不足的問(wèn)題,故而在宜居城市建設(shè)過(guò)程中要?jiǎng)?chuàng)造公眾參與有關(guān)社會(huì)空間生產(chǎn)配置的機(jī)會(huì),減小弱勢(shì)群體表達(dá)意見(jiàn)的阻力。公眾參與有效化的實(shí)現(xiàn)在極大程度上可以讓社會(huì)群體有權(quán)力對(duì)資本和政府的強(qiáng)制介入說(shuō)不,這是公民空間權(quán)益正義性的得當(dāng)表現(xiàn),也使得城市在政府、市場(chǎng)和社會(huì)三重要素的制衡下朝著宜居的方向發(fā)展。
4.2 空間的互動(dòng)性
4.2.1 空間分布混合化
城市空間的互動(dòng)是城市社會(huì)空間多元化的基礎(chǔ),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仿生學(xué)角度出發(fā)社會(huì)空間越多元即多樣性越突出,城市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越強(qiáng),宜居度越好。而空間的互動(dòng)又可以理解為不同社會(huì)空間之間的互動(dòng)和社會(huì)空間內(nèi)部因子的互動(dòng),城市功能空間分布混合化屬于典型的不同類(lèi)型空間間的互動(dòng)。由于不同功能空間性質(zhì)差異,空間和空間的混合布局能增加不同空間的接觸面,異質(zhì)空間接觸面往往就是互動(dòng)的發(fā)生場(chǎng)所,故而城市空間布局混合化即一定程度上理解為用地布局混合化是增加社會(huì)空間互動(dòng)的有效措施之一。
4.2.2 公共空間大眾化
社會(huì)空間內(nèi)部因子的互動(dòng)是空間互動(dòng)的另一種空間表達(dá),城市中能大量發(fā)生人與人互動(dòng)的具體空間場(chǎng)所莫過(guò)于城市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城市精神的承載物,也是社會(huì)生活的發(fā)生器,其具有重大的社會(huì)學(xué)意義,社會(huì)空間的大眾化將進(jìn)入其中的成本和門(mén)檻降到最低,能有效促進(jìn)不同社會(huì)階層的人群進(jìn)入其中,多元生活背景人群的碰撞與互動(dòng)可以活化城市空間。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城市對(duì)弱勢(shì)群體的空間剝奪和邊緣化,能有效緩解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空間生產(chǎn)被資本和權(quán)力裹挾進(jìn)行而造成的社會(huì)矛盾,盡量拉平既有空間資源配置不公的差距,提升城市宜居度。
4.3 空間的共享性
4.3.1 低效空間共享化
城市生活的活躍度需要其發(fā)生器城市空間的基礎(chǔ)支持,努力營(yíng)造充足、多元的城市社會(huì)交往空間能有效刺激社會(huì)活動(dòng)的發(fā)生,而在既有城市交往空間相對(duì)缺乏的現(xiàn)狀下合理促進(jìn)低效空間共享能有效緩解這一問(wèn)題。“小街坊,密路網(wǎng)”的實(shí)踐就是低效空間向共享空間轉(zhuǎn)化的典范,此舉不僅在城市交通微循環(huán)層次上提升了地塊的通達(dá)性,其深刻的社會(huì)學(xué)意義在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大社會(huì)活動(dòng)發(fā)生器的容量,構(gòu)建多尺度、開(kāi)放和諧的生活街區(qū),增加人與人互動(dòng)交流的機(jī)會(huì),提高城市空間的品質(zhì)和宜居度。
4.3.2 閑置空間共享化
城市空間中閑置空間的出現(xiàn)降低了空間資源的利用效率,對(duì)閑置空間的共享化處理在考慮到使用效率的前提下,應(yīng)該強(qiáng)化閑置空間對(duì)城市空間活力的潛在貢獻(xiàn)價(jià)值。閑置空間的合理貢獻(xiàn)是緩和空間緊張、局促及刺激社會(huì)空間活力再生的有效措施。例如城市高架橋下方灰色空間的改造利用,一些城市的高架下方會(huì)進(jìn)行專(zhuān)門(mén)的綠化改善,增設(shè)健身器材,形成散布城市各段的口袋公園,從而吸引附近的常住居民利用這些原本的灰色閑置空間從事健身、休憩等活動(dòng)。合理的閑置空間共享不僅緩解了局部地區(qū)公共活動(dòng)空間緊張的問(wèn)題,也能有效生產(chǎn)社會(huì)活動(dòng)空間,激發(fā)城市空間活力,提升城市的社會(huì)宜居度,因而城市空間的共享特質(zhì)是打造新型宜居城市的必要社會(huì)屬性。
5 結(jié)束語(yǔ)
宜居城市是一個(gè)發(fā)展變化的概念,不同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其內(nèi)涵解讀側(cè)重點(diǎn)各異,當(dāng)前我國(guó)城鎮(zhèn)化進(jìn)入全面提升人居環(huán)境品質(zhì)的關(guān)鍵時(shí)期,作為城市階段性問(wèn)題映射的宜居城市內(nèi)涵在延續(xù)“人本主義”“可持續(xù)發(fā)展”思想的前提下應(yīng)加強(qiáng)對(duì)城市社會(huì)空間層面問(wèn)題的解讀。社會(huì)空間空間視角下的宜居城市應(yīng)該是在滿(mǎn)足傳統(tǒng)宜居城市內(nèi)涵要求的基礎(chǔ)上,具備空間正義性、空間互動(dòng)性以及空間共享性的新型宜居城市。當(dāng)前,社會(huì)不公是諸多城市現(xiàn)存的突出問(wèn)題,從社會(huì)空間視角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城市社會(huì)空間的互動(dòng)和建構(gòu),有益于社會(huì)各階層異質(zhì)性在城市空間上的融合,提升城市宜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