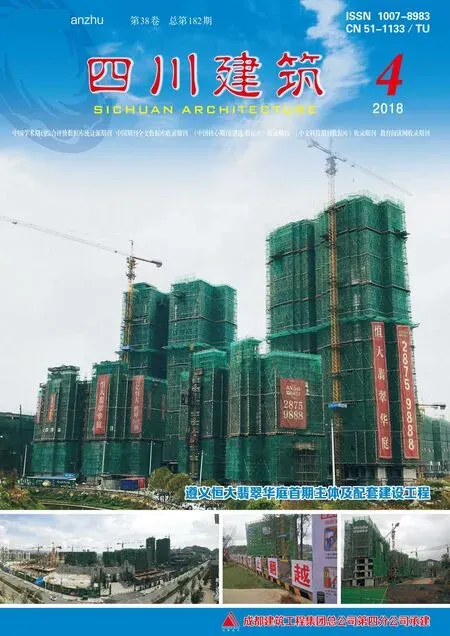大型鋼桁架屋蓋卸載過程應力監測與分析
李 鵬,張 曄,鄧星河,鄭小川,張 麒
(1.中建一局集團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北京100102; 2.重慶大學土木工程學院,重慶400030)
大型鋼結構由于自重大,往往無法整體一次性吊裝到位,多借助臨時支撐進行拼裝,待結構整體成形后再逐步卸除臨時支撐上的荷載并將其拆除。而在臨時支撐的卸載過程中,結構和臨時支撐的受力會逐漸轉移、內力發生重分布[1-2],現有工程實例表明,卸載過程受力狀況將直接影響到結構的初始內力、變形,使用階段的性能甚至使用壽命[3]。因此,借助當前先進的監測手段,掌握卸載過程中結構的受力變化已成為保障結構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國內針對不同類型屋蓋結構的卸載過程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曾志斌對國家體育場(鳥巢)支撐胎架的卸載過程進行了應力監測,實測值較好地反映了鋼結構在體系轉換過程中整體受力的變化[4];張亮泉對連續鋼梁和網殼結構組成的復雜大跨結構進行了應力監測,連續鋼梁和網殼結構的結合使結構受力不均勻,應力監測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陳志華針對天津市圖書館在施工過程中存在體系轉換的問題,進行了應力監測,監測結果為現場施工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6]。
但在實際工程中,大型鋼結構為滿足建筑或功能的不同需求,采用的結構形式往往不同,導致卸載施工過程中結構內力變化規律也不盡相同。因此本文以某雙向交叉平面鋼桁架結構為研究對象,在其臨時支撐卸載過程中進行結構桿件的受力監測,并結合有限元分析,研究卸載過程中桿件內力變化規律,為同類結構的卸載施工提供技術支持。
1 工程概況
某大型體育場作為以籃球比賽、訓練為主的多功能體育、文化活動中心場所,總建筑面積27.9×104m2。為滿足賽事要求及多種使用功能需要,建筑采用了大跨度屋蓋。主體平面結構呈橢圓形,采用鋼筋混泥土框架結構體系。固定屋蓋平面形狀為圓角矩形(接近橢圓形),整體采用雙向交叉平面鋼桁架結構,短邊跨度為109.2 m,有四榀桁架貫穿其中,長邊跨度為126 m,有六榀桁架貫穿其中,四角部位為肋環形布置,共設置8處臨時支撐,屋蓋整體支承于下部型鋼混凝土柱頂,桁架結構高度(上、下弦桿軸線間距離)5.77~8.717 m。其中桁架上弦桿采用方鋼管,其他桿件均采用H型鋼,節點采用相貫焊接節點(圖1)。

圖1 施工中的鋼桁架屋蓋結構
2 有限元模型分析及測點布設
2.1 有限元理論計算
采用Midas gen軟件,根據鋼屋蓋的施工圖紙并結合現場實際情況建立有限元模型。由于結構構造復雜,為減少計算量,所有構件均采用梁單元模擬。桿件截面按施工圖紙取值,鋼材彈性模量取為2.06×105MPa,泊松比取為0.3。卸載階段采用減少支撐反力的方法來模擬,且所有支座處均采用節點彈性連接。最終有限元計算見圖2。

(a)上弦桿

(b)腹桿

(c)下弦桿圖2 卸載后鋼屋蓋的應力云(單位:MPa)
2.2 測點布置
為保證選取的測點能反映結構的最不利狀況,在選取測點時綜合考慮以下因素:(1)卸載完成后應力較大和位移較大的桿件。(2)卸載前后應力和應變變化較大的桿件。
從圖2可以看出,上弦桿、下弦桿均在中央區域應力最大,且往四周逐漸減小,因此在布置上弦桿、下弦桿的測點時均以中央區域控制為主,四周控制為輔。且腹桿的應力也較大,承擔了一定的傳力作用,因此在腹桿應力最大處也布設部分測點。
共布置30個測點,均采用振弦式應變計布設于桿件表面(圖3)。其中上弦桿布置8個測點,腹桿布置8個測點,下弦桿布置14個測點,且每一個測點距最近的桿件節點均為2 m。

(a)上弦桿

(b)腹桿

(c)下弦桿圖3 測點布設
3 現場監測方案
本次支撐胎架的卸載過程共分4次完成,均以位移控制為主,力的卸載控制為輔。其中前3次卸載,每次控制下降40 mm,最后一次卸載下降5 mm,共下降125 mm。為保證實測數據的精確性,每次卸載后待數據穩定后(即應變在一定時長內保持不變)方才開始下一次卸載,并在全部卸載完成后的1 h、24 h、48 h、30 d分別對測點進行一次獨立監測,作為后續施工階段對應力監測影響變化的對比依據。通過分析應變變化規律,從而評估結構的安全狀態。
同時考慮到溫度變化會影響傳感器的自身量值,因此對每次的實測數據均采用式(1)進行修正,從而消除其自身量值產生的影響,再根據材料本構方程將應變轉化為應力。
ε= (ε1-ε0) + (T1-T0) (Fv-Fs)
(1)
式中:ε1為當前儀器測量應變值,單位為με;ε0為初始應變值;T1為當前傳感器測試溫度;T0為初始溫度;Fv=12.2為鋼弦的線膨脹系數(με/℃);Fs=12為鋼結構設計規范中規定鋼結構的線膨脹系數(με/℃)。
4 監測結果及分析
4.1 上弦桿應力分析
最終不同工況下各上弦桿的應力實測值如圖4所示。

圖4 各工況上弦桿應力變化
從圖4可以看出:(1)前3次卸載中上弦桿應力增長較快,但在第三次卸載完成后,應力逐漸趨于平緩,說明此時結構已基本完成應力重分布;(2)第5次、6次卸載中部分測點應力出現明顯波動,但波動幅值較小。主要是因為實際監測中,第7次卸載時的溫度高于第6次,溫度的變化影響了桿件的受力,因此部分桿件的應力有所增加;(3)第8次卸載時的應力較第7次有所增加,其原因是第8次卸載晚于第7次卸載一個月,在這期間屋蓋四周安裝了托架,導致下弦桿增加了附加荷載。
考慮到U7、U8號測點存在異常,因此單獨將其實測值與理論值進行對比分析(圖5)。

圖5 U7、U8測點實測應力值與理論值對比
從圖5可以看出,前三次卸載中,U7、U8號測點的應力實測值均大于理論值,其主要是因為有限元分析中每次卸載所采用的模型均是理想模型,即不考慮殘余應力等因素的影響,而實際結構在卸載后會存在殘余應力,容易引起局部應力集中,且隨著卸載量的增加,累積殘余應力持續增大,應力集中現象也愈發明顯,從而導致部分測點實測值與理論值之間的偏差也逐漸增大。雖然存在一定偏差,但實測值始終小于卸載完成后的最大理論值(即工況4),表明結構安全仍在可控范圍內。
4.2 腹桿局部應力分析
不同工況下W1、W2測點處的應力值如圖6所示。其中W1為腹桿腹板處的測點,W2為腹桿翼緣處的測點。

圖6 各工況下腹桿W1、W2測點應力對比
從圖6可以看出,不同工況下同一桿件中不同位置的應力始終相差20 MPa左右,表明此時腹桿主要受壓或受拉,同時承受部分彎矩。而H型鋼中腹板主要承受剪力作用,翼緣主要承受彎矩作用,因此W1(腹板處測點)處的應力普遍大于W2(翼緣處測點),符合理論設計要求。
4.3 下弦桿應力分析
不同工況下下弦桿應力值如圖7所示。從圖7可以看出,前3次卸載中,D9~D14號測點的應力增長明顯較D1~D8更快,主要是因為D1~D8號測點位于屋蓋最外側,自身承擔的荷載較小。而后5次卸載中,所有測點應力逐漸趨于平穩,雖然D1~D8號測點應力出現小幅波動,但始終小于25 MPa,在可控范圍內,相反,D9~D14號測點在第一次卸載時應力值已接近25 MPa,表明桿件的卸載順序以及卸載量的大小會對結構的受力產生一定的影響。

(a)D1~D8測點

(b)D9~D14測點圖7 各工況下弦桿應力曲線
5 結束語
本文采用有限元分析指導現場測點布設,對某大型鋼桁梁屋蓋卸載過程中的桿件進行了應力應變監測,驗證了卸載過程中桿件的安全性,并對桿件內力重分配規律進行了分析,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1)前三次卸載完成后,鋼屋蓋已基本承擔了自身荷載,結構逐漸趨于穩定,雖然附加結構、溫度變化以及殘余應力的存在仍會引起整體結構、部分桿件的應力變化,但并不會影響結構安全。
(2)腹桿的偏心受力和受彎作用會使斜腹桿腹板和翼緣板的受力產生差異,因此在同類型結構卸載過程的腹桿監測中,應以腹板監測為主,翼緣監測為輔。
(3)下弦桿最外側受力普遍較小,卸載過程中應力變化規律并不明顯,因此在同類型支架卸載過程中可減少最外側的測點布設,從而達到節約經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