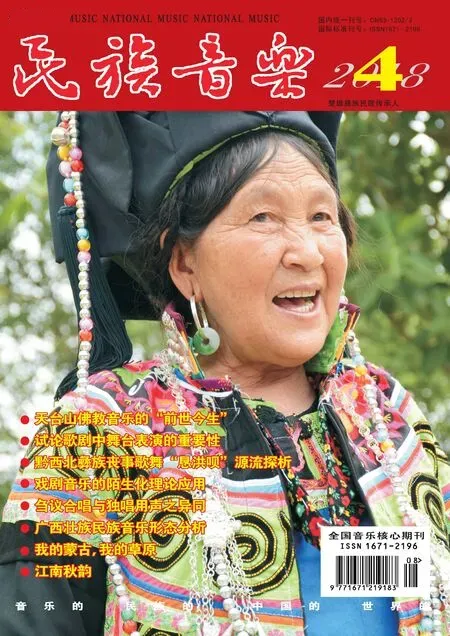多元文化背景下古箏音樂的文化釋義
——以《草原英雄小姐妹》為例
■張 華(重慶師范大學)
文化是推動一個國家發展的精神動力,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音樂作為一種最接近人的內心世界抽象性的“心聲”,或許最能體現精神性的表達,它既表現出人們自我審美的行為方式,又反映出人們的觀念信仰和審美情趣。美國人類學家索爾曾說:“一個特定的人群,在長期生活的地域內,一定會創造出一種適合環境的文化景觀和標志性符號”。古箏自秦朝流傳至今,其演奏技法由單一到多樣、由易到難,演奏技法的多元性與創新性使得古箏在近現代更加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旋律多樣、內涵豐富、文化意義深遠。由此,古箏無疑是中華民族人民智慧與精神追求的物化表達。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在特定生態背景下產生的作品,是作曲家張燕和劉起超在觀看同名電影后產生創作沖動,歷時三月而成。音樂故事是圍繞內蒙古草原人民熟知的龍梅和玉榮展開,為保護集體的羊群,不懼艱險,與暴風雪抗爭20余小時,最終成功救下羊群。她們的事跡被譜成箏曲,以獨特的藝術形式,弘揚“草原英雄小姐妹”精神。
■音樂本體分析
每一首作品的產生,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草原英雄小姐妹》作為一種特定的人文符號,是自然時間與社會記憶有機結合的產物,以“年”為時間向度,以民眾生產生活的進程為空間緯度,構成了草原民眾的整體場域。而理解一首作品,對其音樂結構的認識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美國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所提出的“概念-行為-音聲”三元分析模式,音本體是探究作品的藝術之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全曲的曲式結構共分為七個部分:
(一)引子。自由式的散板,由高音區的四度和音的小撮引入,雙手交替流暢的技法運用再加以清晰明亮的琶音,瞬間將人帶入“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草原之中。流暢的刮奏加上馬頭琴的模擬音色,展現出草原人民熱愛生活、和諧美麗的人文景觀。
(二)第一主題。音樂的主題樂思采用《草原英雄小姐妹》動畫片中的主題音樂,四二拍的節奏加之左右手演奏創造出的復調氛圍,使得樂段活潑而又富有動感,將人物形象淋漓盡致地首次呈現。之后進行變奏,速度上的明顯加快、聲部織體的加厚,下行和上行的旋律進行如同珠落玉盤,簡潔優美,與主題之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內部對比,使得樂曲既保留主題樂思而又不會審美疲勞,表現出小姐妹在草原相互嬉戲打鬧、放逐羊群的快樂場面。
(三)第二主題。右手連續的搖指,含蓄而不熱烈,猶如歌唱般的蒙古調,四二拍到四四拍的節奏轉換,使得旋律拉寬,樂型猶如波浪,它柔和動人、輕盈可愛,和聲的功能體系起著鮮明作用,畫面一片祥和。
(四)暴風雪主題。此樂段為全曲的高潮段落,無論是情緒的渲染還是演奏技法的使用,都將曲子推向一個新的層次。首先,7弦與12弦在演奏過程中移碼,要求一定的演奏功力,才能完美地將其不和諧音程的設計表現出來。音區的驟變、增八度與減七度的出現、雙手在琴碼左右側激烈的反響刮奏,猶如暴風雪肆虐一般。之后的快四點彈奏、掃搖、雙抹等技法的綜合運用,展現出小姐妹與暴風雪激烈抗爭的景象。隨著琴碼的移位、五聲音階的恢復,暴風雪逐漸變小變弱,馬蹄聲趕來,小姐妹得救了。此樂段是典型的復調手法,兩個主題并置。右手旋律象征著“正義”,緊密連續的十六分音符,搭配激昂的搖指,塑造了一個鋼鐵英雄的形象;左手則是“邪惡”的代表,在傳統演奏技法的基調上,加上高八度演奏以及非五聲調式的音階進行,刻畫了一個邪惡的形象。兩個主題相互交織,最終正義戰勝邪惡,交響性與戲劇性并存,主題刻畫的極為飽滿與生動。
(五)第二主題再現。描述的是小姐妹在進行了一系列頑劣抗爭后的喜悅以及內心訴說之后回歸的平靜。右手搖指加以左手琶音、和弦的推進,使得旋律明亮寬廣。四四拍到二二拍的節奏轉換,讓音樂更加充滿激情,情緒更為飽滿,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六)第一主題再現。此樂曲再現部采用的是倒敘的創作手法,第一主題再現置于第二主題之后,強調主題材料,歡快的節奏和跳躍的旋律展現出小姐妹重回活潑的場景,同時也將她們的精神加以歌頌和贊美。
(七)尾聲。和弦的快四點進行,將全曲最后的熱情點燃,結束在強烈的掃搖中,對整首樂曲的情緒給予肯定和升華。
■風格特性
對于任一首音樂作品的理解,都不只是對音樂和聲曲式的分析,更為關鍵的是要挖掘隱喻其后的象征性闡釋。而藝術人類學對藝術作品的解讀也不僅僅是對藝術作品本身的關注,更是通過對藝術作品形式與文化的整體分析。
(一)作曲技法“西為中用”
《草原英雄小姐妹》中所采用的復調式織體,是以對比、襯托、減插、模仿、移位等手法構成的織體結構,旋律之間相互補充,結構并置,無主次之分。在當時創作的所有箏曲當中,作曲家張燕在《草原英雄小姐妹》對復調式織體的使用具有開創式的意義。除此之外,奏鳴曲式與回旋曲式的曲式布局也在作品中有所運用,這正是突破傳統作曲局限,奏出時代新聲的最佳說明。
(二)少數民族色彩濃郁
音樂是一個族群歷史文化的記錄,正如彭兆榮先生指出的那樣:如果一個地方生活著幾個民族,其音樂文化的類型結構必定是:每個民族文化為“共體”承擔著一個支點,共同建構“共體”。《草原英雄小姐妹》是草原人民的真實事跡改編而成的古箏作品,其中所體現出來的蒙古族音樂元素,不僅提高了音樂辨識度,同時提高了聽眾的審美體驗。作品在音樂風格的表現上,以蒙古民歌為主軸,將蒙古族的馬頭琴、長調、短調等體裁與古箏的特色指法相融合,使得樂曲具有濃郁的地域特征,同時又增添了音樂表現力。
(三)戲劇性的情感體驗
一部好的音樂作品,不僅給人帶來聽覺上的享受,同時還會給人帶來情緒上的共鳴,從而引發更為深層次的思考。一般而言,作品通常從“被感覺--想象--情感體驗”三個階段展開聽眾的情感認知,《草原英雄小姐妹》通過前兩個主題的“被感覺”階段,逐步推向暴風雪主題的“想象”,再現的主題部分將聽眾帶入“情感體驗”。創新的演奏技法和作曲布局給人以戲劇性的情感認同,并在欣賞音樂的同時升華主題,滿足人們的聽覺需求與情感需求。
■社會功用
文化人類學認為,每種人類文化都是一項獨特的產物,是由自然環境、文化接觸以及其他各種因素所制約。《草原英雄小姐妹》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節點產生并發展至今,必定有其特有的文化功能屬性。
(一)藝術欣賞功能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美學》中寫道:“人類本性中就有著普遍愛美的要求。”生活就是美,音樂就是美。《草原英雄小姐妹》,來源與生活,訴說著生活中最真實的故事,體現著生活中最為質樸的美。古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編創與演奏,無論從作曲技術層面還是演奏技巧方面,都帶有表演性的欣賞功能,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審美價值。高標準的演奏技法與演奏者完美結合,濃郁的民族風格展露無疑,曲調與內蒙民歌相交相融,將真實故事用古箏的形式呈現給觀眾,將聽覺與視覺、表演形式與內容相統一,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功能。
(二)娛樂功能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音樂在本質上是令人愉快的,在和諧的樂調和節奏之中,存在著一種與人心靈的契合或血緣關系。”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高強度與快節奏的生活與工作給人們帶來了無形的壓力。古箏因其悠揚的曲調與五聲音階的和聲進行,給人以和諧舒適的感覺。《草原英雄小姐妹》曲調動人、段落銜接錯落有序,人們在生活之余,可以通過聽箏的方式緩解壓力,起到娛樂與舒心的功能。
(三)教育功能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創作由真實故事為源頭,記錄著年僅十幾歲的兩個小姐妹用小小身軀抗爭暴風雪保護羊群的行動,展現出來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書寫了民族團結進步和共同繁榮發展的奉獻精神與犧牲精神。為此,古箏曲目《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每次演奏,都是在傳遞著民族精神,在“寓教于樂”中教化眾人。箏曲在傳播與流傳的過程中,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正因為它背后隱藏的深厚文化底蘊,才是其深受群眾喜愛重要因素。由此說來,《草原英雄小姐妹》在教育人民、團結集體等方面,也起著積極的教育功能。
(四)民族認同功能
文化的認同是民族認同最基礎的要求,是族群情感的附著體,是族群內心的情感依附。《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內蒙民族文化的體現與延續,有著本民族特定的歷史記憶,是了解自我歷史的重要依據。“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方人養育一方文化。”差異性的社會結構構成了多元文化的基礎,同時也展先出有別于“他族”的鮮明文化特色,體現出草原人民文化的精髓與民族思維的外顯。《草原英雄小姐妹》作為一種聲音的符號,構成民族共同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結構,有著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向心凝聚力,對維系族群社會和諧安定、人民生活幸福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
(五)文化傳承功能
文化實施著傳遞社會經驗而維持社會連續性的重要功能。《草原英雄小姐妹》形象地保存了草原人民的精神文化風貌和文化現象,傳承了豐富的民間文化,具有較高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草原英雄小姐妹》植根于民間文化,傳承著民間精神,受到民族與當地文化的共同浸染與滋潤,傳承著草原民眾本土化的社會風情與審美意味。古箏作為演出的載體,在表演形式上與其情感體驗、文化內涵相結合,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傳播著歷史、傳遞著精神、傳承著文化。
■文化內涵
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形態和載體,音樂蘊含著一個族群情感之旅的記錄,是作為社會思想和時代思潮的一種體現,它不僅折射出人們思想觀念的變遷和行為方式,更是大眾思想價值的重要反映。長期以來,音樂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
自十八大召開以來,“中國夢”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民族的未來,國家的強大,都取決于我們今天的行動和認識,古老而神奇的內蒙古養育了不畏艱險的草原小姐妹,多元、立體的文化生態特征和萬物有靈的開放思想體系,造就了她們特殊的精神追求和藝術個性,從而塑造了有別于他者的社會心理特征和民族性格。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五周年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最基礎、最廣泛、最深厚的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在多元文化交織的背景下,我們對任一音樂事象的認識,絕不能是單一、片面的,要學會站在不同的視角解剖問題的本質。正如我們認識《草原英雄小姐妹》一致,不能拘泥于音聲本身,“音”源于“聲”,又高于“聲”。作為一種文化經驗,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聲音隱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不同文化中人們情感體驗和行為方式的內涵也是不同的。所以,音樂作為一種“藝術”的符號系統,它不僅僅是形式的呈現,更是一個過程的體驗和與心靈交融的過程。
■結 語
在全球化風暴的席卷下,多元文化的發展讓古箏音樂乃至音樂學科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力。與此同時,本土音樂及民族音樂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多元文化支撐著整個民族的精神,各地都在積極地用音樂的方式傳承屬于自己一方熱土的文化積淀。《草原英雄小姐妹》可謂是草原大地上的一大文化明信片,音樂與文化相互交融、滲透,動人箏樂傳遞大愛無聲的奉獻精神、英雄精神、團結精神和愛國情懷。音樂作為載體,傳承著草原精神,傳頌著英雄形象,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與現實意義。作為音樂學科的后學,更應發揮自己的專業能力,提升自身素質,即理論學識、鑒別能力、技巧能力等多方面能力,并借著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契機,以全新的姿態投入到社會需求的發展之中,為古箏音樂的發展贏得更多的機緣,為本土音樂的發展與壯大乃至民族文化的弘揚與傳承爭取更為重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