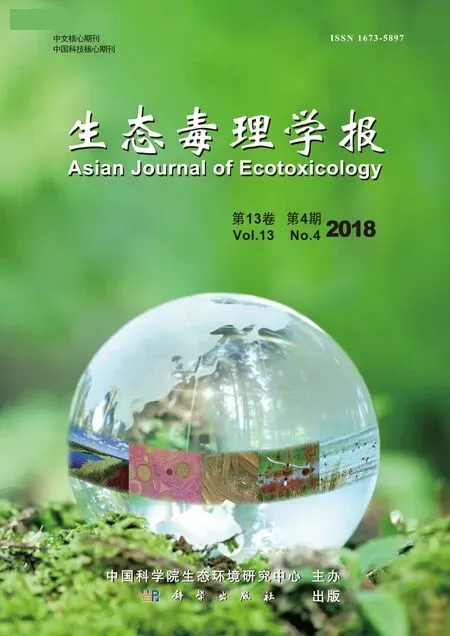洱海冬季水鳥群落結構與水位變化的潛在關系
張淑霞,王榮興,沈建新,馬暢,肖文
大理大學東喜瑪拉雅研究院,大理 671003
水鳥是位于濕地生態系統食物鏈頂端的生物類群,其對濕地的利用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水深、水位波動、植被、鹽分、食物、濕地面積大小、濕地連通性等因素[1]。在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水深是影響水鳥棲息地利用最重要的因素[2],而濕地的水位波動會導致水深發生變化,因此這2個影響因素密切關聯。
每種水鳥受限于自身的喙、頸和跗蹠的長度和覓食行為,僅能利用一定程度水深的濕地[1]。早期關于水深與水鳥多樣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各生態功能群可以利用的水位范圍[3],例如小型涉禽(small shorebirds)一般在水深不超過5 cm的棲息地覓食,鉆水鴨(dabbling ducks)和大型涉禽(larger waders)在水深最多30 cm的淺水區覓食,而潛水覓食的水鳥則需要在最小水深超過25 cm的深水區覓食[1]。近代關于水位波動對水鳥群落多樣性影響的相關研究則從可利用的覓食棲息地變化上入手,通過研究水位波動帶來的水鳥覓食地暴露面積或植被的變化,揭示水位波動對水鳥多樣性的影響機制[4-7]。其中對秋冬季遷徙鳥類的研究從2個角度證明水位波動對水鳥產生的影響,一方面冬季水位下降使濕地覓食地暴露,從而水鳥多樣性增加[4-7];另一方面,水位上升,限制了部分水鳥類群對濕地的利用,使遷徙的秋季水鳥多樣性下降[8]。
已開展的水深或水位波動對水鳥多樣性的影響研究,研究地點往往集中在沼澤灘地較發達的內陸淡水湖泊、沿海泄湖濕地或河流泛洪濕地[4-9]。對于灘地發育不顯著的濕地,水位波動帶來的水鳥多樣性影響研究關注較少。然而,基于地方特異性的研究是進行濕地管理具體指導所必需的[1]。
云貴高原地區湖泊多水深岸陡,灘地發育遠不如我國東部平原湖區的湖泊[10],水深岸陡這一外部形態特征決定云貴高原湖泊水位波動帶來的鳥類覓食棲息地變化將不如灘地發達的濕地顯著,水位波動是否仍然能夠顯著影響水鳥群落的多樣性,這一問題的回答將為從水鳥棲息地保護角度進行云貴高原湖泊水位管理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研究區域概況
洱海(25°36'~25°58'N, 100°06'~100°18'E)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內,是一個典型的內陸斷陷淡水湖泊,水位1 973.66 m時,長42.58 km,最大寬8.0 km,湖面面積249.0 km2,最大水深20.7 m,

圖1 洱海北部湖灣水鳥觀察點分布Fig. 1 Survey sites in the northern Lake Erhai
平均水深10.17 m[10]。洱海湖濱帶全長128 km,其中西部48 km,南部8 km,東部51 km,北部11 km[11]。湖區屬中亞熱帶高原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5.0 ℃,1月平均氣溫8.5 ℃,極端最低氣溫4.2 ℃,7月平均氣溫20.1 ℃,極端最高氣溫34.0 ℃。多年平均日照時數2 472 h,無霜期305 d,年均降水量1 056.6 mm,最大年降水量1 456.5 mm,最小年降水量650.2 mm,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85%~96%[10]。近50年來,隨著洱海流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入洱海的氮、磷負荷持續增加,洱海水質持續下降,從而導致洱海水生態系統發生退化,沉水植物多樣性下降且群落結構趨于簡單化[12]。為恢復水生植被,大理市洱海保護管理局在2017年降低了洱海運行水位。
1.2 調查方法1.2.1 調查年度的確定
由于早期2014年已經對洱海冬季水鳥進行過監測,因此使用2014年的數據作為水位下降前的水鳥多樣性對比數據。同時向大理市洱海保護管理局分別收集2014年和2017年全年的水位數據。在2017年,由于環湖截污工程的大規模實施,道路交通條件較差,致使調查效率較低,因此僅對洱海北部湖灣進行了調查,調查的5個地點與2014年冬季調查地點和視野范圍完全重合(圖1)。
1.2.2 水鳥調查方法
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和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每隔10天左右調查一次(表1),在洱海北部5個調查地點完成水鳥調查。其中2014年冬季共調查10次,2017年冬季共調查8次。每次水鳥調查至少由2名調查人員完成,在每個觀察點,搜索左右兩邊沿岸帶至湖中心視野范圍內的所有水鳥,配合使用施華洛世奇單筒25~60倍變焦望遠鏡(Swarovski,ATX25-60×85,產地奧地利)和10×42雙筒望遠鏡(Olympus,EXWP I,產地日本),采用“Look-See”方法[13]對視野內的水鳥進行物種鑒定和分種計數。調查日均為晴天,且風浪小,調查僅在日照條件良好的時間段內進行(09:00—17:00時)。
1.2.3 數據分析
根據Taft等[3]的覓食棲息地功能集團劃分依據,將觀察到的水鳥按照涉禽(waders)、鉆水鴨(dabbling ducks)和潛水類(diving waterbirds)三大類群進行分類。在洱海北部觀察到的紅嘴鷗Larus ridibundus和[普通]鸕鶿Phalacrocorax carbo多處于飛翔或棲息的狀態,并沒有嚴格處于覓食狀態,因此未將這2個物種包括在本研究的數據分析中。將歷次調查的水鳥數據進行分年度匯總比較,并按照3個功能集團分類進行水位下降前后物種豐富度和物種多度的比較。
2 結果(Results)
2.1 水位變化
2014年和2017年洱海水位呈現出相似的年內變化規律,均為夏季較低,而秋季最高,冬、春季逐漸下降的規律(圖2)。2017年洱海運行水位明顯低于2014年運行水位,2014年洱海月水位平均值為1 973.82 m,而2017年的為1 973.47 m;與2014年相比,2017年月水位平均值下降0.35 m。

圖2 洱海2014年和2017年逐月水位對比Fig. 2 The comparison of water level in Lake Erhai between 2014 and 2017 by month

2014年冬季The winter of 20142017年冬季The winter of 20172014-11-082017-11-082014-11-152017-11-192014-11-222017-12-062014-11-292017-12-212014-12-062017-12-302014-12-142018-01-092014-12-272018-01-192015-01-032018-01-242015-01-202015-01-26

表2 2014年和2017年冬季在洱海北部觀察到的水鳥物種和個體數量Table 2 The species and its individual number observed in the northern Lake Erhai in winter of 2014 and 2017
注:所屬集團一列中的字母含義分別為Di代表潛水類水鳥,Da代表鉆水鴨類,Wa代表涉禽;物種名稱及排列順序依據《中國鳥類種和亞種分類名錄大全》[14]。
Note: Di stands for diving waterbirds, Da for dabbling ducks, Wa for waders; the taxonomy refers to A Complete Checklist of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the Chinese Birds[14].

表3 2014、2017年冬季洱海北部不同功能集團水鳥的物種數和個體數Table 3 Species richness and individual number among waterbird guilds in the northern Lake Erhai in winter of 2014 and 2017
2.2 水鳥多樣性變化
2014年和2017年冬季洱海北部共調查到33個物種(表2),其中2014年冬季共記錄到22個物種,11 611只個體;2017年冬季共記錄到30個物種,17 278只個體,因此,2017年洱海北部冬季水鳥群落無論從物種豐富度上,還是多度上都高于2014年。通過詳細比較各功能集團的物種豐富度和多度變化(表3),發現潛水類和鉆水鴨類無論在物種豐富度上,還是多度上,2017年冬季均高于2014年冬季,僅有涉禽物種豐富度不變,且多度下降。與2014年冬季相比,2017年冬季潛水類中新增加的物種是黑頸Podiceps nigricollis、紅頭潛鴨Aythya ferina和青頭潛鴨Aythya baeri等3個物種;鉆水鴨中新增加的物種是灰雁Anser anser、針尾鴨Anas acuta、羅紋鴨Anas falcata、斑嘴鴨Anas poecilorhyncha、赤頸鴨Anas penelope、琵嘴鴨Anas clypeata等6個物種;涉禽的物種豐富度雖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其中3種發生了周轉,即2014年冬季的水雉Hydrophasianus chirurgus、磯鷸Tringa hypoleucos和白琵鷺Platalea leucorodia為2017年冬季的白胸苦惡鳥Amaurornis phoenicurus、白眉田雞Porzana cinerea、鳳頭麥雞Vanellus vanellus所取代。
3 討論(Discussion)
3.1 水鳥群落變化
雖然2014年洱海北部冬季水鳥的調查頻次更高,本研究仍然發現洱海水位較高時,即2014年冬季洱海北部水鳥群落物種豐富度和多度均少于水位下降后2017年的。洱海水位下降后,各功能集團的表現為潛水類和鉆水鴨的物種豐富度和多度均增加,涉禽類的物種豐富度沒有改變,多度下降,這與淺水灘地型濕地研究得出的結論不同,后者的研究結論為水位下降會使涉禽和鉆水鴨多樣性上升,而潛水類多樣性下降[3]。這是由于在水深岸陡型的湖泊中,潛水類不存在最低水深的限制,因此潛水類的多樣性沒有像淺灘發達的濕地一樣表現出下降。涉禽在淺水和深水濕地對水位變化表現出的差異,是由于洱海中的涉禽并非像淺水濕地中一樣在灘地上覓食活動,而是在洱海近岸生長旺盛的漂浮植物鳳眼蓮形成的草苔上活動,鳳眼蓮本身以及附生的無脊椎動物均能夠成為涉禽的食物。根據調查人員觀察,2017年漂浮植物鳳眼蓮的生長沒有受到洱海水位下降的顯著影響,因此對涉禽來說,覓食棲息地沒有發生明顯的改變,涉禽的物種豐富度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但是與2014年相比,2017年冬季后期洱海濕地管理加強了對鳳眼蓮的打撈去除,可能是涉禽多度下降的原因。
3.2 鉆水鴨種類的增加
2017年洱海冬季水位下降之后,洱海北部的鉆水鴨種類同時增加6種。一直以來,洱海北部水鳥利用的棲息地類型較為單一,以明水面和漂浮植物帶為主,而較缺乏鉆水鴨覓食所需的淺水灘地。食物資源可獲性是限制鉆水鴨能否利用棲息地的重要因素,因為即使在食物資源豐富的情況下,水深較大時,鉆水鴨受限于自身的頸長,如果不能夠到食物,依然不能使用這樣的棲息地。鉆水鴨只有水位下降至其可利用水中食物時,才會出現[9]。
3.3 洱海水位下降與水鳥多樣性變化的潛在關系
雖然缺乏關聯二者的食物資源變化直接證據,但本研究依然能夠為洱海水鳥群落變化提供線索。楊嵐等[15]1984年冬季對洱海進行調查時,報道灰雁、赤頸鴨等2種鉆水鴨曾經為洱海的優勢物種之一,但是近代卻大幅減少[16]。洱海在1963年以前為天然調節水位的湖泊,水位較高(1962年年平均水位為1 974.26 m),經過20年的流域生態改變、工農業用水增加后,在1982年年平均水位下降為1 971.10 m[17],而此時也巧好是鉆水鴨為洱海優勢物種的時候。近代,為改善洱海水環境,政府又重新提高了洱海運行水位[18],鉆水鴨亦開始大幅減少。因此,歷史上鉆水鴨的數量變動亦與水位波動相符合。本研究在更加精細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從沒有到發現它們的再次出現,而且是多個物種同時出現,應為共同的環境因素所吸引導致的,極有可能是低水位這一因素。結合歷史上洱海鉆水鴨數量變動和水位變化的過程,本研究認為水位下降是鉆水鴨類物種豐富度增加的必要條件。未來關于水位波動帶來的食物資源變化的研究將進一步證明水位變化是洱海水鳥群落發生改變的根本原因。
綜上,對于水深岸陡型高原湖泊來說,水位下降可能使冬季鉆水鴨和潛水類水鳥的物種豐富度和多度均增加,這一結論雖然需要更長的時間尺度和更多的湖泊研究來支持,但在大量水鳥的遷徙過境或越冬期,以提供更多水鳥可利用的棲息地為目的有計劃的降低湖泊濕地水位,將毫無疑問有益于水鳥多樣性的保護。
致謝:感謝大理市洱海保護管理局提供研究所需洱海水位數據,感謝日內瓦大學Davide Fornacca博士對英文摘要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