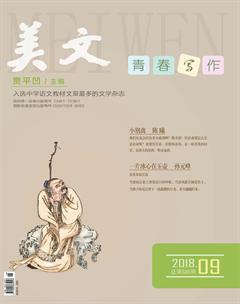復仇與寬恕
安黎
僅讀過一部武俠小說,我便勒令自己與這等書籍絕交。
這類作品在我看來,堪比含毒的精神甜果,初吃很過癮,復吃則上癮,多吃必中毒。
一個少年或少女,在夢想初綻的年齡,目睹自己的父親被人謀害,之后的全部人生,便簡化成了兩個字:報仇。復仇,既濃縮為他們活著的唯一內容,又演化為他們活著的終極目標——這是何等的執著,又是何等的哀痛?于是乎,人生就在窮追不舍中度過,生命在打打殺殺中耗損,及至消滅仇人,隕落自己,了卻一筆血債為止。
這樣的生命邏輯,貌似無愧于“忠孝”二字,但其價值何在,意義何歸?
冤冤相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私刑解決私仇,以血刃清算血恨,究其實質,皆為蠻荒叢林的古舊法則,與現代文明的人際理念,差之千里。
衡量文明躍升與生命進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于如何對待“恨”和化解“恨”上。
“恨”是人性中的毒藥,自己釀制,最終也必將自己吞食。“恨”的毒性,不一定能毒死所“恨”的對象,但很容易將自己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可以肯定的是,“恨”的種子一經在心田發芽,便宛若春天的韭菜那般瘋狂恣肆地生長,繁殖力超乎尋常,割掉舊的一茬又會長出新的一茬。割割不斷,生生不息,枝枝蔓蔓的“恨”,足以將人的心靈緊緊地裹纏,讓其動彈不得。被恨意俘虜的心靈,猶如坐擁黑牢,從此暗無天日,再也難以沐浴陽光與甘霖。
“恨”是深入骨髓的病菌,一旦附體,便成頑疾,很難療治。“恨”的母體為“仇”,是由“仇”分娩的;但“仇”,又是由“恨”孕育的——兩者既血脈相連,又互為基因,更彼此推波助瀾。要解除“恨”,就要釜底抽薪,將心中淤積的仇怨的冰凌,予以逐步消解和徹底融化。地雷摘除了,爆炸的幾率就降低了;心暖起來了,“恨”意也就稀釋了。
相比之下,寬恕,也許是人的精神領域,最為有效的融雪劑。寬恕猶如暖陽,既能把一切霜凍化為烏有,又能把任何一個幽暗的角落徹底照亮。寬恕更形若對癥下藥的救心丸,能把人墜落懸崖的心靈救贖,能促使人執迷不悟的靈魂得以復蘇。
被“恨”折磨,并被“恨”牽著鼻子狂奔的復仇,毫無疑問是一條自我毀滅的不歸路,唯有寬恕,才能回頭是岸。寬恕,貌似是在原諒仇家,其實是在原諒自己。
相較于人性中的其他美德,寬恕是所有美德中至高無上的巔峰。巔峰,是由寬厚的胸懷和偉岸的人格鋪墊與托舉的。寬恕散發的巨大光澤,既輝映古今,又輻射四方與四季。
《論語》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子貢問老師孔子:有沒有一個字可以讓人陪伴終身?孔子回答:有,那個字就是“恕”。
“恕”和“容”是近義詞,但兩者內涵的尺度有著很大的不同:“容”只限于是對異己的包容與不計較,而“恕”,則是對仇家的體恤與放棄追究。如果“容”是一座寬大的倉儲,可以接納儲存各類喜歡不喜歡的物品,那么“恕”則是浩渺的蒼宇,能夠將整個大千世界一并囊括,其中包括善,也包括惡。“容”即使再寬闊,但終究是有邊界的,而“恕”卻無邊無際。
寬恕,不是枉顧原則,丟掉是非;亦不是對暴虐的放任,對罪惡的縱容,而是在罪錯已經鑄就的情況下,面對殘局,自身所釋放的一種善意。罪錯造成的惡果,猶如水潑于地,已無可挽回,與其沉浸于夢魘,糾纏于過往,執著于懲罰,毋如著眼于未來,抬頭仰望天藍,低頭俯視草綠,既饒恕過對方,也釋放出自己。
人活一生,草木一秋。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人可以庸庸碌碌,滿足于吃飽穿暖,享受平凡的幸福;也可以豪情萬丈,以改天換地為己任,立志于彪炳史冊,但絕然不可滑落仇恨的迷津,誤入復仇的歧途——那樣的話,既是對自己的無情辜負,更是對世風的再度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