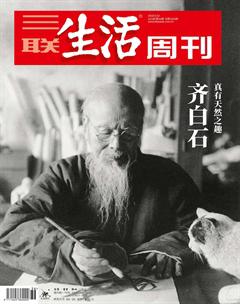那時人人都確信未來會更好
張星云
“五月風暴是個高潮,但并不是所有問題都在這場運動中得到了解決。”
如今已經70歲的達尼埃爾·塔達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不認為自己是“六八一代”。1947年出生的她是戰后嬰兒潮一代,她和那些五月風暴的參與學生同時期長大、上學,也信仰共產主義。1968年她正在巴黎上精英學校預科班,五月來臨,全校都停課了,但她沒有去壘街壘。風暴結束后,她從1970年到1984年在中學當了14年老師。此后她致力于研究20世紀法國政治史,從1997年起,她開始在巴黎第八大學執教。2012年至2016年,擔任巴黎八大校長。她研究的主要領域涉及社會運動史、街頭示威游行史以及政治危機史。
在專訪中,她和本刊聊了聊50年后歷史學界對五月風暴的理解。
三聯生活周刊:已經50年了,近年在法國,是否出現了對五月風暴的新學術研究成果?
塔達科夫斯基:首先我們需要區分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分別的研究成果,以及社會對歷史事件的解讀,它們都是不同的。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最初10年,學者們還只關注巴黎尤其是在拉丁區發生的事情,回顧科恩-邦迪等學生領袖當時做了什么,并沒有對整個事件進行全面的觀察和研究。
第一部比較全面看待當年的書籍,并不是一部科學論述的論文,而是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一部隨筆,叫《為十周年紀念活動和講話做出的微小貢獻》(Modeste contribution aux discours et cérémonies officielles du dixième anniversaire)。在這篇文章中,德布雷對五月風暴進行了正面評價,將它視為之后法國新自由主義的起點。那是他1979年寫的文章,那時法國剛經歷了第二次中東石油危機,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對五月風暴態度的突然轉變。直到1999年,社會學家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亞佩洛(Eve Chiapello)合著《資本主義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以左派的批判視角,將五月風暴比作資本主義派來的特洛伊木馬,認為美國自由資本主義通過五月風暴打入了法國。
與此同時,歷史學家也在進行研究,1988年,五月風暴20周年的時候,安托萬·普羅斯特(Antoine Prost)在一次學術報告中頭一次提出:我們已經知道1968年在巴黎拉丁區發生了什么,學生們干了什么,但我們也應該知道當時巴黎以外的省市都發生了什么,工人們都干了什么。由此五月風暴的歷史記憶形象發生了很大變化。隨后各個領域的學者都在進行自己的研究,一些學者關注五月風暴之前兩年法國社會矛盾和罷工風潮。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汀·羅斯(Kristin Ross)則觀察到在外省一些地區,運動之前大學生和年輕工人就產生了明確的交流與溝通。2008年時任總統薩科齊公開表示法國需要與五月風暴徹底決裂,雖然他的言論不會影響學術研究,但卻是政治領域對五月風暴最激烈的一次攻擊。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近幾年針對五月風暴時期外省的記述書籍越來越多,還有大量講述五月風暴參與者后來個人際遇的書籍。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不再孤立五月風暴,而是用編年史的視角看它前后10年發生的事情。
三聯生活周刊:不同的語境下,人們對五月風暴的解讀是否也不同?
塔達科夫斯基:當時各類階級、各種思想流派都參與了五月風暴,而這些參與者們其實在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上存在著非常大的內部分歧,以至于后來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定義也被討論持續至今。“五月風暴”“五月事件”“五月運動”“五月危機”“全國大罷工”,不同團體對1968年5月份發生的事件起了各種各樣的名字,也代表著對它各種各樣的解讀。

法國歷史學家達尼埃爾·塔達科夫斯基,她致力于20世紀法國政治史研究
如果我們拉開距離,從更廣義的歷史角度去看,我們會看到,盡管參與者內部分歧非常多,但那時所有人都相信世界需要改變,政治也需要改變,盡管變化的方向不一定一致,那時人人都確信未來會更好。我后來也參與過一些學術討論會,我們很多專家在一起討論,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當人們不再相信未來會更好的時候,五月風暴就算徹底結束了。
三聯生活周刊:1968年無論在美國、歐洲還是亞洲,都發生了很多運動,從五月風暴的起因上來看,現在如何給它定性?
塔達科夫斯基:五月風暴其實屬于一場國際運動中的一部分,而這場國際運動又有著明顯的代際特點,是屬于一代人的社會運動。我們知道60年代的西方國家,很多社會現象同時出現。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嬰兒潮一代開始成年了,同時各國經濟大幅增長,西方進入了當時廣為詬病的“消費社會”。隨著現代化的進行,教育普及,嬰兒潮那一代接受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即獨立的青少年。這一群體大量涌入大學,1948年至1968年間,法國大學生數量增長了180%。西方各國大學里人滿為患,顯然無論學校還是整個社會都沒有準備好接待如多的大學生。也就是在同時,1965年起,反對越戰的運動逐步轉變為政治運動。從北美和西歐開始影響到世界各地。
1968年的法國,那時新政權剛滿10周年,而那10年法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高速發展。我會用一位德國歷史學家的理論來做出定性,他就是主要研究德國納粹之前魏瑪共和國歷史的德特勒夫·J.K.波依克爾特(Detlev J.K.Peukert),他曾提到過一個概念,“晚期現代性的危機”。通常情況下,歷史上兩個動蕩時期中間會有一個間隔期,但1968年的法國卻沒有這個間隔期,兩個動蕩時期相連,于是產生了危機,我覺得用這個詞來形容五月風暴最合適。
五月風暴發生前的兩年里,社會沖突就已經在不斷激增了。1965年法國政府通過的五年計劃中打算于1968年7月1日取消貿易壁壘,正式進入歐洲共同市場,以完成法國經濟的現代化。為了鼓勵更活躍的自由市場,法國政府決定漲工資、擴大政府采購、增加企業競爭力,工薪階層遭遇失業危機,而農民因取消貿易壁壘受到嚴重沖擊。與此同時,政府還在醞釀一場大學教育改革,給予大學更多自治權利,引入競爭體系,提高入學標準,這也引起了很多大學生群體的不滿。
三聯生活周刊:所以五月風暴這場運動的主體,是大學生還是工人?
塔達科夫斯基: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稱5月10日學生發起的街壘之夜為“危機事件”,那晚460名學生被逮捕,367人受傷。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危機事件”指的是“本應正常開始并終結的諸多歷史事件,最終卻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場廣泛的危機”。
街壘之夜引發了5月13日全國大罷工所有占領和示威運動全都以言論自由和個人主義為名,法國社會學家多米尼克·梅米(Dominique Memmi)將這種占領運動稱為“近距離控制危機”。由此,整個國家陷入停滯和癱瘓,所有國家機關都喪失了運轉功能,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巴黎的學生們才擁有了自由的空間持續進行游行示威。因此至于學生還是工人是五月風暴主體,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工會發起的全國大罷工,巴黎學生們組織的街壘之夜也不會成為“危機事件”。
三聯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說,雖然五月風暴沒有獲得直接的成功,但它的訴求在接下來幾年中都獲得了實現?
塔達科夫斯基:其中一些訴求確實實現了。為了贏得選舉,戴高樂把工資提高,使男女薪資更加平等,使年輕人工資提高,重新組織大學,讓更多年輕人獲得上學機會。雖然戴高樂最后下臺了,但接下來五年里法國連續不斷地進行法律改革。1971、1972年,德斯坦上臺后進行了一系列社會和文化的開放政策,將選舉權最低年齡降低到了18歲,通過離婚法案,自愿人工流產法案,取消法國廣播電視辦公室以結束電視廣播壟斷,我們看到的是右派政府不斷進行開放改革,順應潮流,直到后來十月危機出現,法國政治才進入了一個新的周期。
三聯生活周刊:那如何總結五月風暴對現代法國社會的遺產呢?
塔達科夫斯基:50年過去了,然而這50年并非一種線性的歷史發展軌跡,全世界的經濟基礎變了,科技變革,政治也變化了,蘇聯解體了,所以我很難明確說出如今法國日常生活中哪些是五月風暴的遺產。當年我們每個人參與的方式不同、立場不同,隨著時間推移,五月風暴留給我們的遺產是非常復雜的。
比如很多人說,五月風暴之后,女性主義得到了更好的發展,但其實五月風暴的領導人都是很男權主義的,他們對女性也不夠尊重,以我當年自己走在街頭的印象,以及后來的很多歷史照片中,參與運動的女性并不多見,還是以男性為主,所以很難說女性通過五月風暴直接獲得了更多的權利,至于個人主義的地位,以及性解放,也是同樣的情況。
如果不在紀念五月風暴這個語境下探討,我會說我獲得了更多言論自由。但法國特別喜歡搞紀念活動,然后將五月風暴推到一個很高的地位。其實后來法國還出現了很多政治運動,可以說,五月風暴當年將很多社會問題推向了一個高潮,但并不是所有問題都在這場運動中得到了解決。
三聯生活周刊:50年過去了,想象中的五月風暴與真實的五月風暴是否存在沖突?尤其對于沒有親身經歷過歷史的年輕人們來說。
塔達科夫斯基:如果我跳出紀念50周年這個語境下來談五月風暴,尤其我又作為一位大學里的歷史學者,離開紀念語境越遠,我越覺得五月風暴對現在的影響很小。社會學家瑪麗-克萊爾·拉瓦布爾(Marie-Claire Lavabre)專門研究不同類型的集體記憶,她說過,歷史事件確實需要每五年十年進行一次紀念活動,媒體們也會追隨熱度每五年十年用封面報道重新回顧歷史。
最近巴黎又開始了大規模游行,法國國鐵和法航罷工,學生罷課、占領教室、封鎖學校,巴黎街頭被涂上了紀念五月風暴的標語,寫著“我們要繼續”。這就形成了并行的兩種記憶,歷史記憶和想象中的記憶。其實今年在巴黎的游行示威與五月風暴沒有任何關系,也沒有任何相似性,五月風暴的那個時代早已結束了,但想象中的記憶有時比歷史記憶更強大。好比近年雷恩的抗議者也磊街壘,大家只會嘲笑他們,但如果巴黎的抗議者磊街壘,人們馬上想到的是巴黎悠久的示威傳統。
這一點在1936年人民陣線運動每次的周年紀念活動中更加明顯,隨著時間推移,如今人民陣線運動早已褪去了它原本的政治內涵,成為一個純粹的文化符號。而五月風暴還沒有成為完全的文化符號,但10年之后,不好說。無論如何,我不覺得五月風暴的記憶還會直接對現在的社會進步有幫助。
三聯生活周刊:你是“六八一代”嗎?
塔達科夫斯基:其實我并不清楚大家說的“六八一代”到底是什么人,經歷過1968年五月風暴的這些人中,有很多人覺得自己并不屬于“六八一代”。托洛茨基主義者、毛主義者、工會成員,他們都不覺得自己是“六八一代”。
因為整個事件是被媒體充分引導的,情境主義國際喊出“街壘底下是沙灘”等口號,攝影大師們拍的游行照片、巴黎美院制作的抗議宣傳海報,還有五月風暴之后的《太凱爾》雜志,這些元素都將這場運動符號化,學生領袖科恩-邦迪與警察對峙的照片當時立馬在全世界范圍獲得了影響力,大家開始使用“六八一代”這種說法。
就像當時科恩-邦迪說的,1968年這一代確實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但實際上每個人創造的新東西都不一樣。我覺得真正給予這一代人共性的就是1968年這一時間段,時代在變,社會在變,經濟在變,正好那一年法國發生了五月風暴。
三聯生活周刊:盡管法國有著悠久的游行抗議示威傳統,但似乎五月風暴成了法國現代史上游行的最高峰,是否可以說,五月風暴是法國游行史上的一個參照標準?
塔達科夫斯基:街頭游行示威長久以來在法國占據著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成了法國的特色。自50年代以來,法國人開始用“manif”這個“小詞”來指稱抗議示威,抗議示威不再代表革命,也不再會對政權制度起到推翻或建立的作用,甚至成了革命的相反面。
尤其是1934年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以及1968年的五月風暴,兩場示威分別開啟了危機,又在隨后為危機找到了出路。這兩場重大危機都并非制度危機,共和制在這兩場危機中都存續下來。可以說,這些抗議示威反而有助于人們在現有的政府管理體系下解決危機,歷史發展到那個時期,抗議示威成為擁護共和國這一社會共識的表現方式之一,正是也只有通過游行示威,反對意見才能夠得以表達。在1968年之后,法國游行示威數量急劇增長,60年代巴黎每年會有差不多50次游行,90年代達到每年上千次,現在則為每年2000次。抗議示威成為質詢政府的一種常規方法,甚至扮演了自發性全民公投的角色。
然而從2003年開始,游行在法國幾乎完全失去了曾經的作用,再也沒有任何政府提案因示威游行帶來的壓力而被取消。游行示威的起因不再是曾經的“危機示威”,人們無法突出矛盾并在短時間內將其公開化,更多新游行的起因是對代議制政治體制衰敗的不滿。由此游行不再具有以前實證主義歷史觀,新形式的游行展現了現時主義(présentisme)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