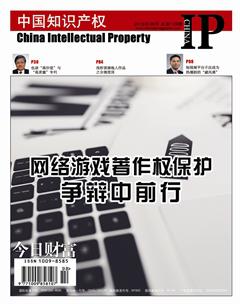淺析表演他人作品之合理使用
白帆 胡萍
隨著群眾精神需求的增長與社會文化生活的繁榮,公開表演他人作品的現象已屢見不鮮,而這樣的表演很多并沒有獲得作品著作權人的授權,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為平衡權利人與社會公眾間的利益,《著作權法》對著作權人的權利進行了必要限制,為公眾提供了可以不經許可、合理使用作品的途徑,1但在實踐中,法律的規定卻似乎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清晰。
合理使用的邊界存在模糊性
《著作權法》采用了雙重結構來對表演進行規范:一方面在第十條第一款第九項規定了著作權中包含有表演權這一權項,即控制公開表演作品和公開播送作品表演的權利;另一方面在第三十七條第一款對使用他人作品演出也進行了規定,即表演者(演員、演出單位)或演出組織者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而作為對作品著作權中表演權的限制,《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九項規定,如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該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的,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著作權法所享有的其他權利。
《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他人作品進行表演的規定似乎是較為明晰的,其中“免費表演”由“未向公眾收取費用”和“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兩個要件構成,但目前在實踐中卻往往會將“免費表演”解讀為“非商業性表演”,并增添其他新的判斷要素。持此觀點者一般認為,目前的營銷手段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完全能夠實現不直接向公眾收取費用而又為演出的組織者、贊助者等帶來經濟利益,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為給著作權人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害;社會發展已遠遠超出了法律條文規定的要件,因此需要進行適當擴展,對法律規定進行擴張解釋。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確有合理性,但對“非商業性”的理解又會帶來新的問題。具體而言,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存在如下一些表演方式:1.向觀眾收取費用;2.不收費,但要求觀眾以其他行為換取觀看表演的資格,如購買商品、加公眾號、轉發集贊等;3.對觀眾無要求,但在表演中主動甚至重點宣傳企業或產品,包括播放、宣讀和派發廣告等;4.在表演中附帶提及企業或產品,如標注logo、冠名贊助、植入廣告、贈送試用品等;5.在營業場所(如商場、酒吧、咖啡店等)對作品進行人工或機械表演;6.在非營業場所組織目的特定的義演,觀眾可自愿捐款;7.在學校、福利院等場所面向學生、家長、老人、兒童等特定群體進行的免費表演;8.在非營業性的公共場所面向不特定公眾進行免費表演。以上列舉的表演方式并未窮盡,但已然使問題更加復雜化。
當我們運用抽象概括法區分思想與表達時,正如漢德法官所說,在抽象化的過程中總有一個點是區分內容是否可以受到保護的。筆者也同樣相信,在判斷表演是否構成合理使用時同樣存在這樣的界分點——個案的情況千差萬別,但一些標準應該是具有普適性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地找到并接近這一平衡點。
關于“對合理使用作品進行表演”的資料解讀
(一)法規沿革與立法釋義
在對法律條文進行解釋時,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編撰的法律釋義往往可以體現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規范時的思考,也是進行主觀目的論解釋時較為權威的依據。合理使用作品進行表演的規定最早來源于1990年版即第一版《著作權法》的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九項,其條款序號與現行《著作權法》相同,但表述有所差異,具體為“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同年出版的《著作權法釋義》中認為,“免費表演”指“非營業性的演出”,且其不包括向觀眾收費后演員捐獻演出費的“義務演出”。2
2001年版《著作權法》將該條規定修改為現行著作權法的表述。同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釋解》中則使用了與前一《釋義》相同的表述,即同樣認為“免費表演”指“非營業性的演出”,同時說明為進一步明確什么是免費表演,著作權法修正案作了明確的界定(兩個要件),以利于實踐中操作執行。3該釋義中使用了“明確的界定”這一表述,似乎表明立法者的本意是認為“免費表演”僅由兩個要件構成。
而在國務院法制辦2014年起草的《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相應條款的表述又發生了變化,該稿第四十三條第一款第九項在現行著作權法規定的基礎上,增加了“也未以其他方式獲得經濟利益”的新要件。從中可見,這一修改明顯是對“非商業性表演”觀點的回應與印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提到的兩部法律釋義中,也均使用了“非營業性的演出”的表述。
(二)國際公約與比較法
《伯爾尼公約》第11條規定了著作權中包含有公開表演權,同時第11條之二規定的播放權的一部分和之三規定的公開朗誦權也屬于我國著作權法中表演權的內容,但該公約并未對表演權專門設置例外。《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第13條則對著作權的限制進行了概括性規定,即著名的“三步檢驗法”(three-step analysis)條款。該條規定實際上來源于《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但將適用的對象從復制權擴大到所有著作權權利。此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也都將三步檢驗法納入其中,作為對專有權限制與例外的評估標準。
各國國內立法方面,《日本著作權法》第38條明確規定了"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要求,且不得向觀眾收取任何費用(即以任何名義收取的對價)。《韓國著作權法》第29條第1款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既不向聽眾、觀眾或第三人收取費用,也不向表演者支付費用的,可以對已公開作品進行公開表演或廣播。《德國著作權法》第52條規定無營利目的、對參加者不收費、表演者無收入的表演或宗教活動表演無需經過著作權人許可,但應支付適當報酬;教育、福利機構舉辦的僅由特定范圍人員參加的活動無須付酬;公開戲劇表演應取得權利人許可。《美國版權法》第110條分別對非營利教育機構、宗教集會和儀式、政府機構、非營利性組織、銷售企業表演作品等進行了詳細規定;其中包括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商業利益,且不支付給表演者、發起人或組織者以費用或其他報酬而表演非戲劇文學或音樂作品,還包括銷售企業為促進作品或播放裝置的零售而免費向公眾表演非戲劇音樂作品。《法國知識產權法典》L.122-5條規定作品發表后,作者不得禁止僅在家庭范圍內進行的私人和免費的表演,和用作教研中說明的對作品摘要的表演。《英國版權法》第34條規定了教育機構活動過程中對作品的表演。《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277條僅規定了官方及宗教儀式或葬禮時可公開表演音樂作品。《巴西著作權法》第46條第5款規定,為了向銷售者展示的目的,在商業場所使用作品不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只要該場所銷售可以進行此種使用的材料或設備(即銷售被展示的作品復制件或播放設備);第6款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在家庭范圍內或完全以教學為目的在教育機構進行舞臺和音樂表演不侵權。《埃及著作權法》第171條第1款也有類似前述第6款的規定。
由比較法視角可以看出,目前世界范圍內對合理使用作品進行表演存在四種不同的規范形式:一是為其設置一般條款,該條款通常明確包含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要求,其余要件則與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較為一致;二是不設一般條款,而是對表演主體、目的、場合等進行詳細限制,如私人(家庭)、教學、福利、宗教活動、葬禮等;三是前兩點結合的雙重結構,即規定符合一般條款規定的情形無須著作權人許可但須支付報酬,而符合法律規定的特定目的則無須支付報酬;四是一些國家特別為作品或其播放設備銷售者的展示行為設置了例外。
(三)學界觀點
專家學者在自己撰寫的教科書中的觀點也可供參考。在國內學者的研究中,王遷老師認為,從“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推斷,“免費表演”應僅指現場表演,而不包括機械表演;“費用”和“報酬”則包括以任何名義收取或支付的,與欣賞或表演作品有關的直接或間接的費用和報酬;此外,進行籌款的慈善義演并不屬于免費表演。4張今老師的觀點也與此相近。5吳偉光老師則認為,“免費表演”也包括機械表演,其具有即時性、受眾范圍有限的特點;如果表演有商業上的廣告或者贊助等收入,那么也不是免費的。6
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享有盛譽的《著作權與鄰接權》一書中在“自由無償使用”部分認為,該情況可能包含在學校進行的表演或演奏,為了示范目的在專門商業機構中播放音樂錄音作品,私人表演和免費表演等。7另有日本學者認為,“不以營利為目的”是自由使用作品的獨立的要件之一,其中既不包括直接目的為營利,也不包括間接目的為營利,例如營利單位為宣傳商品而舉辦的免費表演和商店播放背景音樂等。8
由上述資料可見,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合理使用他人作品進行表演應不以營利為目的,其中包括間接的營利。但如何判斷“間接的營利”,無論是從比較法還是學術研究的角度,目前都缺乏明確、可操作的判斷標準。
對“免費表演”進行規制的可能的法律構造
從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看,法律為免費表演設置的例外是很嚴格的,其不僅是基于繁榮文化、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的目的,而且還要在滿足此目的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保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防止某些商主體以“免費表演”為名搭便車進行商業宣傳。基于此,我國目前采取的是一般條款式的立法模式,在其中似應加入排除間接營利的這一要件。具體而言,筆者認為該條款中的幾個判斷要件可作如下展開。
一是向公眾收取的“費用”也應包含其他替代性義務,如要求觀眾購買商品等換取觀看表演的資格。而在被課以加公眾號、轉發集贊等義務時,觀眾看似并沒有費用的支出、沒有財產的變動,此時可用下文將分析到的“間接營利”要件進行判斷。
二是在判斷表演者是否獲得報酬時,基于不當得利法的原理,應支出的費用未支出也屬于一種消極的獲利,故表演者本應支出費用得到減免似乎也可視為其獲得了報酬。例如某企業免費向一業余表演團體提供演出場地、設備、服裝、道具等,換取在演出中標注logo、冠名贊助、插入廣告等機會。實踐中,在表演者與欲獲宣傳的經營者分離的情況下,鮮有后者不向前者支付報酬或提供其他利益的情況,除非兩者具有密切的關聯關系;而在表演者和經營者是同一主體的情況下,判斷表演者是否因演出而獲得報酬則并非易事。
三是關于“間接營利”的判斷。在現行著作權法及相關學說對其并無詳細規定及闡釋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引入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一些要素,來對“間接營利”或者說對法條中的“免費表演”進行解釋,以達到一方面更為妥善地實現利益平衡,另一方面使法律增加確定性和可操作性。之所以做如此考慮,一方面是基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知識產權法中所具有的兜底性質,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蘊含的對不勞而獲、搭便車等行為的規制,以及對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商業道德的維護。
具體而言,在主體方面,對營利的追求意味著表演活動中必然有經營者的參與,即組織表演或者為表演提供幫助(包括資金、服裝道具、場地、設備等)的主體,一般為具有營利性質、追求利益的經營者,包括商品生產、銷售者和服務提供者等。更為重要的是,在獲利方面,“間接的營利”意味著該經營者雖未通過向觀眾收取費用而直接獲利,但通過表演活動卻能夠為其奪取交易機會、贏得競爭優勢,或者破壞其他經營者的競爭優勢。例如借助“免費表演”實施企業或商品的宣傳推廣活動,或者提升服務場所檔次等,都屬于為經營者攫取交易機會、爭奪購買力的行為。
基于這一觀點,前文所述要求觀眾加公眾號、轉發集贊等換取觀看表演資格,在表演中主動或附帶宣傳企業或產品,在營業場所對作品進行人工或機械表演等,均屬于為經營者增加競爭優勢、謀取交易機會的行為。而如果用這一觀點對進行籌款的慈善義演做解釋,則似乎可以認為眾多企業在慈善義演上的捐款屬于為企業贏得正面評價、積累商譽的行為,現實中也發生過某些企業在鏡頭前承諾捐贈巨額善款,但事后又反悔、拒不認賬的情況。在此還可另舉一例:某著名歌唱家受其好友、某商場經營者邀請,赴該商場演唱多首歌曲并分文不取,觀者紛至沓來。此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但為該商場增加了客流量、攫取了交易機會與購買力,更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增加了該商場的知名度、提升了商譽,使其贏得了競爭優勢。此時該歌唱家顯然不能主張其表演是對音樂作品的合理使用。
需注意的是,本文對“間接營利”的判斷,雖然借用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理論和要件,但所得出的結論是表演者的合理使用抗辯并不成立,其行為構成侵犯著作權(表演權),而非不正當競爭。進一步展開,在“間接營利”的情況下適用著作權法,其實也是對行為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不勞而獲、食人而肥的行為進行規制,但著作權法保護的是著作權人的合法權利,反不正當競爭法則旨在維護其他競爭者、消費者合法權益和市場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