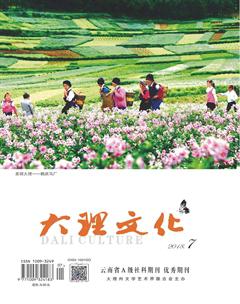漂浮與存在
陳苑輝
像夜風一樣出走
驀然回首,我的一只腳已邁人不惑的門檻,離遲暮也就那么一點時間了。離墓地還有多遠?不知道,也許明天,也許明天的明天,未知像一條冰冷的蛇在潛伏。
不惑,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概念,天地如此博大、奧妙與深邃,細小如蜉蝣的我們恐難“不惑”,有“惑”才是常態吧。惑,始于年輕,卻沒有終點。一個人從年輕的時候出發,至兩眼昏花的遲暮,究竟會經歷多少淺灘與湍流?這是長期以來困擾我的問題。十幾年前背上簡單行囊形單影只潛入陌生城市的畫面,總會不分時段襲擊我的腦海。當我凝望水泥路上一片片寂靜的枯葉,仿佛心也緊貼著冰冷的地面,不知如何向人訴說。
人生路漫漫,也許每個人至少設想過一次出走。出走,是年輕人特有的秉性。對于心懷理想與溫情的人而言,出走的想法就像一小團搖曳于野外的燭火,永不熄滅。出走,免不了被貼上幼稚的標簽,跟逃避、背離搭上關系,一心馳向更遠的遠方,去抵達一個從未到過且能巧妙繞開熟人的地方,默默翻開嶄新的日歷寫下一行行印記。
日歷是時間的皮囊,一本日歷撕完了,這一年就走到了盡頭。我的母親有個習慣,每天晚上都會撕一頁日歷。趴在書桌上看書、寫字的我,聽見“哧”一聲,抬頭一看,她已經扯下了“今天”,“明天”或綠或紅的底色也顯示出來了。年少的我凝視著兩個巴掌大的日歷,總有一股無法言說的憂傷在心房蟄伏起來。
多年后,我陷入下落不明的漂泊,隱形的日歷也就掛上了心頭。
出發前,朦朧的山巒尚未褪去夜色的束縛,寒風從山坳口涌過來,而雙親已經幫我收拾了行囊。清晨,村莊里的煙囪還沒吐出縷縷炊煙,我像夜風一樣離開故土。我的心里很亂,很亂,不知道此去一年是否順暢,勤懇的工作能否換來體面一些、從容一些的生活。坐在摩托車上,我一路眺望那層層疊疊的山巒,耳朵被呼嘯的山風掰扯著,冷,刺痛,仿佛有一柄刀在刮。到了墟鎮,改乘一輛客車直達務工的城市。鉚足了勁的車輪將我隔離地面,我像塵埃一樣飄浮起來,一直飄向陌生的城市。剎那間,我恍惚覺得過往的時光偷偷埋了伏筆,母親撕下的一頁頁日歷不正是我的情感頁碼嗎?離開了家鄉,歲月不斷地從我身上撕下眷戀、痛疼,直到生命的頁碼被徹底撕完,我的日子也告罄。
我一直覺得有些東西是冥冥之中就已注定的。譬如很多年前我在另一個城市教書之時曾設想自己的下一站會不會是這座城市,結果才過去一年半,我便輾轉于此城。
在日益繁榮的城市能停留多久我不知道,就如漂浮的小船蕩入了廣闊的海洋,槳并不一定有絕對的權力把握其行蹤,很多初衷都經不起時光殘忍的手。踏進城市里的水泥路,我甚至比不上一棵樟樹、一株大葉榕,它們的穩定與踏實令我自嘆弗如,它們的綠意與伸展空間讓我低下了頭,它們的內心可以安靜如水,對如織的車輛和潮水般的行人無動于衷,而我顯然做不到,我總是多愁善感,總是在心里鄙視著骯臟的事物,總是擔憂那些和我一樣游走在這座城市里受傷、孤獨的靈魂,碼著一個個冷冷的文字。
愁緒難耐的夜晚像風一樣,偷偷跑到某個街邊的燒烤攤灌幾瓶冰涼的啤酒,目送一個個歪來倒去的身影消失于轉角。酒精沒有解救我,微涼的風吹來吹去,我用力踢著路燈下的易拉罐,讓它在空蕩的夜里發出叮叮當當的響聲。在農村一定會有警惕的狗叫聲,而城市已經沉睡,我只好學一兩聲狗叫,叫聲回蕩在寂靜而空曠的街道。
沉重的肉身溺于三餐一宿,游走的靈魂始終找不到一片棲息之地。“只有憂傷著的靈魂,像一只受傷的小狐貍……開始自敘自聽,邁著狐步返回洞中”,已縊詩人吾同樹在《雨中即思》中這樣寫道,亦契合每個打工者在城市里的心境吧。
無數次佇立于宿舍的樓頂瞭望廣袤的城市,熱鬧就在下面,繁華也在下面,我高高地佇立穹宇下,擁向茫茫無際的虛妄與虛無。
夜風,哀嚎如泣。
在噩夢與妄想之間
起初,我對城市的想象是簡單而美好的,高樓大廈炫目地林立,洶涌的海浪會攜帶著濤聲涌進色彩斑斕的夢。但是過了多久,如履薄冰的痛楚便覆蓋了進城謀生的日子。城市里有那么多鋒利的爪牙,可以伸向每一個角落、每一身肉體。
因為學的是教育專業,我應聘了民辦學校,然后匍匐著前進。民辦學校的老師也是弱勢群體,每個人都苦苦掙扎于教書育人與尊嚴貶值的泥沼。本分地教書,竭力地奉獻,收獲一點小小的幸福,這是我對自己的最初想法。我痛恨一切捕風捉影,痛恨陰險小人居心叵測的告狀,尤其厭惡那些陰冷的臉色、尖酸刻薄的話語,莫名其妙劈頭蓋臉的訓斥與苛責猶如一把冰冷的刀刺進了我的心窩。魯迅先生在《孔乙己》一文中寫道:“掌柜是一副兇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確實如此,若上頭心情不好,員工便成了發泄的對象——學校那么小,我們也總會被逮到。
就這樣,尊嚴在一天天、一點點地瓦解、摔落,滿地皆是……
在偏遠且貧瘠、落后的鄉下,我曾是父母寵愛的孩子,編織著讀書的美夢長大。父親從小也給我灌輸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理念。長大后,我選擇了教育這片凈土,以為可以做些高尚的事,受些真誠的敬重。可是,事實并非如此,從小不斷囤積的善良遭遇了惡,遭遇了刁難與排擠,我的內心消化不了那些侮辱般的訓斥,就像透明的玻璃瓶,如果誰往里頭丟石子,若干年過去那些石子依然會冷冷地躺著——它們極難磨損、消化,時光也對它們束手無策。我只好沉醉于散文和詩的精神鴉片中,試圖忽略玻璃瓶里的石子。我自然知曉,最終我是騙了不了時間的,它冷眼旁觀,且偷走我的一切。
曾經有很多機會擺在我的面前,但我沒有抓住它們。如同趕一段夜路,一顆顆閃光的金子都被我匆匆的腳步忽略了。它們消失了,也就永遠消失了,懊惱和愧疚挽回不了什么,酒精也不能帶我重返昨日那條路。時至今日,究竟是什么魔力讓我一根筋地陷入民辦學校的泥淖而無法自拔呢?我也講不清楚。也許冥冥中一切有定數,很多事情不清不楚地發生,推著人無奈地向前,我們成了木偶人。我女兒出生那一年,迫于宿舍的逼仄,我們在學校沖完涼后,迎著冷颼颼的夜風前去外面的出租房,活像逃荒的難民。詩人北島曾寫過一篇《搬家記》的文章,里面引用了秘魯詩人瑟塞爾,瓦耶霍(Cesar Vallejo)的詩句:“我一無所有地漂流……”想起這句話,我脆弱的情感瞬間被擊中了——在民辦學校教書十二年有余,我成了家也生了孩子,雖不敢說一無所有,卻是實實在在的兩手空空。
而今,晚上躺在十幾平米的宿舍里,往日的遭遇好像冰冷的蛇偷偷爬進來,纏住了夢的翅膀,而我的意念卻一直頑強地掙扎。一次次從噩夢中驚醒過來,心里滿是悵然、迷惘。也許噩夢做多了,儲在另一處的妄想,就敲開一條通道噴出來——它終究無法被世俗壓抑,帶著我飛翔在空曠而孤獨的領域里。這些妄想不能被人發現,也不能輕易暴露出來。有時候,我將它融化在一首歌里,或者將其埋藏在一篇文章中,只讓一小部分的讀者捕捉到。有妄想總比沒有妄想好,否則我早已被塵世淹沒,尸骨無存。
有了妄想,我前行的路上便有了絲絲暖意與光亮。
背井離鄉并不可恥,進城謀生的人都想積累一點錢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合情合理,我也不例外,踏踏實實邁出每一步。返鄉后,看見那些外出謀生的村民都買了房或者購了小汽車,有了這些炫耀的資本,他們說話頗有底氣。我還是老樣子,每年都為坐哪輛客車回家或返城而犯愁。村民不知道我這十幾年外出教書改變了什么,抑或什么也沒改變等于原地踏步。拉家常的時候,話語權都被有權之人或有錢之人掌握了,他們的謬論也會變成真理。面對他們囂張的氣勢,教了十七年書的我依然底氣不足。卑微的人總是誠惶誠恐,加上周圍的附和者皆站在他們一邊,我也就識趣地少說為妙,大多時候我望著夸夸其談的他們,或附上一點苦笑。我不仇富,也不仇權,保持距離是因為受過太多的刺傷。
在城市森林的低處,在噩夢與妄想之間,我消耗著青春的尾巴,像一只在夜間游走的驚恐的老鼠。
路耗掉了時間
2009年,年近三十的我成了家,然后生了兒子和女兒,這是教書以來最大的收獲。幾年時間又倏忽過去,轉眼他們都相繼入學。
從今年九月份開始,原本在同一間幼兒園念書的兒子和女兒分開了,女兒仍留在幼兒園讀大班,兒子則去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念小學。我和妻子做了簡單的分工。早上她騎電動車送兒子去上學,耗時約四十分鐘,我乘坐順路的學校校車送女兒,也需要四十分鐘。
回校后,我們便迅速投入各自的工作去,像一滴水融進渠道,來不及歇息片刻。
上學時,凌晨六點多鐘我們就起床了。但比我們起得更早的是那些跟車老師,他們六點半跟著校車去接學生到校。天空是被他們吵醒的,吵亮的。當校車“噠噠噠、咯、轟轟轟”啟動,預示著全校上下一天的工作拉開了序幕。
二十輛校車整齊地擺放,它們都劃出了固定的位置,每天拖著空蕩蕩的車身從規定的點出發,學生接完后又回到原來的位置,按部就班。下午放學后,它們載著一車的學生送回早晨乘的地點,然后又拖著空蕩蕩的車身返回學校,進入那個固定的位置,每天周而復始。
女兒和我坐在校車上,她不時張望著窗外的高樓、綠化樹、來往車輛以及行人。她還沒有完全睡醒,眼皮耷拉著。我每天都會催她,快點,快點,要上學了,快點進園門,爸爸不能送你到教室了,你自己進去,爸爸還要回去上班。背著書包的女兒回過頭來一臉稚氣地說,爸爸、爸爸,下午你一定要早點來接我喔!
好的,我會早一點來的。我只能這樣安慰她。因為我的時間也是固定了的,放學后我還要維持學生的放學秩序,待走讀生出了校門,我才能去接我的女兒回來。我們住在學校的職工宿舍,工作和生活都在學校里,倒省了奔波的麻煩。
小汽車、摩托車、電動車、自行車、卡車,它們奔跑在路上,在清晨的時光里。路把時間都耗掉了。我們的時間都被一條條道路耗掉了,車子的時間也被道路耗掉了。道路可以帶領我們去到我們想去的地方,它們一段一段交織起來,每一個岔道既是開始又是結束,開始和結束接得一點兒縫隙都沒有。它們早就鋪設好了,一動不動地守候著我們,我的生活、工作,上班、上課、下課、下班也是固定好了的,我們像一顆不起眼的螺絲釘,支撐著這座城市運轉起來。
來到某民辦學校門前那段路,一輛輛甲殼蟲般的小汽車緩緩行駛,偶有一輛車子突然旁插進來或者調頭,這段路便陷入癱瘓狀態,至少要堵上十分鐘才能通暢。在城市道路上,見縫插針的大有人在,良好的秩序頃刻被打亂了,每個人的時間都被擁堵的道路截下了一段。這個時候我的心里便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寄人籬下的人是卑微的,若被逮到未及時返校,輕則難看的臉色、責罵,重則罰上一筆也是有可能的。
原本空蕩蕩的座位被一個個學生填充起來,直到接近校車核準的乘載人數。學生背靠海綿坐墊,或者閉目養神,或者兩眼茫然地盯著窗外,看漸漸擁擠的街道,看呼嘯而來、倏忽而去的各式車子。涼颼颼的風鉆進衣領、袖口,久據炎夏的城市終于入秋了。也有大一點的學生撂下書包,從里面掏出一本教科書或者課外書,認真地看起來。他們被校車乘載著,他們的時間也被道路一點點耗掉了。人的一輩子都在趕路,都在向途經的每一條道路搶時間。當我回到學校,時間到了七點四十分。晨讀已然開始,朗朗的讀書聲從五十余間教室里飄出來,飄到大王椰、大葉榕上,又飄到空蕩蕩的操場上空往四處擴散。
除了節假日,每一天都是這樣周而復始,我也習慣了這樣的工作與生活。從起點回到原點,日子如流水一樣流走了。
我們都很孤獨
性格溫順的簡老師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他是我的同事,月薪三四千塊。當然,寒暑假領不到那么多,只有一千多元的基本工資。當然,如果被安排了寒暑假招生,另外還有一些補貼和招生獎勵。
謙恭的簡老師頭略往下低,背脊如一條拉彎的弓箭。灰白的粗布衫,淺綠色休閑褲,沾了灰塵的皮鞋頭往上翹……這些,似乎成了他的標識,市場的小商販都認得他,喊他簡老師。其實他的真名沒有多少人知道,名字也就是一個代號,跟“甲乙丙丁”差不多。
“三點一線”構成了簡老師的生存狀態——租房、學校、市場。他極少跟人聊天,靦腆的時候臉還會紅。若干年前的簡老師在老家有公職,小日子過得平淡卻也舒暢。令人喪氣的是,第一胎竟生了女兒。鑒于家族的壓力和傳統習俗的脅迫,他們夫妻偷偷商量了一個計劃:再生一個。可事情暴露了,孩子才生下不久,就被人投訴到教育局。盡管找了很多可以搭得上的關系,可惜,皆非關鍵人物,一紙公文下來還是丟了公職。校長找他談過話,說是求了人送了禮允許他繼續教書,不過方式改為“代課”。代課!他可不干,再說面子上也過不去。一個夏日炎炎的日子,簡老師拖兒帶女到了珠三角城市,擺夜市生意不好;進工廠做搬運,勞動強度太大他的身體適應不了。后來拾起了本行,順利應聘到一間民辦學校,教高年級段的數學,這一待就是幾年。他也懶得折騰換學校。
喪氣的是,老天不長眼,才幾歲的兒子居然患有癲癇病,一發作起來全身發抖、口吐白沫。經幾個老鄉推薦了偏方,隔一個月在頭皮上做針灸,取得一點點效果。又聽說貓頭鷹肉可以治本,遂七轉八轉托熟人從外省山窩里弄來這種肉,價錢貴,吃了幾次病情似乎有些好轉。但是,它仍像一個潛伏的炸彈,隨時會炸掉簡老師的希望、心血。
最后一輛淡黃色校車從街道拐進學校后門后,暮色稀薄地涂抹在空中,天邊往往還會落下一小片晚霞尚未完全消退。這時,簡老師在食堂打好飯菜,踩一輛掉漆的自行車出后門,往右拐十米再往左,折進一條又窄又長的巷子。巷子通向了魚龍混雜的肉菜市場。有時候,他會去買一些土豆、紅蘿卜、香菇熬排骨,增強小孩子的免疫力。
騎著自行車的簡老師,一條弓形的弧線從頭部起筆,依次經過肩椎、腹背最后在臀部收筆。收筆的地方連接了一塊被支楞起來的硬皮座墊。坐墊下兩個腳踏板舒緩地、嗒嗒地轉圈。如上坡路段,他用力蹬踏,前抻的身子就會搖擺起來。
買了些廉價菜,簡老師折進另一條布滿出租房的巷道——那是一條近路,通向幾公里外的出租房(如果走大路,還要繞一個大圈)。出租房里,有他的愛人和孩子。他的女兒讀三年級了,兒子沒上幼兒園小班,直接讀大班,平時由他愛人接送,小家伙黏母親。
簡老師的愛人是初中學歷,沒有正式的工作,只好去廠家接一些手工活領到出租房完成,比如裝傘架、插假花之類的。弄好了就給工廠送過去,計件,一個月結算工資。但是要交押金,三個月后押金退了,換成壓一個月的工資,說是防范那些人私自侵吞了原材料,廠家會吃啞巴虧。
有一段時間,鄉下的老母親打電話來,說是身體不好,老生病,骨頭要松散了。簡老師的手顫抖著,輕聲安慰母親,慢慢來,聽醫生的……過段時間發工資了,再寄點錢回去。那邊就嘆著氣,說她命苦,他也命苦……之后,簡老師上火了,班級里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引爆他,這顯然有失為人師表的身份。學生倒也摸準了他脾氣,錯誤犯得不大不小,全屬于“虛心接受、堅決不改”的那一類,令他疲于應付弱小或女同學的投訴。若是學生犯了大錯,那好辦多了,狠批一頓,再請家長到校數落一番,效果往往會好一陣,但是,后來學生又重蹈覆轍。壞習慣像一顆毒瘤,不割掉很難根治的,他暗道。
夜深人靜之時,簡老師偶爾會寫一點小文章,也不投稿,純屬自娛自樂、孤芳白賞。他覺得每個人都很孤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扇密不透風的門專屬自己,門內擺放著一盞燈,外人極難窺見其中是否光亮、幽暗,抑或下著淅瀝的雨。
孤獨的人并不可恥。
一只小鳥的恐懼和憂傷
沒有人在意一只飛在城市低空里的小小鳥是如何卑微,如何膽戰心驚地度日,一粒塵埃、一棵小草,抑或一只躲在陰暗角落里的草蟲,都是它的化身。
就像誰也沒有料到消失月余的門衛——小賴,竟然傳來令人揪心的消息。起初,我們習慣性地以為他換了更好的工作——打工一族都是同病相憐的,總祝福對方能早日脫離苦海,泅渡上了岸,迎向一片蔥蘢而散發清香的青草地,可以歇息、享受。然而,我們的幻想在一個夜晚被擊得支離破碎了。肝腹水,一個聽起來多么令人恐懼且張牙舞爪的名詞。它暴發的威力可不小,令人恐懼、不安、難受,人類的肉體根本無法抵抗。究竟它是何時神不知鬼不覺地攻進小賴內臟的城堡,然后隱秘地潛伏下來伺機發力?在病魔的面前,我們是那么脆弱、無奈。
時光回溯到二十多年前,散發著青春氣息的小賴從鄉下老家來到珠三角城市打工,二十多年后,他孤身一人揣著癌癥回家了,回到兩鬢白發的父母身旁。那相逢的場面怕是欲哭無淚的四目相對了。擊倒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往往不是病本身,而是傳統的信念。好好活著是信念,結婚生子是信念,孝順是信念,黑發人送白發人也是信念……如果反過來,便是信念斷了,猶如一支燃燒的蠟燭突然被吹滅,一盞亮堂的燈光倏地斷了電……
四十多歲了,身患重病的小賴還沒有結婚、成家。幾年前聽說談了一個,后來知道他是保安后感情就漸漸無疾而終了。也陸陸續續收到好心人的介紹,大多因為職業的關系、羞澀的存款沒了下文。對于普通人而言,年紀越來越大,作為伴侶的價值就似乎越來越低,鄭智化曾經唱道:“過去我選擇別人,現在別人選擇我。”飽含的辛酸與無奈非親身體驗是很難理解的。小賴的家人也催他,年年催,月月催,天天催,催來催去,他被催出了恐懼癥和焦慮癥,四十歲之后,每年臘月,“回家”這個詞匯已讓他滿目惆悵、悲涼。于是,學校休年假,他主動申請值班、加班,目的就是躲開雙親期盼而憂傷的眼神。在萬家團圓的春節,他孤零零地守著學校的大門,空蕩蕩的校園讓他的心房也空蕩蕩的。外面,冷風用力撕扯著街道、樹木,仿佛也同時撕扯著他的心……
一棟陳舊的樓房,顯然滿足不了一百多名教職員工人住,作為保安的小賴,被安排在旁邊的鐵皮房宿舍。鐵皮房蜷縮于區府的外圍墻下,一場雨水降臨,房頂就會響起“噼里啪啦”機關槍般的雨點聲。雨點砸鐵皮房的時候特別興奮,力度特別大,它們要在城市里發出自己的聲音,要告訴下面的人,它們不是老天拋棄的精靈。它要給詩人送一首詩,要給失眠的人一些騷擾,或者激起一點共鳴。可是,初中畢業的小賴,不喜歡雨水粗暴的方式,也不喜歡寧靜的夜被雨水搗亂。他向我傾訴苦惱,可我根本幫不上忙。后來,每次見他,他就無聲地搖頭苦笑。我亦回之以愛莫能助的苦笑,事實上我居住的四樓也好不到哪里去,陽臺邊已經缺了一個角,裸露出來的磚塊、細碎水泥偶爾還會往下掉。
朋友們來找我玩,就聚集在學校附近的農家菜館。偶爾,我也會叫上小賴,因為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題。一般是先上酒,冰涼的百威啤酒,在凳角上用手掌一拍,哧,白沫從瓶口涌出來往外冒、泄。在酒精的麻痹與亢奮中我們呵護著友誼的溫度與恒度。酒精充分激發了年輕的荷爾蒙,接近二兩的杯子倒盡、放下、灌滿,如此循環往復,只為哥們間的義氣和難于表述卻心靈相通的苦楚。
相比于多愁善感經常喝醉的我,小賴酒桌上的表現還是較為理智的,他喝不得酒,一點點酒精就讓他眼珠泛紅,臉色顯豬肝色,然后羞怯地望著我笑。我也不好勉強,只顧與朋友推杯換盞。酒精未徹底麻醉記憶之前我的頭腦還清醒,晃動的眼神盯著一堆橫七豎八的空酒瓶,眼眶抑制不住地滾出了幾行淚,很快滑到我的兩腮,咸咸的,熱乎乎的,我仿佛覺得它們是從我的心里滾落出來,仍保留著我的傷痛與體溫。依稀記得那位膚色白皙的老板娘過來勸慰了很多話,可是現在一句也回憶不起來。朋友們在一旁勸慰、自言自語,有的高聲吆喝著,有的緊緊摟住我肩膀,像摟住茫茫人海中失散多年的兄弟。感同身受的他們也似乎找到了久違的宣泄的窗口,借助酒精祭奠青春以及其他。不知過了多久,我沉重的肉體悄然下滑至桌底,像一堆爛泥似的。身后挪動的椅子吱吱響著,然后,它頂住了某扇墻,朋友們紛紛過來扛住滑倒的我,之后,我的一段記憶就消失了……
多年后,我身體的一些部件突然亮起了紅燈,醫生給予了嚴肅的警告。
我終于嘗到了壓抑之后放縱的代價。
但是,比我付出更大代價的是小賴——其實他極少喝酒。
誰也沒有想到,從醫院查出肝腹水后兩個月后,小賴在老家悄然去世……
誰會理解一只小鳥的恐懼和憂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