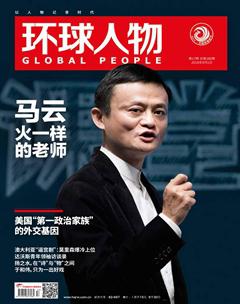用“世界語”講述中國故事
尹潔 凌云 馮璐 李茹玉 劉琳琳
世界經濟論壇誕生于風景如畫的瑞士小鎮達沃斯,因此又稱達沃斯論壇。每年論壇都會評選一屆“全球青年領袖”,入選者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行業,但都是在各自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精英。
“全球青年領袖項目從2005年開始運作,已經13年了。”世界經濟論壇大中國區首席代表艾德維對《環球人物》記者說,“近5年來,中國入選者的數量每年都創下新高,今年達到11人。過去,很多出色的中國年輕人只在國內有知名度,而現在,他們在全球的曝光度越來越高。”
“全球青年領袖”項目有句口號:領袖意味著奉獻而非索取。艾德維用中文告訴記者,今天的中國年輕人追求的不僅是“致富光榮”,更是“行善以積功”,不僅本職工作做得好,還在盡力影響社會。
“比如萬科集團高級副總裁劉肖,正在推動企業建設一些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的項目,以減少建筑物的碳排放。再如來自中央電視臺的李斯璇,她是一名優秀的財經節目主持人,同時還積極參與健身項目,推廣和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
談到“全球青年領袖”的入選標準,艾德維表示,論壇尋找的大多是30多歲、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士。“但是,我們并不想選擇那些只在人生的一個方面取得成功者,特別是那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我們尋找的是那些用自己的成功回饋社會的人。”
每年的“全球青年領袖”評選并沒有專門的主題,但在艾德維看來,這個項目有個潛在的主題,就是幫助他們成為更好的領導者,從而給世界帶來更大的變化。“我們會給他們提供各種機會,包括領導力培訓和各種活動,他們也會彼此合作,發起新的倡議。”
來中國工作前,艾德維從2007年到2015年一直負責“全球青年領袖”項目,擔任大中國區首席代表后,他依然關注這個項目在中國的發展。“青年領袖們的能量、激情、積極向上總是讓我感到驚喜。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努力、很忙碌,卻每每驚詫于他們能在那么緊張的日程中,還擠出時間做更多的事情。”
很多青年領袖在海外接受教育,在中國開展事業。艾德維對記者闡述了他觀察到的一個趨勢:10年前,海外留學的青年精英普遍認為最好的機會在西方,并設法留在那里;現在,他們更傾向于在西方學習,獲得頂尖能力和全球視野,然后回到中國發展。
“這些有著全球視野的青年領導者,非常樂意回報自己的國家,幫助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已經找到了連接東西方世界的渠道,很多年輕科學家回國后會和美國學術機構保持合作,這與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一致的。”
艾德維認為,經過40年的改革歷程,中國的開放勢頭有增無減。他引述中國領導人的話說,中國的開放以及與世界的合作都“不可逆轉”,“其他國家也許有起起伏伏,但中國在政策和愿景方面始終是一致的”。
劉肖:我是危機感很重而焦慮感很輕的人
今年1月,劉肖收到了一封從瑞士發來的郵件,通知他已入選“達沃斯全球青年領袖”的消息。
“起初有點意外,然后覺得能跟世界‘鏈接這件事挺好的。”在位于北京萬科中心的辦公室里,劉肖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除了是萬科集團高級副總裁,他也是萬科旗下家裝公司萬鏈的董事長,“鏈接”這個詞對他而言不僅是行業之間的,也是中國與世界之間的。
在劉肖看來,很多行業的興衰就像一輪又一輪的時尚潮流,或許10年、或許20年,而房地產的潮流期相對更長一些,至少在中國,過去30年中,它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在杭州工作過,清末的胡雪巖曾經在那里經營過很多產業,但延續至今的只有他創立的胡慶余堂。從歷史的角度看,中醫和宗教都是延續幾千年的潮流,房地產與它們相比還是一個新興的產業。”
幾十年中,房子在中國人的生活里從必需品變成投資品,幾乎與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步,而實踐最終證明,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買房依然要回歸“住”的本質。
“越是滿足基本需求的,越是服務于普通大眾的,越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生命力越長。”劉肖說。
當中國人均住房面積達到40平方米后,房地產行業如火如荼的時代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社會的高速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考慮未來如何養老的問題,這也為房地產企業創造了新的機遇。
劉肖告訴記者,萬科的養老業務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09年到2012年,還是以地產為主的思路,如開發養老住宅之類;第二個階段是2012年以后,主要是做養老服務,包括醫療護理等,“這個產業鏈的核心是給養老社區的客戶提供各種服務”。
在中國,已經付諸實踐的養老服務產業有幾種模式,比如學院式養老,讓老人去進修、讀書,再如度假式養老,在三亞等風景名勝地開發一些項目。但在劉肖看來,大部分老年人都希望生活方式盡可能少地改變,所以萬科采取的是“鄰里式”養老模式,養老社區都在城市里,讓客戶生活在熟悉的環境中。此外,還有配套的護理服務,不同社區有數量不等的護理床位。
劉肖認為,中國養老產業的黃金時代遠未到來。“在我們印象中,60歲以上的人就可以養老了,其實我們養老社區的住戶平均年齡是80歲,這才是一個有剛性需要的年齡。目前在這個年紀的中國老人,并不是最有支付能力的群體,也不是人口數量最多的。真正龐大的群體是‘60后‘70后,而到他們80歲還有二三十年,獨生子女一代則更加遙遠。今天的養老產業都是在這個大時代到來之前做的布局。”
從這個層面說,今天的人們很難預測養老產業未來的發展軌跡。劉肖相信,養老行業一定會誕生千億級、萬億級的企業,“但它究竟來自地產業還是服務業,甚至是保險業,都很難說。20年后的事言之尚早,我們能做的只是面對今天的需求,嘗試著提供一些服務。”
這種不確定性讓未來充滿挑戰,也充滿希望。事實上,劉肖自己的職業生涯也經歷了重新選擇的過程。2003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專業碩士畢業,進入麥肯錫咨詢公司,3年后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攻讀MBA,畢業回國后加盟萬科。
“人的生命短暫,你無法選擇自己所處的時代,只能選擇如何去面對。如果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發展比中國明朝更有希望。而現在,世界發展的時鐘在中國。2008年我回國的時候,中國的時鐘在地產行業,我看好萬科,所以就來了。”
1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時鐘或許已經不在地產業了,但新的機遇仍在孕育著。主攻家裝行業的萬鏈,就是萬科新的產業布局之一。此外,還有近來頗受關注的長租公寓業務,也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
“我們有個口號,‘給年輕人一個有家的城市。年輕人指的是所有在城市奮斗、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青年群體。我們有一種情懷,就是不僅能為他們提供一些性價比高的住處,也能把萬科倡導的生活方式、城市資源、服務設施與他們共享,比如一家餐廳、一家咖啡館。我們確實是有這個初心的。”
劉肖把萬科的客戶定位為“普通人”,他希望企業能服務于中國最廣大的群體,“我們的客戶越是普通人,我們的生意空間就越大”。
“我是一個危機感很重而焦慮感很輕的人。”劉肖說,“我經常覺得有危機,但不太焦慮。”危機感可能來自周圍一切新的知識、新的力量,無論是科技的發展還是商業模式的變化,這讓劉肖保持警覺,但更重要的是把問題解決掉。
“把壓力化成行動,找到解決的辦法,焦慮感就會減少。當然,確實有很難突破的情況,那么等待也是一種解決辦法。有些事情是需要時機的,等待經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果你是做金融的,堅持在行業周期的高點去投資,那注定是要賠錢的,地產業也是。學會等待很重要,克制住你內心的焦慮,把等待看成一種解決問題的舉措,希望可能就在明天。”
李斯璇:我在中國與世界聯動
自從加入央視財經頻道,李斯璇采訪報道達沃斯冬季和夏季論壇已經有三四年了,再加上歷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G20峰會等,她采訪了很多國際政要和世界級的企業家。
網絡上流傳著李斯璇采訪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時的一組對話截圖:當庫克說自己工作勤奮、一天只睡4小時的時候,李斯璇調侃“那您或許得戴兩只蘋果手表吧,因為一只表只能續航18小時”。
英語的無障礙溝通是李斯璇一個重要的采訪優勢。從國內高中畢業后,她經過激烈的留學申請競爭,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理學院,主修經濟和數學專業。本科畢業后,李斯璇先后就職于華爾街的投行和私募基金公司。多年的海外求學和工作經歷讓她不僅能說一口地道英語,更能用西方思維和邏輯表達自己的觀點。
另一個優勢是作為央視雙語節目主持人、財經評論員所必須具備的專業素質與人生閱歷。在這方面,李斯璇比同齡人起步更早。作為一個成都妹子,她從小在四川電視臺當節目主持人,中學時參加央視“新苗杯”中學生電視主持人大賽、“希望之星”英語大賽,拿過不少獎項。李斯璇也擅長體育運動,曾在非洲沙漠里負重越野250公里,甚至挑戰過鐵人三項。業余時間,她還積極參與和推廣健康公益項目。
“我的好奇心特別旺盛,感興趣的事特別多,不管什么總想學一學、試一試。”李斯璇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但比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你得堅持下去,不能淺嘗輒止。”
在美國讀書時,她大二進入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實習,并拿到了回聘證書;大三暑假收到華爾街多家投資銀行的全職聘書,最后選擇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私募基金部門。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剛剛畢業的李斯璇經受了磨煉。“那幾年是一段很好的經歷,讓我迅速學習和成長,為日后做媒體工作積累了不少經驗。”
離開投行后,李斯璇進入杠桿收購鼻祖美國KKR私募基金公司,從事投資業務。“當時公司在全球只有110名員工,卻管理著550億美元的資金。我經常早上飛出去,晚上飛回來,有時凌晨三四點還在整理資料。老板要求極其嚴苛,文件里多一個空格、字體不對、頁碼錯誤都要修改,工作壓力很大。那段時間讓我養成了做事細致的習慣,現在回頭看,也是在其他地方難以學到的。”
在金融業工作3年后,有獵頭聯系李斯璇,問她是否有意加盟美國財經媒體CNBC電視臺,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試鏡,李斯璇成為CNBC亞太總部的首位中英文雙語主持人,于是她又在亞太總部所在地新加坡工作了3年。
“在CNBC期間,我與央視財經頻道有很多接觸的機會。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我一方面感到國內機會更多,另一方面覺得央視這個平臺很好,能接觸很多全球性議題,視野可以覆蓋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相比之下,CNBC的報道范圍分成不同區域,如北美、亞太、歐洲等。所以在2014年底,當央視這邊問我是否愿意加入財經頻道時,我就答應了。”
回國發展后,李斯璇與世界的聯動果然更加頻繁、廣泛了。除了固定的財經新聞節目外,她也經常出現在國際會議的現場,與各國政要、頂級企業家面對面。
有一次在秘魯報道國際會議,當天工作結束后,李斯璇穿著拖鞋走在會場外的街上,突然看到秘魯的前領導人,她立刻跟攝影師一起過去,自我介紹并請求采訪,對方愉快地接受了。“這種突然出現的機會非常考驗記者的應變能力,因為你得迅速地跟他聊起來。”
一次在達沃斯冬季論壇上,美國前勞工部長、現交通部長趙小蘭恰好坐在了李斯璇旁邊。“他們之前并沒有安排媒體采訪環節,但既然她坐我旁邊了,我就要抓住這個機會。”在與李斯璇聊了一會天后,趙小蘭答應了央視財經頻道的獨家專訪邀請。
“其實我們交談的前10分鐘都是她在問我問題,包括我的成長經歷、大學生活、工作情況。她在通過一些細節了解你,認為值得信任,才會接受你的獨家專訪。”這種現場碰到的采訪機會,需要記者快速反應的能力。
專訪庫克時,李斯璇盡量在短時間內營造一種舒適的對話氛圍。“如果他感到舒服、習慣,就會對記者放松下來,才能談更多交心的話題。雖然我對他有了解,但當他覺得你很陌生時,是不愿意講心里話的。”
離開美國7年,李斯璇感覺中美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雙向化,中國企業和企業家也越來越愿意走出國門,與世界溝通。
“無論是冬季還是夏季達沃斯論壇,近幾年中國企業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能主動走上國際舞臺,讓世界看到我們現在的情況,同時也積極和外界交流,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發展。”
這種溝通意愿是如此強烈,李斯璇希望以一名媒體人的視角,用世界都能聽懂的語言將其呈現出來,把中國的故事告訴世界,也把世界的觀點帶給中國。
站在全球化的新十字路口,李斯璇感到媒體人的責任。“就我個人的體會,對于中國的日益強大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不光是世界,包括中國自己都需要積極面對、快速適應。無論全球化是否有暫時的逆風,整體的合作趨勢是改變不了的,也很難逆轉。交流、包容、理解、融合,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也需要一些時間。其實溝通的方式并不復雜,只要來中國走一走看一看,刻板的觀念可能就會改變。”
何正德,穿梭于東西方的“富四代”
和曾祖父、香港慈善家何英杰一樣,何正德在外界不事張揚、低調謙遜,遍尋網絡也找不到過多信息,但對于自認為有意義的事業,他們都充滿了熱情與執著。
30歲出頭時,白手起家的何英杰進軍煙草業,在上海創辦了香煙品牌“高樂”,成為富甲一方的超級富豪。同樣在30多歲的年紀,何正德在美國硅谷創立了一家名為S28的早期風險投資基金公司,促進了高科技創投界的跨國交流,他也由于這方面的貢獻被評為2018達沃斯“全球青年領袖”。
“如果不是繼承了曾祖父身上的精神品質,我不會有機會站在‘全球青年領袖的領獎臺上。”何正德說,“除了勇于創新和善待他人,他還教會何家后代勤奮上進,一切美好都要靠勤奮來創造。”
在何正德看來,不斷進取的基因深深流淌在何家人的骨血里。他從小就看到父親何柱國一心撲在工作上,經常旁聽父親的金融會議,自己也刻苦讀書,考入美國斯坦福大學,畢業后曾在美國高盛集團、何氏家族企業星島集團工作。
作為旁人眼中的富家子弟,何正德并沒有滿足于現狀,而是不斷涉足新領域。他分別于2009年和2015年創辦了Harbor Pacific資本和S28資本,專注于為美國及亞洲的新興科技公司提供早期成長階段的資本,利潤頗豐。目前,S28投資了數字健康、人工智能、房地產建設、無人機等與大數據和云計算軟件密切相關的項目,以1.7億美元(約合11.5億元人民幣)的規模成為硅谷數一數二的風投公司。
中國俗話說,富不過三代。但到何正德這一代,何家已經富到第四代了。如今37歲的何正德依然保持著吃苦耐勞和冒險精神,并言傳身教給自己的下一代,希望后代也能懂得個人奮斗的意義。
盡管出生在美國,何正德卻自稱深深扎根于中國。受祖輩教育和家風的影響,他頭腦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東方傳統觀念,比如“奮斗不僅是為了自己成功,更是為了周圍人和下一代,乃至整個社會”。
何正德堅信,技術革新會提高生產力和推動社會進步,致力于為具有實驗性和開拓性的科技力量尋找廣闊的商業市場。以他投資的Airspace為例,該項目研發出一套新一代無人機保安系統,利用人工智能、光學雷達等技術辨識及追蹤目標,攔截惡意無人機。“近幾年無人機熱潮成風,不論是為航拍或競速,都帶來很多社會和經濟上的雙重效益。但若無人機遭惡意操控,入侵政府大樓、公共交通樞紐等上空,則會構成嚴重安全問題,如近期發生在南美洲委內瑞拉的恐襲事件。我們希望科技發展會對世界有正面的影響,讓社會更安全及和諧。”何正德說。
由于工作性質的緣故,何正德頻繁往返于亞洲和美國。平均算下來,過去10年間,他在亞洲和美國的時間幾乎一樣多。不過,這樣的狀態讓何正德感到充實,“幾乎每天都能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聰明人接觸,傾聽他們改善世界的愿景和計劃”。
擁有東西方雙重教育背景的何正德,對于兩者的差異和融合也感觸頗深。他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積攢的人脈和資源,將美國硅谷的創新精神帶入亞洲,同時把亞洲先進的商業模式推介到美國,并盡最大努力讓兩者結合在一起。何正德也把聯結跨國創投資源當成自己的使命:“我有責任建立跨越國家邊界的橋梁,以此連接各方資源和人才,致力于尋找為世界創造更多價值的新方法。”
在何正德看來,亞洲和美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各有各的合理之處,很多地方值得合作、取長補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前美國硅谷的頂級工程師里有很多亞裔移民,這些優秀的國際人才本身就是美國科技創業成功的必要環節。
“中國的創新商業項目中有很多極具創意的商業模式,比如微信,不僅是交流平臺,也是支付平臺,消費者參與的深度無與倫比,這比國外同類社交軟件要先進很多。此外,中國企業創新的速度也令全世界矚目。”何正德說,“但在產品設計上,美國硅谷的創業者值得學習。人才是科技創業的關鍵,這些到硅谷的創業者們在產品的細節雕琢和質量把控上十分講究,基本都是奔著一個長遠目標去努力的,而不是短期成功。”
眼下,最令何正德著急的是當今美國政府不斷升級的貿易保護主義,他希望這種狀態盡快結束。“全球化至關重要,世界上很多難題只有通過各國協作才能解決,比如環境保護,希望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只是暫時的。”
對于未來,何正德的最大感觸是“時間非常緊迫,有太多機會需要及時把握”,而他能做的,就是盡量和那些與他有相同激情、價值觀,并有遠大抱負的人接觸,碰撞出更多的靈感和正能量。“我為自己成為‘全球青年領袖的一員深感榮幸,這也意味著,我愿意和其他獲獎者一起,塑造更好的未來世界。”何正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