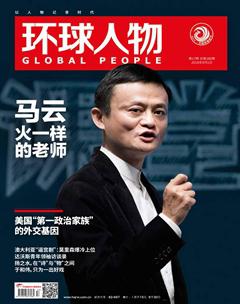三代酒師用工匠精神釀酒中珍品
肖科
黔北明珠遵義,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也有著醬香美酒的芬芳。從成義燒坊走出來的釀酒人,帶著千年茅臺酒文化的傳承,懷揣著讓更多人喝上高品質醬香酒的信念,堅守著敬業、精益、專注、創新的工匠精神,代代傳承,不斷創新。珍酒也因其所體現的工匠精神而受到青睞。
傳承工匠精神,是傳承對自然的尊重和敬畏
先講個小故事。1975年,由國家科委領銜、貴州省科委具體組織實施,探索在茅臺鎮之外釀造茅臺酒的可能性,最終選址在遵義北郊董公寺鎮的石子鋪,命名為“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基地”——這就是今天珍酒廠的發端。
醬香酒釀妥后,要經過至少5年的自然儲存才能老熟。時間是釀造茅臺酒最重要的成本之一,為解決這個難題,來自國家原子能研究所、四川大學、貴州農學院等單位的科學家們行動起來,充分發揮想象力,對酒用紫外線照射,用中子束轟擊,放在烈日下長時間暴曬……嘗試了各種方法后得出結論——這些都沒用。要使醬酒老熟,還得老老實實儲存5年。
科學家走了,這個故事留了下來,讓人回味著珍酒人代代傳承的工匠精神究竟是什么。一位財經作家曾說,工匠精神是對中國兩千多年工匠道統的迭代式傳承與更新,這其中,就包括了對自然的尊重乃至敬畏。
珍酒的第一代酒師、93歲的張支云老人說過一則軼事。除非特意調高或者調低酒度,今天的醬香酒一般都是53度。為什么不取個整數呢?原來,在張支云的時代,沒有酒度表,沒有溫度計,沒有實驗室,一切全憑“腳踢手摸嘴巴嘗”。當年老酒師們并不知道自己釀造的醬香酒是多少度。有了酒度表后,往酒缸里面一拋一看,“嘿,53度!”——大自然為美酒設定了標準。
張支云的弟子、珍酒的第二代酒師、珍酒廠主管生產的副總經理王忠漢曾經和我們一起坐在第一車間,也就是1975年老酒師們試制茅臺的車間。他的身邊堆積發酵的糟醅正在靜靜躺著“做功夫”。我們問他:“你聽得見嗎?”王忠漢連連搖頭:“我聽不見我聽不見,他們那些‘高手才聽得見!”他又補充了一句:“不過我能感覺得到。”——他傾聽的是大自然用神奇之手為酒創造生命的音符。
王忠漢的弟子、珍酒的第三代酒師、珍酒廠主管技術的副總經理雷安亮說,醬香酒是人與自然“合作”的產物,其釀造本身有很多不可控的環節,然而對于時令、溫度、糧食、水文等生產醬香酒的要素,在現在的技術條件下,是可以被認知的,釀酒人要充分與環境互動,與自然互動。醬香酒是天成的,然而人的智慧能夠與自然合作,在雙方的配合之下,滴滴珍酒,生動產生。
一位釀酒人說,對于大部分行業而言,只有產品而沒有作品,標準化的生產也不允許個性化的作品產生,流水線不允許“創造性”,每一個環節的細微誤差都可能會導致全線停擺。但標準化的前提是我們能夠掌握產品生產的全部技術密碼,并將之分解為標準動作、翻譯成機器語言。直到今天,醬香酒釀造的技術秘密還不能被現代科學所全部破解。它仍是大自然的秘密。正因為如此,醬香酒的釀造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每個人對醬香酒的理解都不一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釀造環境甚至不同的心情之下,得到的產品都是不一樣的。每一瓶醬香酒都是一件“作品”,水平高的,就成了“藝術品”。
從張支云到王忠漢再到雷安亮,師徒代代傳承的工匠精神,首先就是對自然的尊崇和敬畏。
傳承工匠精神,也是傳承精益和專注的職人精神
工匠精神以匠心為本。有沒有工匠精神,關鍵是看有沒有一顆安于默默無聞、追求卓越的匠心,堅守初心、執著專注,秉持赤子之心,摒棄浮躁喧囂,坐得住,能吃苦,做得好。從古時魯班雕木成凰、庖丁解牛,到今日珍酒的一代代酒師守住艱辛、釀造香醇,工匠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個人風格的酒師身上代代傳承,這也是珍酒之所以為珍的緣由。
張支云是老一代的工匠,“天生的釀酒人”。他住在遵義老城區湘江河邊,身材高大,性格爽朗,至今每天還要喝上二兩酒。雖已高齡,卻耳聰目明,說話間不時呵呵大笑。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他的身上有一種守得住艱辛、不怕吃苦的精神。
新中國成立前,茅臺地區最大的3家燒坊是成義、恒興、榮和,成義燒坊資格最老、名氣最大。張支云老家在仁懷縣二合鎮,離茅臺有幾十公里,離遵義有100多公里。8歲時他父母雙亡。12歲時,偶然遇到了成義燒坊的掌柜(相當于總經理)薛相臣。張支云的雙手皸裂縱橫,薛相臣卻很有興趣地反復翻看,還特意讓他解開衣裳露出肩膀——肩膀上老繭叢生。薛相臣高興地說:“這個娃兒我要了,帶他去酒廠學釀酒”——代表吃苦耐勞的老繭,打開了他走進釀酒行業的大門。
和師傅相比,王忠漢的文化程度高得多。他是科班出身,小學時跳過級,一直成績優異,1986年高中畢業后考上貴州省第一輕工業學校。在那個時代,考上中專的難度不亞于今天考上“一本”。但讓他脫穎而出的也是吃苦精神。
中專畢業后,王忠漢被分配到珍酒廠。作為科班畢業的知識分子,通常會分到車間實習后安排在行政或者管理部門,王忠漢卻在實習結束后到車間當了操作工。他的工作用4個字總結,叫“翻掀打造”。“造”是川貴土話,意思是把不同的小顆粒混合在一起。體重才100來斤的王忠漢,每天用鐵锨把高粱、小麥(曲藥)、糠殼混合在一起,幾個月下來,滿手打起大血泡,大腿上都磨出了老繭殼——蒸煮過的高粱小麥是很沉的,鐵锨本身也有5斤左右,一般人單靠手臂力量根本玩不轉,何況瘦弱的王忠漢,必須要借大腿的力量。
王忠漢說自己“內向老實”。他不聲不響地在車間干了1年多。有一天,時任珍酒廠總酒師的張支云下車間指導工作,認定“這個娃兒老實肯干”,把他帶在身邊。多年過去,我們再問張支云選擇王忠漢的原因,他還是淡淡的四個字“老實肯干。”
第三代酒師雷安亮是苗族,身材高大,氣度儒雅。比起師傅王忠漢,他的文化水平又上了個臺階。他畢業于沈陽農業大學食品科學專業,是食品生物技術研究生,主修釀酒生物技術。雷安亮的導師是研究釀酒的前輩,求學期間,他已參與了和釀酒相關的國家級科研課題。但他能有今天的成績,靠的還是傳承了工匠精神中的“吃苦”。
2009年,雷安亮加盟金東集團,被安排在集團旗下的湖南邵陽湘窖酒業做技術工作。這是個年產量6000多噸、年產值18億元的大企業。但那時,他在車間一天活干下來,滿身都是窖泥味道。下班后擠上公交車,發現自己身邊總是慢慢就沒人了,很是寬敞。“驚喜”過后他才想清楚,人們是嫌他身上的窖泥味道而故意避開他。對一個帥小伙子來說,這打擊確實有點沉重。
雷安亮又發現,全國大部分著名酒企都在高山深谷、偏遠鄉鎮。釀酒需要環境,在通衢大道是沒法釀出好酒的,想過體面光鮮的生活,就不能加入釀酒行業。原來,所有的釀酒人都很辛苦。
雷安亮想清楚了,他愿意吃苦,以傳承酒文化的輝煌。他沉下了心,兩年后出任湘窖酒業技術主管。那時,和他同期進廠的二十來名高材生,只剩下他一人。2014年,雷安亮調到珍酒廠擔任技術中心的常務副主任。2015年,他升任珍酒副總經理。
從張支云皸裂的雙手,到王忠漢長了老繭的雙腿,再到雷安亮滿身的窖泥味,珍酒傳承的不畏艱辛的工匠精神,就像醬香酒一樣純正、厚樸。
傳承工匠精神,更是傳承出精品、出人才的追求
踐行工匠精神,就是以精品為重,以人才為重。生產優質的產品,靠的是技藝超群、敬業奉獻的高技能人才。而這種敬業精神,在一代代的珍酒酒師身上也不斷傳承。
張支云18歲進燒坊,拜成義燒坊老酒師鄭應才為師。80多歲的鄭應才沒有兒子,張支云還拜他為“保爺(干爹)”。鄭老爺子很嚴。張支云說,從入門到學成,自己至少挨過師父3記耳光,腦門上挨的爆栗和屁股上挨的煙桿更是數不清。鄭應才做了根篾片掛在手邊,專門用來打張支云屁股,“不打你你記不住”。但就是這樣的嚴格,讓張支云掌握了核心的釀酒技術。他舉過一個例子:第一輪的酒有生澀味,要少出一點;第二輪酒有酸味;第三輪酒要酸酸甜甜的,像“栽秧泡兒(覆盆子)”味,這個就是好酒了,稱“大回酒”。但沒有第一輪、第二輪酒,也調不出好酒來。
敬業,就能迅速成才。1948年,張支云出任成義燒坊副酒師(相當于副總工程師)。當時鄭應才已不管具體的事,張支云是事實上的負責人。上世紀50年代初,成義、恒興、榮和三個燒坊組成了茅臺酒廠,張支云加入茅臺酒廠,并先后擔任車間主任、工會主席等職。“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項目開始后,點名要張支云去當酒師。1978年,張支云出任珍酒廠副廠長、總酒師,負責全廠制曲、釀酒、包裝等工作。他有句口頭禪“搞球些啥子!”(貴州土話,意指“你們干的這叫什么事!”)就在接連的“搞球些啥子”聲中,好酒釀成了。
1981年,國務院領導來視察“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項目,張支云以一杯茅臺、一杯試制酒請他品鑒。領導品后開玩笑說:“你是酒師,我是百姓,你這是考我呢!我品不出。”1985年,酒業泰斗周恒剛領銜的鑒定委員會給珍酒打出了93.2的高分,認為珍酒“接近市售茅臺酒水平”。
王忠漢同樣傳承了這種刻苦精神。跟隨張支云學習幾年,他把釀酒的技術環節基本上都摸清了。1992年,他被提拔為車間主任,當時年僅23歲,是7個車間主任中最年輕的。此后,他從生產部部長到主管生產的副總經理,沒離開過生產業務。
王忠漢說,珍酒的釀造可概括為“12789”。“1”是生產一個周期需1年,“2”是每個周期2次投糧,“7”是7次取酒,“8”是8次發酵,“9”是9次蒸煮。所謂2次投糧,是指第一次投糧(行話叫“下沙”)時投一半的糧食。將糧食蒸好后拌上酒曲,攤晾完成下到窖坑里發酵一個月,然后取出再加另一半糧食,經同樣程序后發酵一個月,取出再蒸煮,就開始有酒了。從第二次加糧后,整個釀酒季中不再加一粒新糧食,但蒸煮、攤晾、堆積發酵、窖池發酵過程要重復9次,需耗時一年。
第二次加入糧食再蒸煮發酵后叫糟醅。在生產過程中,潤糧水分的控制非常重要,必須控制在50%到51%之間,過高或過低都會對酒的產量和質量造成較大影響。這1個百分點的誤差如何判斷?王忠漢說“用眼睛看、用手捏、用嘴巴嘗”。他抓起一把糟醅在手眼口之間來回倒騰、品味,那真是高手風范、工匠功夫,拿捏在分寸之間。
而7次取酒中每一次得到的酒,酒體是不一樣的。在同一次取出的酒,酒體和品級也是不一樣的。在酒體上分為“醬香、窖底、醇甜”,等級上分為一等和二等。實際上每一輪次釀完,得到的是6種酒體,然后裝入陶壇儲存。品酒師會對陶壇中儲存的不同輪次、不同酒體不同年份的酒進行反復品評勾調,直到達到品酒師的口感要求為止,儲存5年以上的酒才有參加成品酒的資格,按照不同的產品要求再將不同年份、不同輪次、不同酒體的酒相互勾調,才是成品珍酒。
雷安亮到珍酒廠工作之前,已經在湘窖掌握了濃香酒的釀造技術。當時,集團人力資源部領導找他談話說:“你有沒有勇氣挑戰醬香酒?醬香酒比濃香酒復雜得多,也困難得多。如果你把醬香酒整明白了,你的釀酒技術體系將渾然一體,更加完整。”雷安亮接受了挑戰。半年以后,雷安亮開始跟隨王忠漢具體學習醬香酒的釀造技術,進步很快。正如那位領導所說,1+1的結合,讓他的釀酒技術達到了新的高度。
傳承,也離不開創新。王忠漢說,目前,利用現代科技已可對醬香型白酒的生產進行事后檢驗,發現問題可以在下一季生產中改進。“這比張老師那個時代全憑個人經驗和悟性進步多了”。
雷安亮則在釀酒技術的創新發展上取得新的成就。遵義跟茅臺鎮的氣候不同,海拔也不一樣,雷安亮團隊根據遵義的實際氣候環境條件,總結了珍酒40多年的生產數據,完成了珍酒釀造工藝定型,近年來產量、質量都穩中有升。珍酒釀制技藝也成功入選遵義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為了更好地追求對珍酒品質的極致體驗,雷安亮還帶著他的團隊開展了酒體儲存對口感變化的研究。他說:“在研究成果基礎上,我們寧愿增加儲存成本,也要創新采用‘瓶儲工藝,這樣產品會更加柔和、老熟、怡人。我們還投入資金對白酒風味物質的來源進行研究,并申報了省級科技項目《產白酒醇甜風味物質微生物篩選及關鍵技術研究》,打造‘珍十五醬香柔雅、甘甜爽口的口感風格。”
珍酒被稱為“酒中珍品”,工匠精神則是國之瑰寶。珍酒人說,作為國酒一脈,他們會把工匠精神永遠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