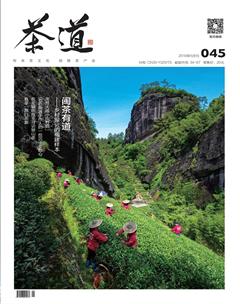90后陶器手作人的一份沉寧安穩心
張小新



認識章垚的作品,是從圖片開始的。然而,當見到實物后,還是被器物的強大張力折服,器物整體所傳達的感動一瞬間沖擊心靈。
第一次覺得,圖片對器物的表現如此乏力。
黑和褐色是章垚陶藝作品的主色調。黑,有著無法言說的神秘,和包藏一切的氣場。正如木心說言:黑保守嘛?黑是攻擊性的,在絕望中求永生。類似古銅的褐色,是歷經世事的老者,是櫛風沐雨的古樹,蒼勁而有力。單純樸素的陶器,只遠遠地眺望,肅穆和沉靜已撲面而來。
作品,傳遞著它身為一個器皿的品格和創作者的所思。所以,作品一定不會孤立于作者而單獨存在。作者的喜怒哀樂,喜好與偏執,經歷和生活的點滴都會記錄在冊。
見到章垚后,對這話有了更深一些的認識。
一個寒涼的冬天清晨,友人相邀一同上山訪友。那是第一次見面,章垚坐在前排,我坐后排,熱烈地向溫暖車廂里的大家問好,并沒有看清章垚的容貌。因都是老友,大家迅速聊開,章垚只一句低沉的“您好”后再無下文。
一位羞澀的男子,三十幾歲的樣子。這是從聲音里,我給出的第一印象。后來,就發現了自己的武斷。
章垚,1992年出生,如假包換的“90后”。他也并不羞澀,只是內斂和安靜。在章垚身上,你會發現屬于又完全背離于“90后”這個族群的表現。他善于學習,卻又極寡言少語。他不僅線下話少,線上也惜字如金。
2016年,一整年一共62條朋友圈。2017年,25條朋友圈。2018年至今,6條。內容清一色是器物的圖片,文字寥寥無幾。
惟一的一張自己的照片,他寫“故作”。
寥寥的字句里,他說與陶的感情。
“陶器在旋轉中成長,是泥土的果實。”“我做陶,喜歡表現陶土的土氣,那是原始不攜帶裝飾的山野。”
他記錄和器物的日常。
“極靜思動,尋一寂處,希望盡力融入背景的滄桑。”“最近特別喜歡摘下眼鏡,十公分的距離觀察壺身細節,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一直想找到一種泥質,安靜,樸素,自然它出現了,有些好得讓自己意外,黃褐色,隱藏著細細的砂斑,手可以感覺到微微的摩擦,像巖石……”
他說心得。
“想表達審美,往往忽略了別人。”“正如普通人的一天,辛苦的勞作中,出現驚喜,對我而言,可以傻笑一天。”“經歷得多了,總會有些磕磕碰碰的痕跡。”“靈感不是偶然,源于苦思背后的升華。”
他創作也臨摹名家作品。“臨摹并非死搬硬抄,而是在前人基礎上,加入自我的審美,為己所用一摹日人杉江壽門南蠻急需”
朋友圈里他提及過無錫一拳石齋的王大漾先生兩次,兩次都是記錄王大漾先生在自己作品上題字的事。對長者的敬重,可見一斑。
無論線上線下,相比于參與到別人的對話和討論里,他更享受做一名傾聽者的身份。
他的不露聲色,有一種超越年齡的深沉。然而,這種深沉,并非故弄玄虛,而是自然的由內而外的生發。他只淡淡地坐著,卻好像洞悉了一切。
這和他的作品的氣質是暗合的。他的陶藝作品,是簡素無華的,也是沉默不語的。
在茶室里,它不是會積極表現自我的器皿,就像空氣般理所當然得存在著。在茶席上,即便是做主器使用,依然是一種無為之氣。只那樣安穩的存在,讓周遭的一切不恐慌。每當你想起它時,就會發現它一直在身邊,守護著一席一室的日常。
在手上,有一種安定的良好手感。手是誠實的,平穩的心情應當是使用器皿的真正喜悅。親手確認陶土的觸感,翻過來欣賞底部的圈足,情緒也會隨著沉靜。之后,在長期的使用下,等茶漬滲入細微的縫隙,悄悄地改變器物的表情。器物也就隨著時間留下使用者的痕跡,完成制作者和使用者的交接。
器物良好的氣質,一是與作者的氣質息息相關,二是仰仗作者扎實的基本功。
大學三年在宜興系統學做紫砂,為章垚打下扎實的基本功。后在陶藝創作道路上,陶藝大師青木木米、昌平寶山又給了他深刻的審美啟迪,并非規整、完美、無痕跡才是美,拙樸、殘缺、痕跡也可以是一種美。正是這種審美觀的建立將他從原來的紫砂壺帶到陶的領域。
說起自己陶作上的細節,章垚說它們表情豐富而又自成一系,根據泥土、壺型、機理、釉料,壺可分為銹(銹斑)系、鐵(金屬)系、羅(螺旋)系、輪(巨輪)系,而五色銹、紫金銹、烏金……則是陶土在釉色渲染下不同的顏色,不論何種壺都有他想要表現的樸素,實用之余更經得起觀賞。
“陶土在旋轉中變化,在旋轉中形成自己的紋理,旋轉紋、橫向水波紋、跳刀紋……這些紋路的形成是簡單的,但如何形成美則是創作者用心的地方。”
正如期待陶土在旋轉中自在的紋理,章垚也從不限定陶器的創作形式,樂于嘗試實驗各種燒制工藝、泥土配方。時常為了找到自己滿意的泥土,而試上十幾種泥料,比如一把簡單的煮水壺往往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泥土,而需花上半年之久才能將泥料配方穩定并確定下來。
有人說匠人的心必須是平靜的,但冒險的心卻總是按捺不住的,一種成功率高,但是效果普通,一種成功率低,但是效果好。
章垚說他選擇后者,說這才陶土的氣質,寧可燃燒生命的活一場,也不愿平凡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