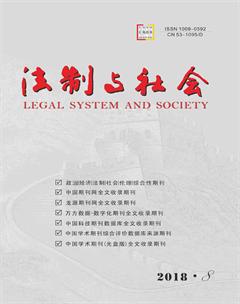論設立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法理基礎
李曉瑜
摘要推進合憲性審查必須落實在制度上。文章依托對合憲性審查制度的內涵、立法例及現實窘境的梳理,詳細闡明設立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關鍵詞合憲性 審查 憲法 法律委員會 憲法監督
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與否,是該國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作為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依托,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首要的是堅持依憲治國。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最高表現形式和制度載體,憲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居于“總章程”地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憲性審查機制,完善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設置,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全面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的專業化、常態化,維護憲法權威,既是法治所需,又是民心所向。
一、合憲性審查的含義與國內外立法例
合憲性審查,亦稱違憲審查,是指享有違憲審查權的國家機關依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法定程序以特定的方式,對有違憲之虞的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以及國家機關的履職行為進行審查、裁決的憲政制度。合憲性審查作為憲法監督手段之一,也被形象地稱之為憲法的“牙齒”。
自180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首次確立違憲審查制以來,實施憲政的世界多國紛紛結合本國政治文化、法律傳統、憲政理念等建立了符合本國國情的憲法監督制度。綜合來看有三種模式:一是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司法機關審查模式,主要以普通法院為憲法監督機關;一種是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專門機關審查模式,主要以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為憲法監督機關;還有一種就是以中國、英國為代表。的立法機關審查模式,主要以最高權力機關為憲法監督機關。
我國早在1982年制定現行憲法時就曾考慮過設立專門的憲法委員會,以具體負責憲法實施、憲法解釋等職責,但基于多方面的因素該方案最終被擱置,而僅在《憲法》第62條、第67條概括地規定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憲法的實施。由于《憲法》條文的概括性和學理上憲法監督主體的廣泛性,導致—段時間以來作為監督核心手段的“合憲性審查”被憲法監督一詞直接湮沒。實踐中由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自身組織制度和工作特性,我國的合憲性審查也一度處于實質上的“休眠”狀態。
依據《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規則》、《監督法》和《立法法》的規定,我國的法律草案在表決之前需要經過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三審”,統一審議工作具體交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負責,法律委員會有權提出獨立的修改建議。換言之,法律委員會在制定、修改法律過程中并不能取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合憲性審查權,但在形式上合憲性審查經由法律委員會來完成。。此外,《立法法》第88條、第89條還落實了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備案機制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上述法規的備案審查權,2005年修訂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經濟特區法規備案審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釋備案審查工作程序》也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的合法性審查程序,但對于比法規位階更高的法律違憲如何進行審查監督,對于國家領導人和公職人員行為違憲如何進行審查監督等卻仍然立法空白。
二、設立專門合憲性審查機關的必要性
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合憲性審查是加強憲法實施和憲法監督的核心,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項關鍵制度,被盛譽為“立憲法治國大廈的拱頂石”。深讀黨的十九大報告原文不難發現,關于“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的表述,立足于“深化依法治國實踐”,落腳于“維護憲法權威”。遣詞“推進”而非“建立”、“工作”而非“制度”,意在強調中國的合憲性審查并非空白而是待加強、并非要全新重構而應在現有制度資源基礎上進一步優化。
在我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合憲性審查權事實上一直是由法工委、各專門委員會及其他輔助機構協同實施的,具體為法律委員會在統一審議法律草案時進行事前合憲性控制,法工委對法律以下的其他法規、司法解釋等規范性文件進行被動合憲性審查與合法性審查。縱覽能公開查詢到的三十余年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和2012年以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備案審查工作情況報告,五年來法工委共主動審查研究了60件行政法規,128年司法解釋,同時還精選十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向社會公布,備案審查工作大幅進展,常態化的、可覆蓋審查主要環節的備案審查規則體系基本完備,憲法實施推進明顯。
但是,由于法律委員會和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相當于司局級)在職級規格上的弱勢、動力機制上的缺失、備案審查程序的不公開,以及長久以來形成的國家機關之間“不唱對臺戲”的非對擾性共識,法律委員會的事前合憲性控制和法工委的備案審查基本上局限于以憲法文本為依據的字面審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合憲性審查亦缺乏操作性。截至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尚未主動公開撤銷過任何違憲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立法法》第99條第1款所規定的有權提出合憲性審查請求的各國家機關主體亦不曾行使過該權利,而第2款所規定的公民、企事業組織、社會團體等其他主體雖以平均每年800余件的數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建議,但也未曾見到關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公開受理、審查或答復的公開報道,工作透明度差強人意。
質言之,當下我國的法律草案審議制度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制度體系未能完全覆蓋全部的違憲情形,合憲性審查被倒置在合法性審查中,且常常被有意忽視;其運行機制和程序建設尚存在一定缺陷,合憲性審查工作的制度化、系統化大打折扣。該情形極大影響我國憲法實施的效果和憲法權威的樹立,有必要依托執政黨的強有力政治決斷,強化合憲性審查和憲法監督,深化人大機構改革和專門委員會設置,設立專門合憲性審查機關協助全國人大常委會集中、高效、統一行使合憲性審查權。
三、設立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可行性
如上所述,設立我國專門合憲性審查機關的構想由來已久,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推進,設立適宜的專門審查機關時機已然成熟。至于應該設立哪種類型的專門機關,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廣大法律人見仁見智。總體來看無外乎以下幾種方案:于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置一個單獨的、與法律委員會平行的憲法委員會;于全國人大常委會之外設置一個單獨的、與人大常委會平行的憲法委員會;于全國人大之外設置一個單獨的、與全國人大平行的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于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置一個優化整合后的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等等。
誠然,設置專門的合憲性審查機關是牽一發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是一項兼顧政治性、法理性的工作。,必須在堅持中國國情、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發生冒進型改革的前提下,縝密論證、精細設計,選擇一個成本最低、可行度最高的方案。與全國人大平行的憲法委員會方案顯然是在效仿法國的憲法委員會模式,不論是憲法法院還是憲法委員會,這種二元制方案與我國政體不相符合,缺少在中國生根的土壤。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平行的憲法委員會方案在學術界一度擁有很高的呼聲,其優點在于能確保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元制和憲法委員會的高規格,但卻難以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這一現有監督機關與新的憲法委員會之間的職能協調問題。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從戰略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高度對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優化升級作出了重要部署—一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在原有職能基礎上增加合憲性審查等職責,充分發揮專門機關作用,加強憲法監督,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總體而言,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設立采取的是一種穩步推進的方案,在堅持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享有最高立法權和憲法監督權、維護全國人大常委會合憲性審查最終決議權的前提下,充分整合優化法律草案統一審議過程中的合憲性審查和合法性審查機制,賦予專門委員會強有力的審查權,突出合憲性審查和憲法監督職能,能夠很好地協調人大常委會和專門委員會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