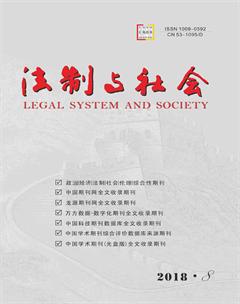公司法股東代表訴訟前置程序實證研究
鄭曉霞
摘要本文基于對2017年裁判文書網中關于股東代表訴訟的案件進行分析,探討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前置程序的態度,并結合最新施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簡稱法釋[2017]16號)的相關規定,提出公司法前置程序完善建議。
關鍵詞股東代表訴訟 前置程序 實證研究 程序豁免
一、概述
股東代表訴訟,是指“當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主體侵害了公司權益,而公司又怠于追究其責任時,符合法定條件的股東可以以自己的名義代表公司提起訴訟。在我國法律體系中,除了公司法中有所規定外,《證券法》第47條還規定了短線交易情形下的股東代表訴訟,在此不予細致討論。
根據我國《公司法》第151條的規定,股東在獲取代表訴訟訴權之前,必須先履行前置程序,窮盡公司內部救濟。具體來講,股東在提起代表訴訟前,根據被告身份的不同,應事先書面請求監事(會)或董事會(執行董事)向法院提起訴訟,若監事(會)或董事會(執行董事)拒絕原告股東的申請,或者在收到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沒有提起訴訟,股東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除了這種常規性規定外,還規定有一種前置程序豁免的特殊情形,即在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時,股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就是說,履行前置程序是進入股東代表訴訟的一條必經之路,而前置程序豁免則是一種例外情形。
二、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股東代表訴訟前置程序的處理
截至2017年12月份底,筆者在裁判文書網上搜索“股東代表訴訟“關鍵詞,并限定案由為”與公司、證券、保險、票據等有關的民事糾紛“,檢索到案件數量總計為445件,2017年作出的判決中與前置程序直接相關的案例為61件。本文基于對2017年新作出的61個案件進行分析,探討法院在實務中對于股東代表訴訟前置程序的態度。
在61件確與前置程序有關的案件中,因前置程序未履行或不合格而被法院直接駁回起訴的案件有32件,占到總案件數量的一半。因原告合格履行前置程序而進入訴訟的案件有19件,約占1/3,原告獲得前置程序豁免的案件有10件,約占1/6。
法院對于前置程序的性質和作用看法的不同,直接決定了原告是否能進入股東代表訴訟程序之中。有法院認為,“前置程序是一項法定的強制性義務”,也有法院認為,“前置程序規定在法院在受理案件時,只是一條具有釋明性、指引性的條文,并非是一條強制性的程序規范”,并進一步認為,“從法律規定的本意而言,股東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設置系為了充分發揮公司的內部監督機制,是竭盡公司內部救濟原則的體現,并非以阻礙股東白行訴訟為目的。因此,對于股東是否已經履行前置程序,其判斷標準不能過于苛求”。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法官也曾在判決中表示“對于公司法第151條有關股東提起代表訴訟,應當認為其所針對的是公司治理形態的一般情況;對于確屬股東申請無益,即客觀事實能夠證明公司監事(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不可能接受股東的上述申請,應當認為已經‘竭盡公司內部救濟,公司法的本意并不要求這種情況下的股東代表訴訟仍然要經過‘書面請求公司機關起訴這一前置程。”因此,實踐中不同法院關于前置程序的認識,還存在差異,這也直接導致了現實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在法院因前置程序駁回起訴的32個案件中,原由為未書面請求公司監事(會)或董事(會)的案件有22件,原告在履行前置程序中形式存在瑕疵案件1件,原告具有股東身份與監事身份重合的案件有8件,股東身份與法定代表人身份重合的案件有l件。
在前置程序豁免的10個案件中,原由為被告(侵權人)包含公司董事、監事,原告是否履行前置程序均無實際意義的案件為2件,原告兼具股東和監事身份的案件4件,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案件3件,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公司未設監事會或監事的案件1件。
三、前置程序的制度價值
通過對比發現,當原告同時具有股東和監事雙重身份時,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有些法院認為不能當然豁免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東代表訴訟,如果要提起訴訟,應當代表公司以公司名義提起訴訟,而不能以監事身份直接提起訴訟,因此駁回起訴。而有些法院認為原告兼具公司股東、監事(公司未設監事會)雙重身份,要求其先以股東身份向作為監事的自己提出相關書面請求,并不合理亦無必要,因此不能以此理由駁回起訴。
公司自治是法人制度的一個核心點,公司自負盈虧,具有獨立人格,從而區別于公司內的股東。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建立則似乎是超越了公司的獨立人格,賦予了公司股東代行公司訴權的權利,在客觀上限制了公司自身處分自己權利的自由。所以,為了平衡公司自治與股東利益之間的關系,尊重公司自主意志,防止股東濫用訴權,節省訴訟成本,就在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中加上了前置程序,給公司以自行矯正、自我治理的機會。可以看出,前置程序具有平衡公司自治與小股東權利之間的作用。
而關于前置程序的豁免,有學者認為,“在法律明文規定的‘緊急情況之外,還存在其他—些具體的請求豁免情形:董事和監事同時為被告;原告兼有股東和監事的雙重身份;公司清算過程中,董事會與監事會等機構停止運作,前置程序無法實現目的”。而美國很多州的法律對于前置程序的豁免執行“申請無益”的標準。“申請無益”的含義在上述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法官的判決中也有所闡述。
四、完善建議
法釋[2017]16號中第23條至26條規定了股東代表訴訟的相關問題。其中,第23條中規定,監事(會)根據《公司法》第151條第—款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訟時,應當列公司為原告,然后依法由監事(會)代表公司進行訴訟。董事(會)根據《公司法》第151條第—款的規定對監事或第三款的規定對他人提起訴訟的,應當列公司為原告,依法由董事長(執行董事)代表公司進行訴訟。此項規定,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是當監事和股東身份重合時,應當直接以公司為原告,以監事身份代表公司進行訴訟,無需再進行股東代表訴訟,這是與股東代表訴訟性質不同的訴訟方式;二是對于非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其它侵犯公司權益的“他人”,應當由董事會(執行董事)而不是監事(會)提起訴訟。換言之,在法釋[2017]16號公布實施后,對于前述案件中,原告兼具股東和監事身份的情形,不應再成為股東代表訴訟前置程序中的豁免理由,而是應當告知其以公司名義直接提起訴訟。
但是對于《公司法》第151條第二款中的“緊急情況”應當如何理解,新的司法解釋中并未明確,而實踐中所遇到的被告包括董事和監事等情形,是否能夠獲得前置程序的豁免,也還經常會產生不同的判決。因此,前置程序在司法實踐中依然還存有困惑。
前述也提到了前置程序的價值理念,而前置程序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其本質是一種權衡:究竟是公司自治(通過公司機關進行自我優化)更有利于維護公司利益,還是依靠小股東提起代表訴訟更有利于維護公司利益?筆者認為,相較于耗時耗力的訴訟而言,具有管理公司專業能力的公司機關更有可能維護好公司的利益。因而前置程序作為一道關卡,宜嚴不宜松。對于“緊急情況”的解釋也不可太過寬泛,但是對于前述朱慈蘊教授提出的幾種情形,筆者認為,應當在實踐中進行個案探討,并進行類型化分析,并由立法機關進行立法或最高司法機關進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