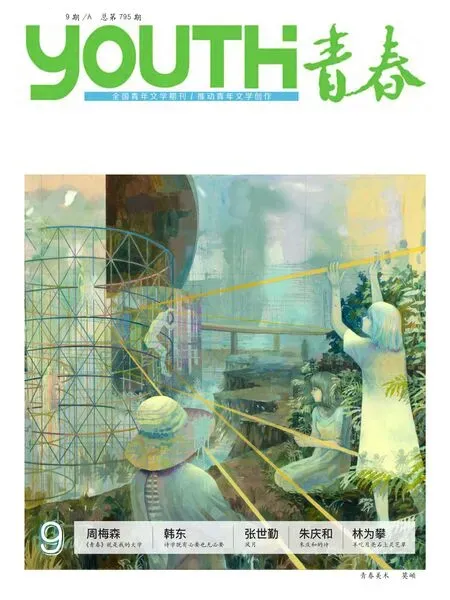周梅森:《青春》就是我的大學

周梅森,中國當代作家、編劇,1956年3月9日出生于江蘇省徐州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主要作品有《人間正道》《中國制造》《絕對權力》《至高利益》《國家公訴》《我主沉浮》《人民的名義》等政治小說,這些小說均被其親自改編成影視劇。
編后語 :《青春》創刊于1979年,40年來,數以千計的寫作者在這里留下青春的夢想和呼喊。為迎接本刊40周年大慶,特開設此專欄,邀請您來講述“我的《青春》故事”。專稿郵箱156543832@qq.com。?
情起《青春》,一往而情深
“《青春》這一兩年又回到了正軌,回歸到我們那會兒引領文學青年,推動青年文學創作的初衷,為年輕人留了不少版面……刊物的內容和版式也改觀不少……”一見面,周梅森老師就夸起《青春》來。
情有所起,一往而情深。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許多現在雄踞文壇的大家,都曾在青春發表過作品。比如王蒙連載了十來期的創作談《當你拿起筆》;比如張平的《姐姐》,發表后獲得了全國短篇小說獎;比如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一經發表便引起轟動,被稱為“知青小說”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時獲得1984年獲全國最佳中篇小說獎,隨后被拍成同名電視劇和同名電影……而嚴歌苓、葉兆言、蘇童、陳沖等,《青春》就是他們的起飛之地,他們的處女作大多是在《青春》發表的。像賈平凹、王安憶、韓東、賈慶軍等,都獲得過青春文學獎。青春文學獎一共辦了三屆……說起這些,周梅森如數家珍。
但要說對《青春》感情最深的,還得數周梅森。
從1979年下半年到1984年,周梅森在《青春》工作了整整四個年頭。“《青春》就是我的大學”,周梅森毫不諱言,娓娓道來:“1979年11月我到《青春》編輯部實習,那一年我23歲,相當于大學畢業的年齡。昨天還在煤礦上班,下井,第二天就坐到了代表中國文壇最前沿陣地的殿堂。那時的《青春》對全國的文學青年來說,就是圣殿、廟堂……”
在多次采訪中,周梅森曾都坦言自己并沒有上過大學,并不是因為他沒有上大學的資質條件,而是他自行選擇了放棄。空閑時間,他醉心于文學閱讀與創作。“那時的主編斯群,給我們編輯有一項很好的福利,每個月都會給我們發書,各種文學名著,我的閱讀積累都是在那幾年完成的。《青春》就是我的大學,我在《青春》通過自學完成了我的大學教育和文學教育,這甚至是在大學里都學不到的。”周梅森說。

周梅森老師(左)與本刊主編李檣合影
國家撥的紙只夠印20萬份
1979年,《南京文藝》創刊,這個名字用了四期,到1979年10月,正式更名為《青春》了,當年出了3期。發行量達20萬冊,到1981年的第一期,就30多萬冊了。當時《青春》的印刷用紙,是國家撥的,就夠印20萬份的,想多印自己想辦法去。要不是因為紙張問題,《青春》的發行量,1981年那一年至少50萬份。讀者需求太大了,怎么辦,我們就自己想辦法,到處去找紙,能弄來多少就加印多少,總是不夠賣的。后來紙源問題解決了,《青春》的發行量很快突破50萬份,接著是60萬,最高時達65萬冊。
“那個時候的《青春》真是太火了,跟現在沒法比。那個時候《青春》的小說編輯部分為兩個組,小說一組和小說二組,一組是負責省內的稿件,我在二組負責省外的稿件,而二組里只有我一個編輯,但雜志社要求每稿必復,任務量非常大。我們就請了金陵中學、中華中學等學校的語文老師幫忙,幫忙挑選優質稿件,剩下的稿件寫好退稿信寄給讀者。他們每次來雜志社都要背著麻袋,一麻袋一麻袋的裝稿件回去。”任編輯期間,周梅森每日收到來稿能有上百份,只要有一天不看稿,桌子很快就被積壓的稿件淹沒了。“而我們當時的工作,除了編稿子,還有一項重要的事情就是落實紙張問題。”周梅森驕傲地說。
當時的紙張來源,有一個重要渠道,是通過軍隊系統幫忙弄到的。有一天,周梅森和吳野兩人開著面包車去城南的大校機場拉紙。那時候的大校機場是軍用加民用,管理比較松散。“由于路況不熟,加上是晚上,我們居然把面包車開到了飛機跑道上,一輛飛機正巧在著陸,與面包車幾乎是擦頂而過,險些釀成大禍。”說起這段往事,周梅森還心有余悸,似乎沉浸到了年輕時代的激情回憶中。
“《青春》因此與當時的上海的《萌芽》,北京的《青年文學》,四川的《丑小鴨》并稱文壇四小名旦,轟動一時。后來《丑小鴨》不辦了,四小名旦也有了多個版本,但不管哪個版本,都少不了《青春》……”周梅森有些感嘆。
從小礦工到大作家
1971年周梅森初中一年級就以半工半讀的名義進入了礦工行列,17歲高中沒畢業就繼續留在煤礦,做機械工,這期間他聽著皮帶運輸機的噪音,加上藥物反應,留下了后遺癥——耳朵失聰。

周梅森老師(左)與本刊編輯張元合影
周梅森22歲時,還在徐州韓橋煤礦當工人。他回憶說,我們全家6口都生活在煤礦,全家的固定資產不足人民幣三百元,家中的家具全是向礦上租用的,大床8分錢,小床4分錢。那時,我喜歡寫作,卻連一張最基本的書桌都沒有。
他的文學夢卻在深深的礦井里悄悄萌發。一次偶然,他從廢品收購站得到了一本殘缺的《巴爾扎克傳》。巴爾扎克在拿破侖像下寫了一句話:“你用劍征服世界,我將用筆征服世界!”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激勵了他。于是利用空余時間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習作《煤鄉怒火》,被大伙兒爭著傳閱。
那時改革開放剛起步,工人們開始學技術,而周梅森卻鬼使神差地一心想當作家。但文學創作對他的家鄉來說,簡直是個笑話。創作之初,發表作品絕不是個簡單的事情,稿子一篇篇被退了回來。
1979年的10月,《青春》雜志剛剛創刊,機緣巧合之下他被借調到《青春》當一名文學實習編輯。做文學編輯的前一天,他還在下井工作,第二天便拎著柳條箱進了《青春》雜志社的大門。一開始,他的父親不同意他去做文學編輯,周圍同事,鄰里也說,你去做編輯,工資肯定拿不到那么多了,一個月比礦工少了20多塊錢。其次父親擔心膽大放肆的周梅森惹出事,不如在家老老實實做技工。但父親拗不過他,他堅定地選擇了自己的文學夢。
1980年,周梅森在《青春》上發表短篇小說《明天一定再來》,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那時候,周梅森喜歡研究歷史,因為那時他還沒有過于豐富的人生閱歷,像《人民的名義》這種作品是寫不了的,他就從文獻資料中尋找素材和靈感,去翻新那些“歷史的塵埃掩蓋下的故事和人性”。如《黑墳》《軍歌》《英雄出世》相繼應運而生。
1992年,周梅森回到家鄉,家鄉正熱火朝天地集資建三環路。當時家鄉還比較閉塞,老百姓對修路的意義不大了解,還有人告主要領導的狀。一次偶然的機會,那位領導和他談了話。這次談話使他認識到改革的艱難,不僅改變了他對官員的看法,也改變了他的文學道路——以反映這個時代的巨大變化和深刻的矛盾為重要內容。1995年,他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小說《人間正道》。其后仿佛是掘開了一口富產的油井,不可遏止地噴發出直面現實問題的作品,《人民的名義》等一大批長篇小說問世。
繼《人民的名義》之后,周梅森又用一年的時間創作了《人民的財產》。在我們的雜志新刊發行之際,《人民的財產》電視劇已經在南京開機,期待他能給予讀者和觀眾更多的感悟與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