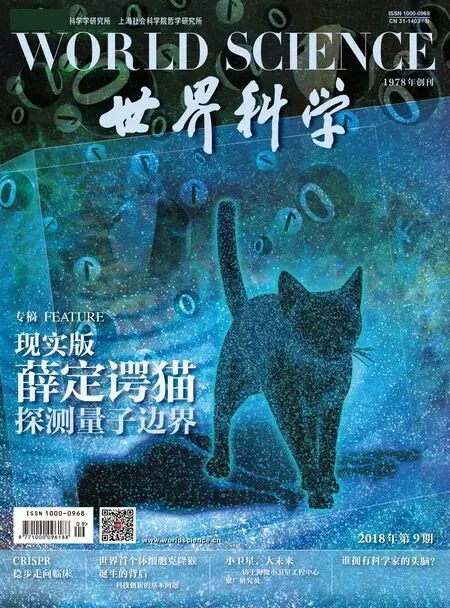量子云計算
編譯 魏劉偉
量子計算設備正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是當今只有少數專家可以在這方面用到它們的能力。托馬斯·帕彭布洛克(Thomas Papenbrock),帕維爾·盧高夫斯基(Pavel Lougovski)和馬丁·薩維奇(Martin Savage)描述了可商用的基于云的量子計算服務將如何向新用戶開放。

使用量子力學疊加原理處理信息的設備——量子計算機,正在大學和國家實驗室以及初創企業和谷歌、IBM、英特爾、微軟等大公司中開發、建造和研究。這些設備非常令人感興趣,因為它們可以解決某些計算上的“硬”問題,例如在搜索大規模的無序列表或分解大數字方面,量子計算機會比任何經典計算機都快得多。這是因為量子力學疊加原理類似于并行指數計算——換句話說,它可以一次探索多個計算路徑。
由于自然界在基礎上是量子力學的,量子計算機也有希望解決有關固體、分子、原子、原子核或亞原子粒子的結構和動力學的問題。研究人員在經典計算機上解決此類問題取得了很大進展,但隨著粒子數量的增加,所需的計算量通常呈指數增長。因此,這些領域的科學家對量子計算機感興趣并不奇怪。
作為建造量子處理器的基礎,許多不同的技術正在被開發出來。這些技術包括超導體、離子阱、光學器件、具有氮空位中心的鉆石和超冷中子等。所有這些技術面臨的共同挑戰是保持量子態相干足夠長的時間以執行算法,同時保持以受控方式操縱這些狀態的能力。
近來,具有超過50個量子比特的通用量子處理器已經發布出來——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里程碑,因為即使在這種相對較低的復雜程度下,量子處理器的操作也會變得太復雜,只有使用最強大的經典超級計算機才能模擬。這些50個量子比特的機器解決“硬”科學問題的效用目前受限于在退相干發生之前可以執行的量子邏輯運算的數量(幾十個),并且大量的研發工作集中在增加這樣的相干時間上。在這些設備上已經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問題是,怎么解決?
首先,找一臺電腦
科學家們在研究領域內邁出了使用量子器件解決化學、材料科學、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問題的第一步。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家與設備的開發者、所有者以及操作者之間就這些問題進行了合作研究。然而,公用的軟件(如PyQuil,QISKit和XACC)與程序量子計算處理器的組合,以及對設備本身讀取的改進,正開始向更廣泛的相關方開放。例如,IBM和Rigetti公司允許用戶分別通過IBM Q Experience和Rigetti Forest API訪問他們的量子計算機。這些都是基于云的服務:用戶可以在模擬器上測試和開發他們的程序,并在量子設備上運行它們而無須離開辦公室。
例如,我們最近使用IBM和Rigetti云服務來計算氘核的結合能——這是一種質子和中子的束縛態,構成重氫原子的原子核。我們使用的量子器件包括大約20個超導量子比特。單個量子比特上量子運算的保真度超過99%,而兩個量子比特的保真度約為95%。每個量子比特通常連接到3~5個鄰居。預計這些規格(量子比特數、保真度和連通性)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善,但近期的通用量子計算可能都會基于類似的參數——加州理工學院的約翰·普雷斯基爾(John Preskill)稱之為“有噪聲的中尺度量子”(NISQ)技術。

量子硬件:Rigetti的19量子比特處理器被用于執行氘核結合能的計算
氘核是最簡單的原子核,其性質眾所周知,這使其成為量子計算的良好測試范例。此外,由于量子比特是雙狀態量子力學系統(通常被認為是“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狀態),因此在量子比特和費米子之間存在自然映射——即具有半整數自旋的粒子遵守泡利不相容原理——例如構成氘核的質子和中子。從理論上講,每個量子比特代表一個費米子可以占據的軌道位置,并且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分別對應于占據該軌道的零個或一個費米子。基于這種喬丹·維格納映射,量子芯片可以模擬與其量子比特一樣多的費米子。
氘核結合能的量子計算的另一個有用特征是可以簡化計算本身。其平移不變性可將質子和中子的束縛態計算問題降低為單粒子問題,而單粒子問題僅取決于粒子之間的相對距離。此外,氘核的哈密頓量在長波長的限制下變得更簡單,同時質子和中子之間復雜的強相互作用的細節在低能量下沒有解決。這些簡化使我們可以只使用兩個或三個量子比特來執行量子計算。
然后,進行計算
我們在量子處理器上準備了一族糾纏量子態,并在量子芯片上計算了氘核的能量。狀態準備包括作用于一個初始狀態單一操作,它分解為一系列單量子和雙量子比特的量子邏輯操作。考慮到雙量子比特相對較低的保真度,我們采用了最少數量的雙量子比特CNOT(無控制)運算來完成這項任務。為了計算氘核的能量,我們以哈密頓量測量了泡利算子的期望值,將量子比特狀態投射到經典比特上。這是一個隨機過程,我們收集了每個量子態多達10 000次的測量統計數據。這大約是用戶通過云訪問可以進行的最大測量次數,但這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了,因為我們受到噪音的限制而不是統計數據的限制。然而,采用更多量子比特或更高精度、更復雜的物理系統可能需要更多的測量。
為了計算氘核的結合能,我們必須找到所準備的所有量子態的最小能量。這種最小化是使用經典計算機完成的,使用來自量子芯片的結果作為輸入。我們使用了兩個版本的氘核的哈密頓量,一個用于兩個量子比特,一個用于三個量子比特。雙量子比特計算僅涉及單個CNOT操作,因此不會顯著地受到噪聲的影響。
然而,三量子比特計算受噪聲影響很大,因為量子電路涉及三次CNOT操作。為了理解噪聲的系統效應,我們在量子電路中插入了額外的CNOT操作對——相當于沒有噪聲的同一性算子。這進一步提高了噪音水平,使我們能夠測量和消減能量計算中的噪音。最終,我們的工作產生了通過云執行的原子核的第一次量子計算。
接下來——
我們同時使用量子處理器和經典計算機進行計算。然而,量子計算機也為獨立應用帶來了巨大的希望。例如,由于相互作用的費米子的動力學由單一的時間演化算子產生,因此可以通過量子芯片上的單一門操作自然地實現。
在另一個實驗中,我們使用IBM量子云來模擬施溫格模型——這是一個典型的量子場論,描述了通過電磁場耦合的電子和正電子的動力學。我們的工作遵循由埃斯特班·馬丁內茲(Esteban Martinez)和因斯布魯克大學的合作者所做的工作,他們2016年使用高度優化的離子阱系統作為量子器件,探索了施溫格模型的動態,該系統允許他們實施數以百計的量子操作。為了通過云訪問NISQ設備進行模擬,我們利用模型的對稱性來降低量子電路的復雜性。然后,我們將該電路應用于初始基態,產生單一時間演化,并僅使用兩個量子比特測量電子-正電子含量隨時間的變化。
來自IBM和Rigetti公司的公開的Python API使得云量子計算體驗變得非常簡單。我們在模擬器上測試我們的程序,并在實際量子硬件上運行計算,無須了解有關硬件本身的許多細節。然而,雖然軟件將我們的狀態準備單元操作分解為一系列基本量子邏輯運算,但該分解并未針對硬件進行優化。這迫使我們修補量子電路,以便最小化雙量子比特操作的數量。展望未來,并考慮更復雜的系統,如果這種類型的分解優化可以實現自動化,那就更好了。
在量子計算史的絕大多數情況下,量子計算僅僅實驗性地供少數研究人員使用,這些研究人員擁有建造和操作此類設備的專有技術。量子云計算將改變這一點。我們發現它是一種解放性的經驗——一個偉大的均衡器,有可能為許多人帶來量子計算,正如設備本身開始證明自己的價值一樣。
資料來源 Physics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