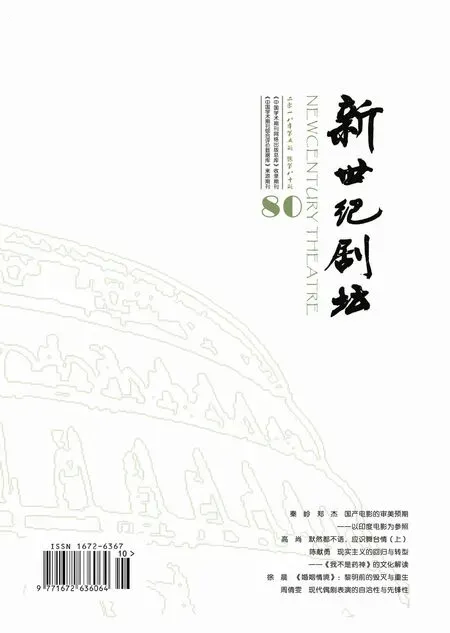當(dāng)代導(dǎo)演藝術(shù)中西“融合”的實(shí)踐與思考
——以實(shí)驗(yàn)戲劇《命中注定》中國(guó)元素運(yùn)用為例
2018年6月16日到18日,“當(dāng)代戲劇導(dǎo)演藝術(shù)與導(dǎo)演藝術(shù)人才培養(yǎng)國(guó)際論壇”在上海戲劇學(xué)院召開(kāi),與會(huì)三天各位戲劇導(dǎo)演專家、教育專家就目前全世界范圍戲劇導(dǎo)演及其人才培養(yǎng)話題展開(kāi)熱議。在這期間,關(guān)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戲曲在當(dāng)下的生存,東西方戲劇的審美特征,舞臺(tái)手段的東西方碰撞等課題引來(lái)眾說(shuō)紛紜,中國(guó)的導(dǎo)演藝術(shù)家爭(zhēng)論的話題一直都集中在中國(guó)戲曲的發(fā)展如何借鑒西方戲劇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在實(shí)際運(yùn)用中出現(xiàn)的參差不齊、優(yōu)劣參半等問(wèn)題。而國(guó)外的學(xué)者更加強(qiáng)調(diào),為了使導(dǎo)演培養(yǎng)立足民族性,很多國(guó)外專家都有過(guò)向中國(guó)戲曲“寄養(yǎng)”的經(jīng)歷。這一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實(shí)則非常有趣,體現(xiàn)了世界范圍內(nèi)導(dǎo)演藝術(shù)獨(dú)立性與“融合性”的撞擊。
在這幾年的創(chuàng)作中,我本人也做了類(lèi)似的探究和嘗試,先后執(zhí)導(dǎo)、主演了由上海戲劇學(xué)院出品,參加國(guó)際戲劇節(jié)的實(shí)驗(yàn)作品:《命中注定》(導(dǎo)演)、《趙氏孤兒》(導(dǎo)演)、《朱麗葉還魂記》(主演),在這里我想以《命中注定》為例,談?wù)剬?duì)導(dǎo)演藝術(shù)中西“融合”的理解。
2014年7月,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huì)博士生交叉平臺(tái)資助項(xiàng)目——實(shí)驗(yàn)戲劇《命中注定》,在韓國(guó)首爾參加國(guó)際青年戲劇節(jié),第二年6月,由上海戲劇學(xué)院繼續(xù)教育學(xué)院推出的修改版,亮相于土耳其比爾肯特大學(xué)國(guó)際戲劇節(jié)。既是實(shí)驗(yàn)戲劇,那么這出戲的“實(shí)驗(yàn)”在何處?“實(shí)驗(yàn)”的尺度以何為衡量?在當(dāng)下的琳瑯滿目的“實(shí)驗(yàn)”劇潮中究竟扮何角色?本文將從這三部分逐一展開(kāi)。
一、“融合”式的實(shí)驗(yàn)
(一)如何理解“融合”
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中對(duì)于“融合”的解釋是:“幾種不同的事物合成一體”,這里我借用這個(gè)詞的目的主要是區(qū)別于時(shí)下另一種實(shí)驗(yàn)戲劇。
比方說(shuō),標(biāo)榜實(shí)驗(yàn)先鋒戲劇的孟京輝導(dǎo)演在話劇《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的意外死亡》中,即用歌隊(duì)的形式代替了很多表達(dá)主題的段落,讓觀眾時(shí)刻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讀解和表達(dá)立意上。又如2007年獲勞倫斯奧利弗最佳喜劇獎(jiǎng),2009年成功上演于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的《39級(jí)臺(tái)階》,就充分利用假定性的舞臺(tái)方式、弱化懸疑成分的敘事結(jié)構(gòu),成功地將一部懸疑巨著變成了一個(gè)喜劇。再比方說(shuō)由上海戲劇學(xué)院李建平教授排演的甬劇《風(fēng)雨祠堂》僅僅借用了迪倫馬特名劇《貴婦還鄉(xiāng)》這個(gè)故事,上演了一出中國(guó)江南小鎮(zhèn)的愛(ài)恨情仇,映射出金錢(qián)誘惑下對(duì)人性丑惡的嬉笑怒罵。諸如此類(lèi),舉不勝舉,對(duì)經(jīng)典劇目的改編尤為居多。在原創(chuàng)劇目中,更有類(lèi)似于《魯鎮(zhèn)往事》《人模狗樣》《外套》……這樣的實(shí)驗(yàn)先鋒類(lèi)型,他們對(duì)于文本的要求可能僅僅依靠的是一個(gè)幕表制甚至只是某種概念。
這一類(lèi)戲劇的主要特點(diǎn)是對(duì)劇目或者是文本做了根本性的調(diào)整,其主題立意的表達(dá)更接近編創(chuàng)者的主觀意識(shí),其創(chuàng)作目的更有創(chuàng)造出新的舞臺(tái)劇類(lèi)型之嫌。在這一過(guò)程中,導(dǎo)演拉開(kāi)了與原著的距離,他的創(chuàng)編意識(shí)更強(qiáng)。因此,相對(duì)于“融合”一詞,似乎用其反義詞“分離”更加準(zhǔn)確,這類(lèi)實(shí)驗(yàn)性戲劇不在本文探討范圍之內(nèi)。
我所說(shuō)的“融合”式實(shí)驗(yàn)所針對(duì)的,更類(lèi)似于傳統(tǒng)的戲劇排演,即編劇在文本的創(chuàng)作時(shí)候就已經(jīng)埋下“實(shí)驗(yàn)”的可能性,導(dǎo)演則在這一基礎(chǔ)上,賦予劇目某種舞臺(tái)樣式,追求他的主觀意識(shí),力圖為劇目找到他認(rèn)為最能表達(dá)作品思想內(nèi)涵的外部樣式。我想這樣的案例更為屢見(jiàn)不鮮:經(jīng)典劇目配合當(dāng)下流行元素的全新打造;原創(chuàng)劇目對(duì)姊妹藝術(shù)大膽植入;包括多媒體在內(nèi)的全新舞臺(tái)裝置革命性的誕生等。本世紀(jì)最杰出的代表——音樂(lè)劇的誕生,便是將戲劇、歌劇、舞劇、交響樂(lè)、流行音樂(lè)綜合成了一種全新的舞臺(tái)劇方式,當(dāng)年的某種“實(shí)驗(yàn)”變成了現(xiàn)在的流行,甚至開(kāi)創(chuàng)了新的劇種。這樣的“實(shí)驗(yàn)”歸納到“融合”這一詞上最為恰當(dāng)。
同樣是將不同事物進(jìn)行合成,相對(duì)“綜合”一詞,“融合”顯得更為謙卑一些。它的方式僅僅在于:借鑒、挪用、拼貼、重組。《命中注定》的實(shí)驗(yàn)性,實(shí)際上就是“融合”的實(shí)驗(yàn)。
(二)《命中注定》試圖“融合”的藝術(shù)元素
在劇本的創(chuàng)作初期,定下來(lái)兩項(xiàng)創(chuàng)意:一、將俄狄浦斯王的故事進(jìn)行續(xù)寫(xiě),依然是關(guān)于“命運(yùn)”主題的研究。讓最后垂死的俄狄浦斯有一次重生的機(jī)會(huì),把其與命運(yùn)抗衡的地點(diǎn)放到古代的東方。二、將一個(gè)提線木偶作為俄狄浦斯內(nèi)心欲望的外在表現(xiàn),與其始終較量直至共同滅亡。與此同時(shí),作為國(guó)際交流項(xiàng)目,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還要求突出中國(guó)元素,強(qiáng)調(diào)文化交流。
什么樣的舞臺(tái)樣式,才是屬于這個(gè)戲的最佳方案呢?作為導(dǎo)演,面對(duì)以上要求,更像一場(chǎng)命題作文。
《命中注定》講述的是這樣一個(gè)故事。俄狄浦斯在即將要被刺瞎雙眼之時(shí),代表另一心理形象的小木偶出現(xiàn)。雙方商議后,決定來(lái)到古老的東方再來(lái)做一次與命運(yùn)的抗衡,試圖擺脫“弒父娶母”的厄運(yùn)。在那里,化作俠客的俄狄浦斯,出手救了一名青樓女子秋娘,即使小木偶百般勸阻,依然受情欲的驅(qū)使,沒(méi)有抵擋住秋娘的真情誘惑與其共枕。聞聲趕來(lái)的員外——秋娘孩子的生父,當(dāng)面揭穿秋娘的真實(shí)身份,早已迷失自我的俄狄浦斯與其廝打。在員外生命垂危之際,道出與秋娘所生之子背負(fù)“殺父娶母”的神咒,而親生兒子就是將自己置于死地的俄狄浦斯。悲痛欲絕的東方俠客,頃刻間變回到遭人唾罵的俄狄浦斯,最后依然接受了命運(yùn)的宣判。

《命中注定》劇照
經(jīng)典故事續(xù)寫(xiě)是個(gè)很好的切入點(diǎn),放到了古代的東方本身就是一個(gè)很好的特色,而且俠客受青樓女子真情誘惑的故事,從觀眾視角來(lái)說(shuō)很有吸引力。人偶對(duì)話的實(shí)驗(yàn)性,也不是該劇作的獨(dú)家發(fā)明。近年來(lái),英國(guó)舞臺(tái)劇《戰(zhàn)馬》,百老匯經(jīng)典劇目《獅子王》都是人偶同臺(tái)的經(jīng)典之作。
那么,中國(guó)元素在哪里?于是,在導(dǎo)演構(gòu)思初期:戲曲式的表演,古典舞為主的歌隊(duì),包括極具東方特色音樂(lè)、服裝,帶水墨畫(huà)感覺(jué)的舞臺(tái)設(shè)計(jì)……等等一切,似乎蜂擁而至。我知道這是在看完劇本后的第一個(gè)創(chuàng)作興奮期。事實(shí)證明,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一直堅(jiān)持到了最后演出,姊妹藝術(shù)的“融合”為這出實(shí)驗(yàn)劇目的呈現(xiàn)抹上了一筆亮色。
然而,在聽(tīng)完羅懷臻老師題為《重返中國(guó)戲曲的手工時(shí)代》的發(fā)言后,我開(kāi)始反思,是否我們?cè)诮栌弥袊?guó)戲曲、中國(guó)木偶、中國(guó)古典舞、種種精髓的時(shí)候,太考慮“拿來(lái)主義”?特別是現(xiàn)代中國(guó)的舞臺(tái)導(dǎo)演,大多是在西方戲劇和教學(xué)方式下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對(duì)于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研究和繼承是在新時(shí)期下提出的要求。所謂的手工時(shí)代,我以為是以中國(guó)戲曲為代表的中國(guó)傳統(tǒng)舞臺(tái)藝術(shù)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各個(gè)部分的精致時(shí)代,無(wú)論文本、唱腔、詞曲創(chuàng)作、程式技法還是人物服裝造型,道具制作……其精良的程度,考究的地步足已讓觀眾贊嘆。
羅懷臻老師說(shuō)道:“……手工時(shí)代,是建立了戲曲審美觀的時(shí)候。它凝練在每一樣?xùn)|西里,頭飾、道具……”,他感嘆于時(shí)代變化下戲曲舞臺(tái)的改變:“比如,毯子功的身體翻空,現(xiàn)在的‘威亞’就可以完成,再比如手工的服飾和傳統(tǒng)的制作被工廠所代替……”最后他說(shuō):“……是否現(xiàn)在應(yīng)該回到那個(gè)時(shí)代,就像一塊電子表和手工表的珍藏價(jià)值,手工餃子和機(jī)器餃子的區(qū)別。”
而王曉鷹老師的發(fā)言更引起了我的思考,“……多年來(lái),我致力于‘中國(guó)式舞臺(tái)意象的現(xiàn)代表達(dá)’……假定性——詩(shī)……中國(guó)傳統(tǒng)戲曲的汲取,中國(guó)音樂(lè)等,不能是簡(jiǎn)單地將其堆砌,應(yīng)該是——浸潤(rùn)。”
我們的戲曲在借鑒西方的戲劇,西方的戲劇也在向中國(guó)戲曲取經(jīng)。這中間我想最應(yīng)該保留的是——味道,那個(gè)不管是咖啡還是茗茶,烈酒還是小燒的滋味。融合,在思想表達(dá)上應(yīng)該符合觀眾品嘗的習(xí)慣,手段的運(yùn)用應(yīng)該關(guān)注到可預(yù)計(jì)到觀眾范圍內(nèi)的觀演體驗(yàn)。一句話,我們的戲?yàn)槭裁炊蛟欤^眾是什么樣的群體,作為導(dǎo)演要做研究。
《命中注定》作為國(guó)際交流項(xiàng)目,對(duì)外交流,文化輸出,盡管融入了中國(guó)元素,似乎達(dá)到一種形式上的“融合”沒(méi)有問(wèn)題。但作為戲劇人,特別是中國(guó)的戲劇導(dǎo)演,我覺(jué)得離打造成具有中國(guó)美學(xué)意象的舞臺(tái)精品,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在這里,導(dǎo)演本身的積淀,對(duì)古今各戲劇流派的通曉研究固然重要,同時(shí),對(duì)舞臺(tái)上“詩(shī)”的表達(dá),對(duì)“浸潤(rùn)”的體現(xiàn),對(duì)于戲劇導(dǎo)演這樣一個(gè)以實(shí)踐擅長(zhǎng)的工作部門(mén)更值得推崇。
二、“融合”的原則
(一)淺顯易懂,淺嘗則止
通過(guò)對(duì)文本的分析,我總結(jié)如下:開(kāi)頭和結(jié)尾部分放在了遙遠(yuǎn)的古希臘,語(yǔ)言風(fēng)格是史詩(shī)式的,歌隊(duì)的部分集中在這兩個(gè)地方。中間的部分,集中演繹的是東方故事,語(yǔ)言風(fēng)格介于古語(yǔ)和白話文之間,部分段落還有戲曲的韻轍,敘事的部分在這里。
在表現(xiàn)古希臘時(shí)期,要求演員要有明顯的傳統(tǒng)的古典式誦讀的表演風(fēng)格,語(yǔ)言及心理把握一定符合西方人簡(jiǎn)明直接的表達(dá)方式,而在展現(xiàn)東方故事的時(shí)候,演員的表演是略帶戲曲化的生活表演,突出的是東方人的含蓄之美。
角色的要求,俄狄浦斯是具有東西方美學(xué)特征的代言人。因此,劇目的呈現(xiàn)不是特立獨(dú)行揭示某種東方的神秘,不像《趙氏孤兒》那樣講一個(gè)只有中國(guó)人才能理解和接受的故事,更不是塑造一個(gè)精神分裂能自如轉(zhuǎn)換東西方文化頻道的非正常角色。換句話說(shuō),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探索、人文精神的剖析,不需要過(guò)于晦澀,帶給觀眾的精神愉悅,一定是建立在“能看懂,不要受到語(yǔ)言太大障礙”的原則上,姊妹藝術(shù)的“融合”要淺顯易懂。
那么,需要的是敘事上的簡(jiǎn)明扼要,輔助演員創(chuàng)造一個(gè)由東方人扮演的具有西方文化印象的俄狄浦斯,上演西方人能看懂的東方故事。對(duì)中國(guó)元素的運(yùn)用一定要巧,不能過(guò)分渲染。太中國(guó)化,觀眾不會(huì)相信這樣一個(gè)俄狄浦斯王的存在;太西方化,外國(guó)觀眾無(wú)法獲得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了解。
每出作品都是具體的個(gè)體,無(wú)法有一個(gè)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化的唯一模式。西方的故事由中國(guó)戲曲來(lái)演繹,或者中國(guó)故事由國(guó)外的人物來(lái)體驗(yàn),再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舉個(gè)例子,可能我們無(wú)法將實(shí)驗(yàn)京劇《王者俄狄》和肢體劇《魯鎮(zhèn)往事》直接進(jìn)行比較,這是我的理解。
(二)寫(xiě)意手法的確立
這里先引用一下“戲劇性”一詞的解釋。“戲劇性,即是在人物關(guān)系和情節(jié)發(fā)展中產(chǎn)生的合乎情理的、有機(jī)的、不可逆轉(zhuǎn)的‘突變’,這種突變導(dǎo)致舞臺(tái)上發(fā)生使觀眾感到更大興趣的戲劇情境。”
作為導(dǎo)演,對(duì)于“戲劇性”的把握至關(guān)重要,不管是何種的戲劇實(shí)驗(yàn),“戲劇性”是“戲”能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說(shuō),情節(jié)中我們一定要找到真正有戲的部分。時(shí)下,有很多實(shí)驗(yàn)戲,做了很多的嘗試,但是,在“戲劇性”這一戲劇存在的核心上好像沒(méi)有抓住,吸引眼球的那些絕妙創(chuàng)意恰恰變成了“金玉其外”。
抓住了戲劇性,也就抓住了沖突的頂點(diǎn),我們創(chuàng)作者究竟要說(shuō)什么,要表達(dá)什么也就從這里起航。
俄狄浦斯接受了秋娘的夫妻情意是第一高潮段落。劇本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情欲”“女人的味道”對(duì)男人的誘惑。俄狄浦斯的東方之行,就是向“殺父娶母”的命運(yùn)的一次挑戰(zhàn),因此一路上,小木偶反復(fù)提醒。當(dāng)秋娘被俄所吸引時(shí),小木偶更是百般阻撓。在一古宅,一邊的青樓女子,第一次被俠士打動(dòng),欲托付終身,又礙于古時(shí)女追男的禁忌。另一邊,面對(duì)紅粉佳人,又恐重蹈覆轍,兩廂百般煎熬,最后秋娘奮不顧身,沖破傳統(tǒng)傾力表白。而俄狄浦斯也終究抵不住內(nèi)心欲望,趕走小木偶與秋娘和好。當(dāng)趕走小木偶的那一刻時(shí),全場(chǎng)有一個(gè)巨大的停頓,只有小木偶不無(wú)惋惜地離開(kāi)。
這里最讓人感動(dòng)的一定是面對(duì)愛(ài)情的秋娘,拋棄了所有的舊有觀念,為了生活、為了日后的家庭組建的膽大妄為,而憂心忡忡的俄狄浦斯正是被真情所動(dòng)改頭換面,成就了一段典型的中國(guó)式姻緣。
在這段戲里,“古宅”“雨夜”“窗下”既有著元曲《西廂記》中的東方神韻,又有著《羅密歐和朱麗葉》的莎劇浪漫情懷。雙方內(nèi)心的沖突達(dá)到高潮。
這段戲的寫(xiě)法恰恰說(shuō)明,實(shí)驗(yàn)戲劇《命中注定》依然是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雖然在故事上,是通過(guò)一個(gè)假想完成,但這一假設(shè)出來(lái)的東方故事,依然是嚴(yán)密地建立在生活邏輯上,人物的設(shè)定也是符合正常的生活邏輯,這一點(diǎn)毋庸置疑。

《命中注定》劇照
綜上所述,“融合”的又一原則被確立:遵循現(xiàn)實(shí)主義邏輯的非現(xiàn)實(shí)主義排演,用寫(xiě)意的手法展現(xiàn)中國(guó)元素。
三、假定性的豐富運(yùn)用
在這次論壇上,孫惠柱老師有過(guò)這樣的發(fā)言:“……戲曲在展現(xiàn)真實(shí)的層面上更加有手段。展現(xiàn)大寫(xiě)的人常比話劇更有表現(xiàn)力,現(xiàn)代性更加容易讓現(xiàn)代人接受。”
在《命中注定》中,這一美學(xué)理念在導(dǎo)演手法中得到了體現(xiàn),這種假定性的手法既展現(xiàn)了中國(guó)古典生活,也是非寫(xiě)實(shí)方式的一種嘗試。
(一)一塊“布”的奇思妙想
劇中有一段這樣的戲:窗下,秋娘吟誦一首詩(shī),壯士側(cè)耳傾聽(tīng),其內(nèi)容凄凄慘慘,聽(tīng)得叫人不免心生憐愛(ài)。
第一次拿到劇本,我就生發(fā)出用由兩名歌隊(duì)演員牽住一塊“布”來(lái)代替窗戶,用逆光的方式展現(xiàn)秋娘吟誦的場(chǎng)景。舞臺(tái)上,燈光漸暗,很空曠,很靜……兩人身著古時(shí)服裝,用料很飄逸考究,咫尺之間只有一塊“布”擋住,不遠(yuǎn)處有中國(guó)古樂(lè)相伴,那感覺(jué)更像是一幅唯美的中國(guó)水墨畫(huà)。用“布”來(lái)打破生活的幻覺(jué),非再現(xiàn)而是表現(xiàn)生活,這是典型的寫(xiě)意手法。
但是,僅一個(gè)畫(huà)面是不足以撐起整出戲的舞臺(tái)樣式,必須要讓它貫穿。于是,在大家集體智慧的幫助下,“布”變成了古希臘的神山,古宅的屋頂、窗戶、床榻,甚至變成了墻,最后變成了象征意味的毀滅。虛實(shí)結(jié)合,一動(dòng)一靜。同時(shí),它還起到了幕布、劃分表演區(qū)域和換場(chǎng)的作用,在舞美同行的精心設(shè)計(jì)下,它甚至變成了木偶標(biāo)準(zhǔn)出場(chǎng)時(shí)的背景和一幅水墨畫(huà)的舞臺(tái)背景。
整個(gè)演出過(guò)程,這塊“布”由歌隊(duì)演員牽引,“融合”的兩段古典舞也把“布”變成了必要的手持道具,最后的水袖也是這塊“布”的延伸和變形。
可以說(shuō),在“融合”各種姊妹藝術(shù)中,“布”把所有元素串起來(lái)了。在這里我要說(shuō),這實(shí)際上是假定性在《命中注定》中的充分發(fā)揮。
舞臺(tái)的處理非常簡(jiǎn)潔,從開(kāi)始那一刻到結(jié)束只是一塊“布”,作為外部樣式。“融合”的目的只是在幫助敘事,而到了高潮戲的時(shí)候,相反這塊“布”靜靜地鋪在演員腳下,一動(dòng)不動(dòng)。這樣的方式,實(shí)際上是通過(guò)前后的“動(dòng)”讓觀眾相信,明白我們的“約定俗成”,通過(guò)簡(jiǎn)單的字幕提示就能明白故事的發(fā)展。以此來(lái)強(qiáng)調(diào)高潮場(chǎng)面的“靜”,讓觀眾來(lái)細(xì)細(xì)品味,帶有濃郁中國(guó)味道的愛(ài)恨交織。
這樣一來(lái),屬于《命中注定》的舞臺(tái)樣式感基本確立。
(二)二胡的運(yùn)用
這是《命中注定》的又一中國(guó)元素的體現(xiàn)。劇中首先是情感場(chǎng)面現(xiàn)場(chǎng)伴奏。其次,二胡可以模仿風(fēng)雨、滴水、心跳的聲音,在演出過(guò)程中音效的功能所得到的觀眾回饋頗好,他們的笑聲告訴我們,戲他們看懂了。
在首爾的演出中,小木偶的語(yǔ)言,我們是通過(guò)其中一個(gè)歌隊(duì)演員完成的。而在修改版中,我們是讓二胡演員完成的,實(shí)際上是增加了觀眾對(duì)二胡——這一中國(guó)元素的關(guān)注。
(三)歌隊(duì)的運(yùn)用

《命中注定》劇照
在古希臘戲劇中,歌隊(duì)是常用方式,這一點(diǎn),該劇作者在展現(xiàn)西方文化的古希臘場(chǎng)景里寫(xiě)得非常充分。在東方場(chǎng)景里,盡管三名演員化身成劇中人物完成角色扮演,但我依然不滿足。
中國(guó)戲曲,在假定性的運(yùn)用上有著屬于自己的特有的原則,創(chuàng)造出不少具有很高藝術(shù)價(jià)值的假定性手段。
在《命中注定》中,歌隊(duì)演員在開(kāi)始和結(jié)束充當(dāng)?shù)氖菍徟姓叩男蜗螅诘诙温鋼u身變成中國(guó)普通的人群,在某些環(huán)節(jié)他們要符合前面所提到的“融合”的原則,在觀眾和戲中間會(huì)有跳進(jìn)跳出的環(huán)節(jié),甚至有些戲耍的成分。比方說(shuō),在秋娘前面幾次呼喊“壯士”時(shí),兩名牽“布”的演員,表現(xiàn)出來(lái)也是癡情的樣子,更有甚者,由于對(duì)俄狄浦斯的仰慕竟然忘了牽“布”,其目的既是為了幫助觀眾理解劇情,也是用寫(xiě)意來(lái)傳情。
當(dāng)然,“融合”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關(guān)鍵還是要看對(duì)文本呈現(xiàn)的作用在哪里,修改版中就大膽去掉了兩大塊用“布”的地方,避免畫(huà)蛇添足。形式的創(chuàng)新,歸根到底還是為了讓觀眾把注意力拉回到我們要表達(dá)的主題思想上來(lái)。
事實(shí)證明,在后現(xiàn)代崇尚解構(gòu)、戲耍的今天,關(guān)于實(shí)驗(yàn)也不一定要走得很另類(lèi),一定要?jiǎng)?chuàng)造什么,推翻什么。大家都看不懂了,那是需要把故事講清楚了。觀眾只注重形式了,那說(shuō)明主題內(nèi)容弱化了。新的嘗試未嘗不可,但是對(duì)于戲劇的本質(zhì)切不可遺失。“融合”也是一種實(shí)驗(yàn)的選擇,值得我們更好地探討研究。
關(guān)于《命中注定》的再次思考,是在這次“當(dāng)代戲劇導(dǎo)演藝術(shù)與導(dǎo)演藝術(shù)人才培養(yǎng)國(guó)際論壇”后對(duì)自己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反思,也是從事導(dǎo)演教學(xué)工作多年后我對(duì)東西方舞臺(tái)藝術(shù)交融的實(shí)踐性思考。我想這次的大會(huì)對(duì)于這樣的爭(zhēng)論不應(yīng)該是某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答案的呼之欲出,更應(yīng)該是讓導(dǎo)演者沉下心去、潛心工作的要求。借用楊紹林老師在最后的總結(jié)式發(fā)言的一句話來(lái)對(duì)自己提出要求:“把任何一件事做到極致,也許問(wèn)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