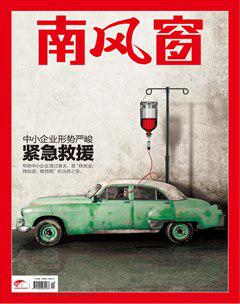那一片血淚橫飛的葉子
何焰

找一個寧靜的郊野客棧,在清晨聽著鳥叫聲,泡一杯茶,呷飲一口,似乎飲下了大自然的靈魂。寧靜、優(yōu)雅、閑適,是現(xiàn)代人對茶的普遍想象,也是現(xiàn)實期待。
沒有人想到,這可能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作家劉杰揭穿了這一誤會。積十余年歷史研究之功,他和賴曉東一起推出了《茶戰(zhàn)》系列書籍,目前《茶戰(zhàn)2》已經(jīng)進入書店。作者發(fā)現(xiàn),在西漢以來的2000多年歷史上,與茶葉如影隨形的,是血淚橫飛的戰(zhàn)爭史。在中國歷史敘述中,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循環(huán)沖突始終是非常重要的一塊,劉杰、賴曉東指出,這些沖突所圍繞著運轉(zhuǎn)的軸心,是茶葉。少數(shù)民族飲食結(jié)構(gòu)里缺乏植物,茶葉是保持族群健康的必需品,而茶葉只有中原王朝的百姓能生產(chǎn),于是,戰(zhàn)爭開始。
這條線索,能幫助人們以一種科學理性的方式,重新進入歷史。2018年9月,《南風窗》記者專訪了劉杰。
茶葉的主題是戰(zhàn)爭
南風窗:《茶戰(zhàn)》這套書,是歷史著作,至少它肯定不是純文學。作為一個文學家,你為什么會花費十余年去研究歷史和茶的關(guān)系?
劉杰:最開始只是因為茶好喝,不同產(chǎn)地、工藝、儲存、泡法,就有不同的味道、氣韻。
接著,是因為喝茶好玩。我在茶館里認識了一大群朋友,因為與某些人之間的感情鏈接,我真正地與茶結(jié)緣。跟老舍《茶館》里呈現(xiàn)的樣貌類似,里面三教九流、人來人往、高談闊論、呼朋引伴。茶館作為一個開展社交的公共空間,它比飯店要冷靜,比咖啡廳要有共享精神,是完全中國化的,社交屬性明顯的場所。
后來,因為我愛讀書,喜歡考究,發(fā)現(xiàn)茶不只是影響一個人、一群人,而是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歷史,甚至是過去的世界政治運行的重要物資。隨著研究的深入,當我慢慢地把茶葉從史書中摘出來,就發(fā)現(xiàn)2000年來,茶葉的主題都是戰(zhàn)爭,中國的歷史分明是一部建立在茶利益之上的戰(zhàn)爭史。這是一條理性的線索,貫穿于中國古代的政治、經(jīng)濟與軍事表象內(nèi)部,是理解歷史的一把鑰匙。
但同時百思不得其解,這么重要的線索,為什么卻被學者們統(tǒng)一地忽視了呢?
我想自己應該要做點什么。讓我下筆寫《茶戰(zhàn)》的直接誘因,是一部關(guān)于茶葉的紀錄片,導演找我?guī)兔π薷拇~。他對每一個鏡頭的執(zhí)著,對每一條線索的嚴謹,在情緒上影響了我,再次引起了我研究茶戰(zhàn)、茶貿(mào)易的想法。
絲綢是中國歷史上對外貿(mào)易的代表性商品,但實際上,絲綢是奢侈品,貿(mào)易的數(shù)量有限,瓷器不易運輸,實際貿(mào)易數(shù)量也遠遠少于茶葉。中國對外茶貿(mào)易的歷史長久,而且廣泛流傳,卻沒能留下太多的思索。
于是我寫了《茶戰(zhàn)1》和《茶戰(zhàn)2》,以后還會有3和4,以茶為線索,用系統(tǒng)的方法,來還原一部中國政治、經(jīng)濟、軍事的歷史。
南風窗:茶是一種飲料,咖啡也是一種飲料,茶對中國人很重要,咖啡對西方人也很重要。那么為什么咖啡在文化上沒有危機感,而茶葉的文化危機卻讓你那么憂心忡忡?
劉杰:茶,尤其是中國茶,正處在歷史上光芒最慘淡的時刻。
中國是茶樹的原產(chǎn)地,中國人飲茶、販茶,控制茶葉資源作為最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2000多年來因茶葉而引發(fā)了無數(shù)次戰(zhàn)爭,貫穿著自西漢至今的歷史。遠一點是黨項、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對中原農(nóng)耕民族的茶資源的剛性需求,讓“華”與“胡”不斷血腥沖突。近一點的鴉片戰(zhàn)爭,起因也是英國因購買中國茶葉耗盡白銀,只能用鴉片來平衡貿(mào)易。茶葉兩個字是和著血、伴著淚書寫出的一部博大歷史,它是飲品,是文明,是資源,更是苦難,不只是現(xiàn)代商業(yè)用來牟利的手段。
茶葉兩個字是和著血、伴著淚書寫出的一部博大歷史,它是飲品,是文明,是資源,更是苦難,不只是現(xiàn)代商業(yè)用來牟利的手段。
可惜,我們中國沒有一個人能夠把茶葉的根脈給刨出來,沒有一個人能講出這一片東方樹葉的真正文化內(nèi)涵,沒有一個人能講清楚茶文化背后的茶文明,反而盡是一些脫離了歷史背景的偽文化。要么是只談“神農(nóng)嘗百草”的遙遠神話;要么是為了商業(yè)利益“神化”茶葉,以便炒作;要么是各占山頭,包裝某個茶種,講一些細分的、單薄的茶葉故事。
咖啡和茶確實比較像。它出現(xiàn)得比茶要晚,但在歷史上的某一階段,咖啡也可以看作一種重要物資。作為西方飲品的代表,咖啡的文化挖掘,比中國的茶做得好太多了,像咖啡的起源、歷史、生產(chǎn)文化等等,都很豐富。中國的茶葉沒有這些,甚至可以說,現(xiàn)在的中國人早就忘了茶葉是什么了。
南風窗:這樣看來,茶的發(fā)現(xiàn)帶給中國文明以雍容氣度,也帶給中華民族以體格健康,但同時茶葉幾乎是一種不祥之物,多少血腥、災難都因它而起。如果中國人不發(fā)現(xiàn)茶葉,那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是否都要改寫?
劉杰:歷史沒有如果,它永遠是條單行道。
南風窗:雖然中國人重史,歷史著述豐富,卻往往呈現(xiàn)得像是史料的集成,缺乏科學的方法論。《茶戰(zhàn)》里面,有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是非常可貴的。茶葉這條線索,是不是試圖用理性的方式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嘗試?
劉杰:中國的史書多以紀傳、編年為主,少有以某一具體事物為線索,展現(xiàn)整個歷史進程的讀本。正因找到了茶葉這一戰(zhàn)略物資的線索,我的治史態(tài)度可以說是理性、客觀的。
所有的戰(zhàn)爭都是受利驅(qū)使,作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資源性物資之一,中國古代的對外關(guān)系史幾乎就是一部爭奪茶資源的戰(zhàn)爭史。每一個歷史人物都僅是歷史的過客,而茶葉是自古至今滔滔不廢的,正因為看透了這一點,我就可以冷靜地考據(jù),上下左右地去研判每一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而盡量避免臉譜化的、零碎的歷史撰述。
我寫《茶戰(zhàn)》,運用的是小說語言,但這種語言風格是基于扎實、準確的史實梳理之上的。正因為史料的可靠性和語言的輕松感,才能讓《茶戰(zhàn)》成為一個能夠快速傳播的以茶說史的讀本。
中國思維和茶的黯淡
南風窗:《茶戰(zhàn)》系列揭示了一個真相—某種程度上說,茶葉是歷史上中原王朝內(nèi)政外交的一個治亂之源,是政治、經(jīng)濟、軍事轉(zhuǎn)動的軸心。過去研究茶文化的學者,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深入看待歷史,您是怎么發(fā)現(xiàn)這條線索的,過去它為什么被人們忽略?

劉杰:以茶為切入口,來談政治經(jīng)濟史的,我不是第一人,但我應該是目前為止,第一個比較系統(tǒng)和完整地把茶葉當作密碼,來探尋中國政治、經(jīng)濟、軍事歷史的人。
中國人為什么忽視茶葉呢,我覺得跟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有關(guān),也跟現(xiàn)今中國茶的相對沒落有關(guān)。
先說中國人的思維,是典型的經(jīng)驗主義,經(jīng)驗主義的特征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可以看四大發(fā)明里的指南針,與其說中國人發(fā)明了指南針,不如說發(fā)現(xiàn)、應用了指南針,因為其科學本質(zhì)—磁力場是外國人發(fā)現(xiàn)和定義的,中國人“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且點到即止,不往深處探尋。茶葉也一樣,我們飲茶2000多年,對于茶葉的理解仍舊是懸浮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不接地氣的。
而中國茶葉的沒落,跟鴉片戰(zhàn)爭相關(guān),也與全球化相關(guān)。在19世紀之前,中國的茶葉仍在世界上占據(jù)壟斷地位,但在19世紀40年代,英國人因西方對茶葉的需求,貿(mào)易中白銀出超嚴重,一方面想出損招,向中國輸入鴉片、發(fā)動戰(zhàn)爭,另一方面帶著中國茶樹種,領(lǐng)著12位中國茶農(nóng)、制茶匠、篾匠出國種植,先后在印度的大吉嶺、阿薩姆試種成功,并大面積推動茶葉產(chǎn)業(yè)的工業(yè)化進程,完全打破了中國茶的世界貿(mào)易壟斷地位。
目前來說,國內(nèi)茶葉市場呈現(xiàn)種種亂象,又因為種種貿(mào)易壁壘,中國茶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份額很小。這種暗淡,也在某種程度上讓中國人忘記了中國茶的歷史。
南風窗:作為茶葉原產(chǎn)國,中國茶業(yè)的工業(yè)化進程為何始終難以展開,遠遠落后于國際?
劉杰:大吉嶺、阿薩姆茶葉雖源自中國,但其工業(yè)化生產(chǎn)、標準化經(jīng)營的模式,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對中國茶葉產(chǎn)業(yè)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也曾以安徽祁門紅茶為主要產(chǎn)品,主力推動過中國茶葉的工業(yè)化,但是由于出口受阻,只能在國內(nèi)尋找市場銷路,不得不再改回到手工制作。
中國人認為茶是有個性的。這種個性一旦與人聯(lián)結(jié),因人而異,便展現(xiàn)出一種藝術(shù)性。藝術(shù),注定是與產(chǎn)業(yè)化、標準化難以共生的詞匯。
在當時,中國茶工業(yè)化的先機已失,再度從英國人手中搶回市場的難度巨大,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當時的中國社會因為長期的閉關(guān)鎖國,處在較為落后的傳統(tǒng)農(nóng)耕經(jīng)濟時代,在技術(shù)上難以快速地向工業(yè)化轉(zhuǎn)型;二是經(jīng)歷兩次鴉片戰(zhàn)爭、甲午中日戰(zhàn)爭以及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之后,國家主權(quán)維艱,經(jīng)濟斷崖式崩潰,幾乎完全喪失了在國際茶貿(mào)易中的主動權(quán);三是中國人的商業(yè)思維守舊。這里的守舊一方面是強調(diào)工藝獨特性,對不同茶種堅持“差異化”制作、營銷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是對標準化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的不信任,不愿意讓利。
而在近代,從商業(yè)、產(chǎn)業(yè)角度來看,中國茶業(yè)處于一個分散的狀態(tài),茶企7萬多家,彼此之間無序競爭,以“小批量、多品種”為主的零碎現(xiàn)狀,導致了資本難以聚焦茶業(yè)。而從國際貿(mào)易角度來看,一系列人為制定的貿(mào)易壁壘,阻止了中國茶葉與世界茶葉的接軌。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我個人認為的角度,這也是一個矛盾點。中國人愛茶,茶因地、因時、因人而展現(xiàn)出不同的質(zhì)感,讓中國人認為茶是有個性的。這種個性一旦與人聯(lián)結(jié),因人而異,便展現(xiàn)出一種藝術(shù)性。藝術(shù),注定是與產(chǎn)業(yè)化、標準化難以共生的詞匯。這種中國傳統(tǒng)中的對茶的藝術(shù)性的堅持,也在某種程度上讓茶業(yè)難以快速地工業(yè)化。
茶葉貿(mào)易和中國歷史
南風窗:按照你的梳理和發(fā)現(xiàn),茶葉其實是連結(jié)漢族政權(quán)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紐帶,是一種戰(zhàn)略資源,也是一種硬通貨,因而是經(jīng)濟控制的手段,這是不是意味著,過去帝國時代存在的華夷秩序、朝貢體系,其實也都和茶葉緊密關(guān)聯(lián)?能否舉例說明?
劉杰:從五代時期后周皇帝柴榮開始,茶葉成為了國家專控物資,并作為控制外族的重要政治手段,歷代史書后附的《食貨志》中都記載得非常清楚。
現(xiàn)今陜西有一種茶,名叫茯茶,名稱即是從古代“附茶”轉(zhuǎn)換而來。附茶是相對于官茶來說的,茶農(nóng)種茶,十要繳八,官茶是政府拿走的八成,剩下的兩成茶就是附茶。
而中原主動向外輸出茶葉來換取和平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文成公主和親。往后較為著名的是“澶淵之盟”,宋真宗趙恒以貢納歲幣、供給茶葉,來向周邊游牧民族換取了北宋時期近九十年的和平。
南風窗:茶葉貿(mào)易和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歷史緊密關(guān)聯(lián)。對茶葉資源的壟斷,讓中國即便在經(jīng)濟形態(tài)和生產(chǎn)力都落后很多的情況下,仍然能在貿(mào)易中占據(jù)主動。這會不會給變革帶來惰性?
劉杰:歸根結(jié)底,茶葉只是一種物質(zhì)資源,它能承擔的意義有限。頂層決策、農(nóng)耕文明、國民心態(tài)導致的閉關(guān)鎖國,才是真正的歷史動因。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難道璧就有罪嗎?
茶葉在不同的時機,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就是不同的工具,僅此而已。契丹曾從中原購茶,作為戰(zhàn)略性資源,來控制周圍游牧民族;宋真宗趙恒簽訂“澶淵之盟”,向少數(shù)民族貢納歲幣,以茶和其他財物來換取宋朝幾十年和平,這些也都是例子。
不只是樹葉
南風窗:問現(xiàn)在的年輕人喝什么茶,他們可能告訴你,“只喝奶茶”。隨著城市化、全球化的發(fā)展,茶葉飲品市場,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任何一種文化,都應該根植于生活,有人喝茶,有人愛茶,才有茶文化。對于飲茶人漸少的中國茶文化現(xiàn)狀,你怎么看?
劉杰:過去的中國,茶文化非常豐富,貫穿于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年齡段。從街邊的大碗茶,聚集著販夫走卒,站著喝,喝解渴茶;到老舍的《茶館》,四面八方,三教九流,莫談國事;再到上等茶樓,講究茶的品質(zhì)、談話環(huán)境;最后是皇家喝茶,講究茶品、茶具、字畫、家具等等。

茶的好處是什么呢,解渴生津、可俗可雅,最重要的是,以喝茶為核心,維系著一個交流、共享的公共空間。喝茶的人不可能不聊天,言語與心靈相連,茶葉就是提供機會的媒介。茶文化連結(jié)著很大一部分的中國人,里面有幾千年的中國共同記憶。
但隨著城市化、全球化的發(fā)展,不同的飲品,從不同的階層方向,沖毀了茶文化的根基。再也沒有街邊的大碗茶,現(xiàn)代人買瓶礦泉水就走;再難尋到茶館,南來北往的人習慣于尋找咖啡廳作為落腳、暫歇的地方。
中國茶飲的沒落,其實是中國式樣的生活方式的沒落,茶所代表的共享、交流、人情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被咖啡、奶茶調(diào)飲等飲品背后的時髦、獨立、快捷的生活方式,侵略式地取代了。
中國茶飲的沒落,其實是中國式樣的生活方式的沒落,茶所代表的共享、交流、人情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被咖啡、奶茶調(diào)飲等飲品背后的時髦、獨立、快捷的生活方式,侵略式地取代了。
但這正常嗎?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走上街頭,只找得到麥當勞,找不到中餐館,那中國人的歸屬感還在嗎?全球化的腳步下,中西并存,才是正常的。但我們今天上街,茶館確實是難尋了。也就是說,在飲品中安置的中國文化,這部分的共同記憶,已經(jīng)可惜地、可悲地、猝然地,消逝掉了。
借用老片子《溫州一家人》里面的臺詞,兒子長大了,有一天看見父親喝茶,對父親說:“我不喝茶,我喝的是咖啡。”父親問兒子:“咖啡能解渴嗎?”這也是我想說的話。
南風窗:中國的現(xiàn)代化尚未完成,仍在繼續(xù)。在當下這個時代,茶葉對社會演進還有影響嗎?
劉杰:在當前的現(xiàn)狀下,與其指望茶葉繼續(xù)推動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不如寄希望于現(xiàn)代化帶動中國茶葉的振興與發(fā)展。
從政治角度來看,茶葉的政治屬性已經(jīng)逐漸淡化了,它已經(jīng)逐步落實到其國民飲品的本質(zhì)上來了。由茶葉所能聯(lián)想起的,不再是頻繁戰(zhàn)爭的表象,而是關(guān)乎民生的,幾千年交融的生活的必需品。茶是歷史的血淚,是傳統(tǒng)的精髓,同時也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茶葉并不曾枯萎,也隨時蘊藏著新生的力量。
從商業(yè)角度來看,中國的茶葉產(chǎn)業(yè)急需變革,無論是工業(yè)化進程的加快,還是分工化生產(chǎn)向標準化生產(chǎn)的變遷,茶葉企業(yè)的未來必定面臨一次重大改組,以改變目前中國茶葉市場的尷尬處境。如果中國茶葉再次對社會的演進產(chǎn)生影響,只有一種可能性,即以產(chǎn)業(yè)的方式,以茶業(yè)制造經(jīng)濟機會和生活機會,進而影響中國的貿(mào)易、政治的發(fā)展格局。
南風窗:你寫《茶戰(zhàn)》系列,想為讀者們留下何種歷史觀照呢?
劉杰:簡單的一句話:要知道什么是茶。對于中國人來說,茶葉不只是一片樹葉,它早就流進了中國人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