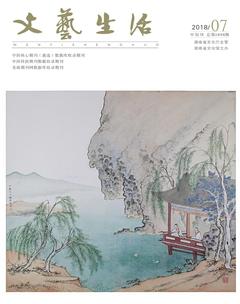文革資源在當代雕塑中的再運用
李平平
摘要:文革資源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成為某些藝術家創作的重要題材,并且它體現了一個特定時期的文化需求,在中國人的記憶中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許多文革資源駐扎在藝術家靈魂深處,在其創作中不斷出現,展示的不只是民族文化,社會制度,更是對歷史問題的反思。文革資源在當代雕塑創作中的再運用,可以讓當今大眾重新解讀歷史,引發人們的思考。
關鍵詞:文革資源;當代雕塑;文化;再運用
中圖分類號:J3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20-0121-01
文革時期許多資源造就了當代無數的優秀雕塑作品,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物和藝術價值。藝術作為時代的反饋,文化的再敘述,挖掘文化大革命資源的方式層出不窮。文革資源的再次呈現讓藝術家和當代人理智的審視文革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
一、王廣義——對時代的信仰
王廣義以中國東北的一個鐵路工人兒子的身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他用《大批判》系列獲得了批評家和國際藝術市場的關注,成為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標識性人物。
《唯物主義者》是一組由12個來自宣傳畫中的工人、農民和士兵造型所組成的雕塑群,這也是王廣義引以為傲的作品之一。根據王廣義的敘述,這些宣傳畫圖片揭示了人民這一主體,他們行為中的憤怒來自于思想中的信仰。通過這些雕塑,藝術家嘗試將這些形象塑造為一般的人民。王廣義說道:“‘唯物主義者在這里有一種語言學上的關連性,這個詞準確恰當的概括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我想使用‘唯物主義者來建構一種雙重的暗示,以使觀者產生雙重的文化聯想。
王廣義說《唯物主義者》這個作品是對曾經的一種信仰狀態的記錄。他說:“無論那種信仰現在看來是否荒唐,但在藝術家看來,信仰的面孔是有魅力的,現在你再也看不到這樣的面孔了。”對于曾經的那個信仰時代,王廣義的情感很復雜:“我不能簡單地說我懷念過去,也許我只能這樣表述:那時候,時代不勿忙,誘惑不多,能常常讓人定下神來,那是一個好時代。”
二、瞿廣慈——形象的圣愚化
革命和藝術是不可分割的一層關系,革命需要藝術進行自我救贖,比如將革命浪漫化。瞿廣慈他選擇了革命的象征雕塑,像社會主義小說中的模范革命夫妻等等。瞿廣慈用圣愚化來表達他的雕塑作品,其實是對于前世行為的一種諷刺,其要表達圣愚化的形象主要來自文革時期,比如政治象征性的公共雕塑“工農兵”塑像和毛澤東的招手像等等,這些帶有濃重文革氣息的資源成為瞿廣慈雕塑創作中的重要靈感來源。
雕塑作品在瞿廣慈的手下,他們仿佛都進入一種革命后的催眠狀態。瞿廣慈雕塑創作中的圣愚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形體的圣愚化,比如身材臃腫、動作笨拙、眼神和表情處于無知無覺的夢游或者催眠狀態。二是將雕塑創作形象角色化。比如將紅衛兵帶入“最后的晚餐”,成為一個文革的現代版等。三是把這種愚癡浪漫化,比如紅衛兵笨拙地拉小提琴,農婦笨拙地模仿擲鐵餅等。對瞿廣慈而言,他試圖使圣愚傾向于一種拙樸和可愛化的語言形象,而且革命版的圣愚形象并非只是一種雕塑語言的形式實驗,它更主要的意義在于,從被灌輸的文化記憶中剝離出六十年代一代人的革命的浪漫化。這在現代性的意義上帶有某種精神力量,比如對于終極和絕對精神的追求、烏托邦和進步主義的觀念、對純真和善的力量的信仰等。
三、隋建國——解構曾經的威權
隋建國1956年出生于山東青島,童年正值文革時期,所以他用作品記錄下自己的感受。他的藝術作品主要通過雕塑實踐來對觀念和形態進行思考和拓展。隋建國的雕塑作品尺寸很大,有紀念碑式的夸張和震撼效果,這種紀念碑式的雕塑創作通過直面觀眾,重建了與歷史偉人的關系,將它們變成可見的視覺文化,而不是歷史的是消逝。
“中山裝”是《衣缽》系列最典型的標志,在中國現代文明史上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中山裝”系列是藝術形態極強的藝術表達,中山裝和軍裝是文革時期革命的標志,但作為藝術家的隋建國首先是從藝術的經驗切入這個深刻的文化課題。這件《衣缽》是隋建國的成名作,創作于1997年,是藝術家“反思現實”的結果。作為藝術家,隋建國開始思考自己與社會制度、精神領袖的關系,也在琢磨用怎樣的方式呈現這一切。“中山裝”成為了最后的選項。這是個戲謔的瞬間,象征威嚴的中山裝可以被穿著時尚的年輕人隨意觸碰,這或許是隋建國心底隱秘的欲望,慫恿任何人幫助自己解構曾經存在的威權。
因此,隋建國的《衣缽》系列是一種歷史的思考,文明的反思,就象他把中山裝置于巨大的神龕一樣,他用這種中國人崇拜祖先的傳統方式讓我們正視自己的遺產,無論是曾經激勵過我們還是現在束縛著我們。
四、結語
將文革資源作為創作題材更有利于實現消除中西雙方的閱讀障礙,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實現自己的文化價值和意義的追問。對于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文革資源在雕塑中的再運用也讓當代人重新了解和審視中國文化史和前輩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