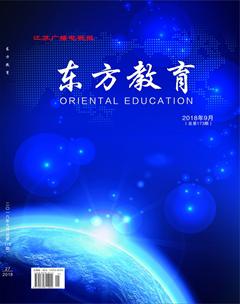淺析《西廂記》崔鶯鶯人物形象
摘要:《西廂記》是元雜劇的代表作之一,崔鶯鶯的人物形象更是成為中國戲劇女性形象的經典代表。劇本對于崔鶯鶯陷于矛盾的心理刻畫更是深入骨髓,反映出封建社會時期年輕人沖破“禮”的束縛勇于追求愛情的精神力量。
關鍵詞:崔鶯鶯;人物形象;矛盾掙扎
引言:
《西廂記》取得了中國戲劇史上的重要突破,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也是細致入微,尤其是對崔鶯鶯的塑造更是栩栩如生。包括戲劇在內的一切藝術,都是把形象性作為自己審美特性的基本標志之一,一切藝術都必須通過似乎目可見、耳可聞、手可觸的感性形象打動人,通過能夠傳達出人物或事物的內再神情的活的形象感染人。[1]這是對藝術作品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藝術品價值的內在手段。
在《西廂記》中崔鶯鶯至真至純又滿懷“花落水流紅,閑情萬種”的感傷。一方面對張生好感與好奇,另一方面迫于封建思想教育的束縛,還要提防監管的紅娘。在三重壓力下,鶯鶯的鮮活生動展現的淋漓盡致——對愛情無限向往,卻羞于承認事實;對自由的無限渴望,又畏于封建禮教的強壓;對生命的無限熱忱,卻陷入懷疑和猶豫。她總是若進若退地試探獲得愛情的可能, 并常常在矛盾的狀態中行動:一會兒眉目傳情, 一會兒裝腔作勢;才寄書相約, 隨即賴個精光[2]。正是因為這種陷于矛盾與自我矛盾的性格特點,才能引發出動人心弦的復雜劇情。
一、傾國美貌的驚艷效果
在戲劇藝術中,人物的第一印象的極為重要。 如《紅樓夢》中王熙鳳“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出場方式,人物特點噴涌而出,日后對人物的見解有更直觀的表現。對于《西廂記》中鶯鶯的第一次出場描寫是“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肖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3],至此一個滿懷心事、無人訴說的少女落落而出,同時這種感傷的情緒更為后文崔張二人的愛情線索做鋪墊。《西廂記》中崔鶯鶯的外貌是通過對張生見到鶯鶯的反應進行的側面描寫。《驚艷》中張生游歷到普救寺時第一次見到崔鶯鶯時遠遠的觀望便驚呼“則著人眼花瞭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4],這種夸張的描寫將觀眾瞬間吸引,正當所有人對“眼花繚亂”的好奇達到頂峰時,鶯鶯的細致描寫才逐層引出,戲劇結構有條不紊又避免華美詞句帶來的審美疲勞。當張生沉浸于對鶯鶯美貌的驚嘆時,一句“寂寂僧房人不到, 滿階苔襯落花紅”更是使得張生更情不自禁“我死也”,不但表現張生對鶯鶯的感情始于貌美忠于內在,又恰好反映出張生“傻角”的性格,在演出中更是帶來了特色的喜劇效果。
《鬧齋》是對崔鶯鶯的形象進行近距離描寫,“大師年紀老,法座上也凝眺;舉名的班首真呆勞,覷著法聰頭做金磬敲。”[5]鶯鶯傾國傾城的美貌連作法事的和尚都目不轉睛,竟把法聰和尚的頭當作木魚來敲。“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沒顛沒倒,勝似鬧元宵”[6]——這個“鬧”字,是崔鶯鶯將包括張生在場的所有人都俘獲了。王實甫更是借和尚特殊身份的人物反應來表現鶯鶯的絕世美貌,不僅為下文張生對鶯鶯的極盡追求做鋪墊,更是達到了一種與之前所描繪不同的喜劇效果。也正因此,觀眾才能從更客觀的角度認識鶯鶯的美。
二、聰慧的內在賦予
《西廂記》中張生對崔鶯鶯一見鐘情,始于對鶯鶯外在形象的吸引,卻忠于對鶯鶯深厚的文化底蘊。《聯吟》中“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張生將自己的落寞孤寂與咫尺天涯的鶯鶯化與濃濃夜里,空留月景無心欣賞。面對張生試探,鶯鶯立刻便唱和了一首詩:“空閨久寂寞, 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這首詩也恰好與鶯鶯之前的心境相符,真誠袒露自己心聲,字字訴衷情。
王實甫對于崔鶯鶯才華的描寫處處可以體現,詩文是崔鶯鶯與張生之間感情聯系的第二個重要的“紅娘”。正是二人相似的文化素養和才情,兩人才能彼此吸引,兩情相悅。
三、敢于反抗封建禮教的典型形象
《西廂記》中崔鶯鶯是封建相國家族的小姐,同時也是一位情竇初開的少女,她渴望愛情又羞于傾吐,但步入愛河后感情一發不可收拾。鶯鶯聽聞紅娘“那壁有人,咱家去來”的時候,有[旦回顧覷末下]六字舞臺提示,內在的心理活動決定了外在的言行,而外在的言行往往是人物內心活動的流露。[7]正是鶯鶯這個剎那間下意識的舉動,被情迷顛倒的張生更是以為成對方意送秋波。在連自己婚姻都無法自己掌控的封建社會環境下,年輕男女若是建立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關系根本不可能,崔鶯鶯的身份已經注定她這半生的命運。可她對愛情的態度是執著而又熱烈的,正是這種至真至純反抗意識的勇氣才最打動人心。
經過“賴婚”之后,鶯鶯對張生的感情更深刻,處理感情卻更謹慎。以崔鶯鶯為代表人物形象的反抗意識并不是在自然狀態下就存在,而是受到強大的社會壓迫之后才慢慢激發出來。雖然崔鶯鶯并沒有與封建家長做最后決裂,在反抗的過程中帶有軟弱性,但是人物形象卻正因她的軟弱更真實飽滿。
四、人物心理矛盾自我糾結
戲劇之所以引人入勝使人著迷,魅力在于其矛盾沖突設置。構成戲劇沖突的手段有兩種:一是利用人物同外界環境的矛盾構成戲劇沖突,一是利用人物內心世界的矛盾構成戲劇沖突。[8]在《西廂記》中,崔鶯鶯近二十年身受封建家族“三從四德”的思想教育,這些牢籠在逐步的封鎖她的獨立意識,使她成為封建社會中眾多犧牲品之一。于是鶯鶯在追求封建社會下的愛情時,不但要和封建勢力的代表斗智斗勇,最難的是還要和自己的內心作斗爭。她要戰勝社會環境的外部壓力固然不易,戰勝自己則是難上加難。
《鬧簡》和《賴簡》深入的表現了鶯鶯內心自我矛盾的掙扎過程。張生決定走,她主動給張生寫信挽留,張生回信,鶯鶯又突然怒罵“小賤人,這東西那里將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敢將著簡帖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等東西?告訴夫人,打下你個小賤人下截來!”[9]紅娘見勢便說要把這簡帖直接拿給老夫人看,“[旦做揪住科]我逗你耍來。”鶯鶯這種突然變臉其實正是內心矛盾自我糾結的突出。一邊是對封建禮教的恪守,一邊是對自由愛情的愿望,鶯鶯的兩個性格在不斷的自我掙扎和選擇,這也是鶯鶯之所以“作假”的原因,自我本我與超我的不斷沖突和碰撞,也是鶯鶯對張生忽冷忽熱、欲拒還迎的重要原因。[10]
結語:
令人欣慰的是在《西廂記》的最后,張生與崔鶯鶯終于戰勝了封建禮教,完美的詮釋了作品“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主題,劇作家的細致描寫與寫作深意更值得后人研究,崔鶯鶯是一位大膽與封建禮教斗爭的貴族小姐人物,更是一位洋溢自由青春的純真少女。她的人物“美象”已然是中國戲劇史的一位形象典范。
注釋:
[1][8]:王兆才,情與理的沖突——談《西廂記》中崔鶯鶯形象的塑造,1994
[2]:蔡雪嵐,《西廂記》鶯鶯形象分析,2006
[3][4][5][6][9]:王實甫,《西廂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7]:王兆才,《西廂記》:寫出人物靈魂的深
[10]:胡艷平,自我本我超我——《西廂記》中崔鶯鶯的精神分析
作者簡介:孫叢(1993.2——),女,漢族,籍貫:山東德州,山東藝術學院戲劇學院,16級在讀研究生,碩士學位,專業:戲劇與影視學,研究方向:戲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