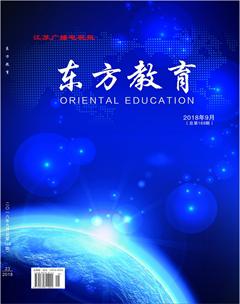從歷史的角度淺析山水畫的繼承與創新
引言
山水畫是中國畫中相對于花鳥畫和人物畫,歷史脈絡最清晰,傳承資料最完備,歷朝歷代留存作品最豐富的一個畫科了。山水畫的面貌和技法也在傳承和發展中越來越豐富。然而繼承傳統和推陳出新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歷代繪畫從業者。一直到現在山水畫的學習過程中該不該大量臨摹傳統作品和如何去創新的問題仍然被業內大量的討論。但言論大多有些極端,要么認為應該撇棄傳統,學習傳統等于泥古不化。要么認為一定要像傳統中某家面貌才是正統的山水畫作品。其實繼承和創新之間并無沖突,臨摹是與古人對話,把握古人山水畫作品內在蘊含的規律,再去觀察古人每家面貌上的創新,就能為自己的創作打開一條思路。
一、我們稱之為傳統的繪畫,其實在當時也屬于現代繪畫
用歷史的角度把時間軸拉長來看待繪畫的繼承和創新,不難發現每一個時期的人都是生活在當下的,我們現在的每一段傳統對于當時的人來說都是現代,當時的繪畫都是現代繪畫,但是為什么我們現在看當時的現代繪畫屬于我們認知的傳統范圍呢?第一點是時間限制,一段大的歷史背景因其社會的發展程度的限制,這一個時期的繪畫在題材或大的風格上都會有相對接近的特征。第二點則是他們的作品都符合中國畫中山水題材傳統的審美規律和造型方法,這些內在的東西才是中國畫的核心。歷史大浪淘沙般的把每個時期平庸的作品漸漸淘汰,能留下來的并且被業內承認和讓大家所熟知的作品無疑在當時就屬于頂尖范疇的作品。而我們當下的所謂現代繪畫中優秀的作品幾百年之后也將成為未來畫家口中的傳統。
二、推陳出新是在能理解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
推陳出新顧名思義是要將陳舊的東西推開,將新鮮的東西加入進去。既然要“推陳”那么就應該明確“陳”在哪里才有的推,不然將之前的東西一股腦否定掉再由自己憑空創造出一個新的面貌,這樣的東西是立不住的。不如將前人的寶貴經驗學習過來之后再逐漸加入自己喜歡的東西,臨摹和創作穿插進行,實時改進自己的畫法和加深自己對古畫的認知,一點一點的發掘傳統作品中對山水畫的理解,真正的做到與古人對話,當然這個過程是沒有終點的,這樣長久下去自然便會形成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特面貌,并不用強求為之,也不可強求為止。《金剛經》中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果一味的想要去創造新的面貌和新的技法難免會入歧途,讓自己的作品顯得怪異而不是新奇。
當然一味的強調傳統,不去思考自己的個性所在也是不可取的。如今也不乏泥古不化,談“新”色變的畫家,沉浸在某家面貌中無法自拔,并且批判一切不像古人的作品,這樣的情況也是不真正了解傳統的表現。元代趙孟頫強調古意,認為“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賦色濃艷,便自稱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他批判當時元朝畫家追求精巧、艷麗的風氣,要殆盡宋人筆墨,強調學習唐人。趙孟頫強調學習唐人也是學習唐人用筆、用墨、用色的方法和學習唐人作品的氣息,并不是強調學習唐人面貌,從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這點。他雖說自己作畫“簡率”但實則是謙虛之詞,他的《鵲華秋色》用筆細密,賦色淡雅,根根小草都勾勒的十分精細。《浴馬圖》中人物和鞍馬畫的精細入微,馬蹄入水產生的顏色及虛實的變化都表現的十分精妙,卻不覺過分雕飾,顏色鮮艷卻不覺艷俗,發現前人已總結出來的優秀經驗并加以運用。這就是他所強調的“古意”。
三、與其談“創新”不如談“出新”
創新一詞給人的感覺是憑空創造一個新鮮事物,而出新一詞則更符合繪畫在尋求自己獨特面目時的過程。去學習傳統繪畫中規律性的經驗,比如構圖規律、疏密規律、山石樹木的造型規律、用筆用墨的節奏、賦色中色與色的關系等等,都是直接能用到自身創作中去的東西,比自己無中生有要快而且這些經驗經過古人長時間的實驗已經十分完備,同時也比完全照搬古人山石樹木要來的自由和輕松。生無所住心讓自己的心境平靜下來,踏實的去學習傳統,再探尋本心,真誠的詢問自己的內心到底喜歡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在傳統之上發現新的課題,以傳統為基礎去研發新的課題。在這個過程中持續一段時間之后就會發現之前長期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新面目已經有雛形出現了。
學習傳統并不是為了增加自身繪畫時的包袱,而是為了達到創作時“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越親近傳統就越堅定自己所出的“新”是有根基的,內心堅定后在創作中才能不被遲疑所擾,真正達到“心無所住”,下筆沉著痛快。中正的去對待傳統的學習和自身的創作,便可創作出屬于這個時代的山水畫作品。
作者簡介:
楊澤瀚(1993.5—),男,漢族,籍貫:河北邯鄲人,天津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16級在讀研究生,碩士學位,專業:現代山水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