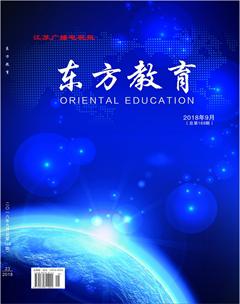刑法311條新增內容的客觀方面分析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對刑法原第311條進行了修改,增添了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情況的明知而拒絕提供,本文擬從該罪的立法背景出發,分析其客觀方面,以期對相關的認定分析有所幫助。
關鍵詞:拒絕提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罪;刑法修正案九;反恐怖主義法
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恐怖主義活動嚴重影響到了各國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這點在我國也不例外。同時,極端主義如影如魅,在我國,尤其是邊疆地區,悄無聲息地滋長起來,其不但以嚴重不理智的思想特征嚴重影響到我國的民族、宗教政策,而且與恐怖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情況下為后者起到思想動員的作用。因此,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下稱《修九》)出臺了大量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將許多相關行為首次納入刑法處罰范圍,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同時,為了提高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修九》將第311條修改為“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或者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行為,在司法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情況、收集有關證據時,拒絕提供,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從罪狀的描述來看,本罪是個純正的不作為犯罪,其只能由不作為構成。 作為刑法中少有的幾個純正的不作為犯罪之一,本罪的客觀表現與其他罪名有著較大的差異,同時,本罪是《修九》在加強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背景下出臺的,因此,對于本罪客觀方面的把握,既要從條文中分析,又要參考2015年12月出臺的《反恐怖主義法》(以下簡稱《反恐法》),綜合兩者來進行把握。
根據罪狀的描述,本罪的客觀表現可以拆解成三個要素:拒絕提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情況及情節嚴重,同時,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本罪的客觀表現,下文還將對本罪與相關犯罪進行比較。
一、拒絕提供
拒絕提供的時間是在司法機關向行為人調查、取證時,即不主動向司法機關報告自己所掌握的有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的不構成犯罪。而依據刑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上述中的司法機關是指有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和監管機關,這里有個疑問,那就是如何看待已被監管的了解他人犯有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情況者拒絕向監管機關提供相關證據的情況。比如,甲從乙處購買大量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宣傳品時常聽乙吹噓自己當年的恐怖主義“事跡”,后甲因犯有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而被判刑,在獄中監管民警向其了解相關情況時其拒絕配合,甲是否構成此罪?有人主張此類行為不應認定為本罪,但筆者認為,第一,從詢問主體來看,此處的司法機關應包括監管機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危害性極大,針對這些犯罪一向主張打早打小,而本罪作為配合打擊這些的保障,其設立就是為了督促知情人盡量積極地配合司法機關反恐反極端主義工作的展開。第二,本罪中設立的詢問主體已經限縮到“司法機關”而無法再行限縮,因此,依據罪刑法定原則,就應當嚴格按照刑法第九十四條中的規定進行認定。綜上,只要是司法機關進行詢問而拒絕提供的,就應當認定為此罪。
這里的拒絕提供,包括明示拒絕和默示拒絕。前者是通過各種方式直截了當地向詢問取證的司法機關說明自己不愿提供,可以口頭,可以書面,可以當面,也可以通過打電話、發信息等,只要表達出拒絕的意愿即可。后者是通過各種消極逃避來表達出自己拒絕的意愿,比如利用各種借口對調查取證推諉拖延,得知司法機關要調查取證而躲避外出等都是此類。另外,由于法條要求的是公民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的配合義務,對于所提供的證據、情況未作要求,因此,即使所提供的證據、情況對司法機關破獲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案件沒有作用,也不能認為其拒絕提供。
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情況
本罪中要求拒絕提供的是有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證據、情況。就證據而言,很好理解,基本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中規定的證據門類進行理解即可。就情況而言,雖沒明文規定,但此處應比照證據進行理解,即能為司法機關防止和打擊兩類犯罪提供有意義幫助的線索,其與證據有同等價值,避免對此進行擴大解釋。
此處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應當參考《反恐法》的精神進行理解。《反恐法》對恐怖主義的表述為“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財產,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以實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等目的的主張和行為”,暴力手段是其表象,政治目的是其實質。《反恐法》對極端主義未進行明確的概念界定,只劃定了范圍,“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義或者其他方法煽動仇恨、煽動歧視、鼓吹暴力等極端主義”,并說明其為恐怖主義的思想基礎。前者或是直接表現為恐怖襲擊,或是對恐怖組織、恐怖主義犯罪分子、恐怖主義主張等進行宣傳等,總體上認定不會非常難。相較而言,后者就更為隱晦些,且從表述中看,其思想性的特征更為明顯,通常表現為對宗教、民族等觀點的歪曲性煽動,經常伴隨有“圣戰”、“異教徒”等歧視性、暴力性的詞匯。
根據上述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分析,首先,刑法中已有的帶有“恐怖活動”、“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字眼的犯罪理所應當地應被認為是此罪規定的兩類犯罪,即第一百二十條及一百二十條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上述罪名都不同程度上利用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所以刑法將這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其次,對于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比如他人在犯有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的同時也犯有殺人放火等嚴重罪行的,或是個人自發實施帶有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色彩的暴力犯罪,只要他人有證據證明自己確實不明知該人進行暴行所持有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主張,雖然司法機關對此進行調查取證但拒絕提供的,不應認定為本罪。這是為了防止將社會中出現的一般惡性暴力案件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案件相等同,出現打擊面擴大化的局面。最后,本著刑法的謙抑性,其他諸如洗錢罪等雖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有密切聯系但刑法另有明文規定的犯罪不應認定為上述兩類犯罪,防止罪名的無限擴大。
三、情節嚴重
此處的“情節嚴重”應該指的是由于行為人拒絕提供證據、情況而造成嚴重后果,具體表現為:首先,從司法機關公信力和社會評價看,因為行為人拒絕提供致使司法機關無法對犯罪分子進行定罪量刑或是使其承擔所有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的應算入其中;其次,因為行為人拒絕提供致使犯罪分子實施了嚴重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罪行的,比如出現犯罪分子實施了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恐怖襲擊,應算入其中;最后,參考一些數額犯中對“情節嚴重”的規定,此處還包括拒絕提供多人或多宗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或情況。
四、與相關犯罪的界限
(一)與窩藏、包庇罪的界限
首先,本罪要求行為人明知他人犯有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而后者只要求明知他人犯罪即可。其次,本罪的行為只能表現為不作為,即拒絕向調查取證的司法機關提供證據或線索,而后者通常表現為作為,即向犯罪人提供住所、財物供其逃匿或是為其作偽證以包庇罪行。最后,本罪的時間點可以在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預備、中止、實行及其以后,并且要求是發生在司法機關因調查取證相關犯罪向行為人取證調查時,而后者只能發生在被窩藏、包庇人犯罪發生之后,若發生在此之前則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綜上所述,若行為人在司法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證據、情況時,其提供假證的,應當認為行為人構成包庇罪。
(二)與其他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界限
首先,從侵犯的客體來看,前者侵犯的是正常的司法活動秩序,而后者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其次,從行為方式來看,前者只能以不作為的方式表現,而后者通常以作為的方式表現。最后,從兩者的關系來看,后者是前者的上游犯罪,若無后者犯罪則前者不構成犯罪,同時前者的行為人不能參與到后者的犯罪環節中來,否則行為人可能成為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共犯。
總之,本罪是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前置化立法背景下的產物,但由于刑法的謙抑性而對犯罪構成要件進行了限縮,因此在對本罪的理解中要注意與其他犯罪,尤其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相區分,以實現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此類犯罪的打擊。
參考文獻:
[1]趙秉志.杜邀.我國懲治恐怖活動犯罪制度細化的合理性分析[M].法學,2012,(12).
[2]黎宏.刑法修正案(九)中有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立法——從如何限縮抽象危險犯的成立范圍的立場出發[M].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
作者簡介:王偉岳(1993-),男,漢族,陜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