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寧(組詩)
宋長玥
春日過南禪寺
風把春天往山上推。山上的風常念平安經
也念心經。
當太陽走過一半天空,風開始為母親們祈福。
如果我正好路過,
會停下來
靜靜聽完。
寺里端坐著菩薩
人間奔波著母親。
現在,我提燈過街,茍且生活。
為天上的母親唯一能做的,
就是春天將臨
在她求佛保佑兒子們的寺院,把思念關在風鈴上,
風吹一次,
鈴響一聲,
心痛一遍。
圣頌含淚,
而春風不知。坐在半山腰的風鈴聲不絕,
為江湖在近,以心為界。
但倘若我在舌根下取出鮮血,除了書寫母親
還能寫出什么;愛,寬宥,
虛空或無形之縛?
多少個菩薩
在春天超度了自己。
初冬上南山所見
一個人在天上,另一個人也在天上。
一個人往西和雪相遇,
另一個人被風吹遠。目之所及,他們經過了青海湖,但悲傷的大地繁錦沒有謝幕。等他們到達黃河沿,也許能看見活佛放生的一只羊,和我十年前在黃昏中問過路的紅衣老僧。
那些空他們早已經歷,因此在星星打尖的湖泊夜色縹緲,再荒也不為所動。半夜里會有一個人從附近的小鎮醉酒歸來,路邊草原薄雪泛光,犬吠遙遠。那時我不知道對自己說苦,而現在也不再告訴夜行人所有的痛。
兩人最終回去哪里?我在漏風的帳篷睡過一夜的珠穆朗瑪峰河谷?也許去日喀則黃昏就關閉了木門的寺院?或者在途中走散,為尋找彼此花費一生?
兩個人,其實是兩片狀如人形的白云。
它們飄過南山,高遠的陰影投在大地上,
正好被我發現。
初冬晴日,上南山
風的右面,是一片荒蕪之地:陽光的孩子們流落山巔,找不見一匹馱動夢的馬。兩只伯勞在樹叢下喋喋不休,不贊美生活,也不詛咒生活。遠方不曾到達,會不會比想象更美。
荒蕪之地
不安靜。
我在風的左面。春天花在那里聚會,
他們無所顧忌,
有的白得耀眼,有的紅著要命。
過了秋天,
命運不分好壞
都在泥土下安身。唯有魂不死不滅
長守南山
靜靜恭迎大雪。
我至今能一一叫出它們的名字,獻給親人的,
獻給戀人的,獻給生命的
獻給死亡的。
人把自己的心思交給它們,花最后低下頭。
現在,我更思念六月的一只蜜蜂
它在一朵花和一朵花之間奔忙,歸巢,直至累死。
人們嘗到了甜。
寄自西寧的兩行情書
1
兩粒瘦弱的燈光,三盞年老的馬皮燈,
一個男人遙遠的夜晚在紅紅的唇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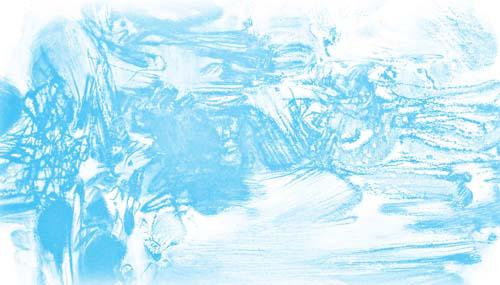
再遠的路長不過思念,等待的日子
風靜靜吹過平安。
盼望不是春天的露珠,一夜心傷,
只是平安驛外的芳草又長幾寸。
羊皮經卷在古道邊重現,它在上面寫著:
憂傷的人翻過山口,心碎的人活在人間。
2
金露梅失眠的夜晚,大風卷走月亮。
浪子被困西寧,街道中間擺滿喝空的玉杯。
三瓣丁香駐守邊城,走過平安的男子
守著青海湖,一滴寂寞的相思。
天鵝留下一座空城,一段牽掛不為人知。
平安驛,你把男人的心穿上。
——白天想你肝花痛,晚夕里想你心痛。
3
老鐵匠的鋪子油燈一夜沒滅,
懷念的老馬不打馬掌也能跑回平安。
三月爬山,四月過河,五月淋雨,
六月到身邊,心想得像一張紙了。
大眼睛,大眼睛,大眼睛,
不為別的,只為你,性命從刀尖上過了。
男人的高陸
1
秋深。青海男子西望:大雪直壓昆侖,颶風堆壘寂地。
父親仍在沉默。他的疆域,花開伏地,人往高處,
有不可言狀的驚悚之象。
他直視雪峰一側睪丸覆蓋半個草原的種牛,頗為得意。
他的世界似是雄性具象的組合。
靈魂游牧之地,一片闔寂。在痛中痛啊。
2
男人。
男人的心史是被血淚鉚定的記憶。他想起黎明,
一塊巨石爆裂——眾草向上的力量改變著命運,
天空成唯一的去向,他的目光砸開冰河。涌動。涌動。
他在碰撞中進行生命和生命的對接。
3
男人在生活中奔走,一次次被黑夜淹沒。
他掩懷潛行。前方不可預知。前方是一柄斷劍?
一抹紅光?一場大雪?一次沒有交鋒的戰爭?
一彎清冷的殘月?前方是兩個頑童搗亂的一盤棋?
是昨夜?是今天?是尖叫?是觳觫?
是雄鹿撞向峭巖的一瞬?前方是父親嗎?
前方僅是等待男人的生活。生命中必須踏上的大道。
他想從大地下掏出太陽。
4
那時,夜的流蘇沉如飛瀑。男子有些恍惚:
廢墟上一朵黃菊笑了,虛掩的雕花木窗內,繡花女子
將一滴血染上花莖,那時,大風吹動青海,
女子吹熄燈盞,無眠復起,念想之人尚在遠方。
在眾水低嘯的寂地,他裸身走向大河,母親的血啊,
男子淚落高陸,在生命逆溯的路上,
他察知的秘密從苦難開始。
而月下想他之人,久坐無眠。青海下起大雪。
5
太陽升起。男人的高陸緩慢展開:心在上午走一月的路程,
在下午也走一月的路程。
他把種子放在大地下面,他把河水澆在大地上面。
他把他舉到天空,青海的天空,你的兒子長著你的骨頭,
流著你的血。你看他在大地絕望的時候降下時雨,
他的確只是火焰水和火焰的保護者。
男人。男人。你生活的地方,你就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