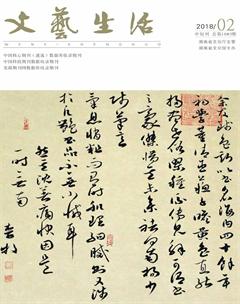“迷惘的一代”與美國夢
王圣瑤
摘要:“迷惘的一代”是美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思潮,它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繁榮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之后被現代主義浪潮所取代。“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們大都經歷過一戰,在戰爭中受到了肉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對戰爭結束后的繁榮社會抱有幻想,卻最終大失所望。而美國夢,則是一劑催化劑,使得那個戰后的短暫繁榮時期的化學反應更加劇烈,接受了這一思想刺激的美國人,開始奮發向上,努力發財致富,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迷惘的一代”青年們,正生活在美國夢刺激下的這個獨特的時期,然而美國夢不但沒有激勵他們前進,反而使他們的情況更加惡化。此時,原本就迷惘的青年們,被極其豐富的物質財富一再刺激,使更加不知何去何從,一味耽于享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美國夢變成了“迷惘的一代”青年們的噩夢。對這些生活在美國夢刺激下的迷惘的青年作家及其作品進行研究,將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青年們的普遍特征。同樣,跟隨著這些優秀作家的目光,我們也能更加清楚的認識到美國夢的虛無甚至罪惡本質,以及它終將破滅的現實。
關鍵詞:迷惘的一代;爵士時代;美國夢
一、“迷惘的一代”產生的歷史背景
20世紀初,世界經歷了一場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無情地奪去了無數生命的同時,更在人們心中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創傷。武器的大規模使用,使得生命看起來更加脆弱,更加不堪一擊,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沉浸在工業文明的美夢中,而是親眼見識到了它的可怕之處。信仰遭遇了危機,人們意識到,對上帝的虔信并沒有使他們脫離苦海;理性遭遇了危機,哲學家們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看到了曾經幫助人們擺脫蒙昧的理性,又使人們掉入了新的牢籠中。文明遭遇了危機,在有些人看來西方文明已經衰落,英雄時代的那些美好品質,古典主義的高貴典雅,浪漫主義的如夢似幻都已經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有骯臟的現實。就像菲茨杰拉德曾說的那樣,“他們是新的一代,長大以后發現所有的神祗已經死去、所有的戰爭已經打完、所有對人類的信念已經動搖”。面對這些事實,站在世紀之交的青年們感到無路可走。在美國,此時,有一種新生的力量在刺激著人們,那就是美國夢。美國夢代表了這樣一種思想,在美國,這個自由平等的土地上,任何人,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這樣的豪言壯語的確激勵了許多人發家致富。處于迷惘中的美國青年們自然也受到了美國夢的激勵,但當熱情過后,他們發現,財富,并不能買到夢想。“迷惘的一代”就存在于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
二、“迷惘的一代”與美國夢
(一)“迷惘的一代”的特征
20年代,僑居法國巴黎的美國女作家斯泰因對海明威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這句話也被海明威作為題詞而放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的篇首。海明威可以說是“迷惘的一代”青年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全面展示了這群青年們的生活狀態。“迷惘的一代”們雖然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迷惘,但他們卻有著共同的特征。
首先,反戰。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們,都不同程度上受到過戰爭的傷害,尤其是那些曾經上過戰場的人。海明威的作品《永別了,武器》就帶有強烈的反戰情緒。海明威本人在戰場上受過傷,曾經從身上取出幾百片彈片,戰時的痛苦回憶導致他長期失眠,入睡后也會被噩夢折磨,十分痛苦。海明威因此對戰爭十分痛恨。他的這一經歷也被他注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永別了,武器》批判了這個國家戰爭宣傳的虛偽性。索爾·貝婁在1976年的諾貝爾文學金獎授獎儀式上曾說道:“海明威可以說是那些在伍德羅·威爾遜和其他大言不慚的政治家鼓舞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的代言人。這些政治家的豪言壯語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這應當用鋪滿在戰壕里的僵硬的年輕人的尸體來衡量。”
其次,自我流放。
“迷惘的一代”的很多作家都長期旅居國外,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曾長期在法國僑居,這也使得在他們的筆下有許多異國風光的描繪。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的作用無非是兩種,一是作家帶著對本民族的認同和自豪與異國比較,從而升出更加強烈的優越感,另一種是作家對本民族的現狀極其不滿,對異國的情況給予高度贊揚,寄希望于本民族的改變。“迷惘的一代”顯然屬于后者,作家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現狀感到不滿和無力,紛紛來到異國他鄉,希望不一樣的風景可以緩解他們心頭的苦悶。
最后,憂郁悲觀,消極反抗。
“迷惘的一代”的青年們對他們所面臨的狀況持一種普遍悲觀的態度,他們不認為情況在未來會變得多么好。戰爭割斷了他們與舊世界的聯系,而新的世界尚未成形,他們在朦朧中探索,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因此憂郁、彷徨。《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杰克,雖然在大自然風光的撫慰下,在西班牙斗牛的刺激下,曾經找回過一些希望,但這些希望與現實無益,也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和愛人之間的關系,最終,太陽還是“照常”升起了,沒有任何改變。而杰克和他的朋友們對主流的價值取向顯然是十分不屑一顧的,他們經常酗酒就是對美國當時的禁酒令的一種蔑視,但反抗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們只能以一種戲謔的態度來嘲諷當時的種種制度規定,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真正改變它們,常常就是酒醒之后一切如常。《太陽照常升起》中出現的青年們,按照自以為正確的愛情、英雄觀行事,但可笑的是,這些價值觀已經被戰爭摧毀了,與海明威之后的作品中塑造的許多“硬漢形象”不同,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反英雄”。
(二)美國夢的破滅
夢雖然不總是美夢,但現實卻始終殘酷。美國夢刺激了美國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但在這種看似美好的外表下,卻隱藏著一些丑惡不堪的現實。金錢的巨大魔力,使得拜金主義大行其道,金錢仿佛可以代替一切,成為身份、地位甚至道德的象征,人們為了金錢,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擁有那顆像里茨飯店那么大的鉆石的布拉多克·華盛頓為了不讓任何人發現自己的寶藏,用盡了各種手段,賄賂、威脅,甚至不惜讓誤闖自己領地的人們付出生命的代價。對于被邀請到自己的鉆石王國里做客的朋友,這一家人也表現出了極度的自私,在他們看來,首先要盡可能的從好朋友身上得到快樂,這是完全自然的事,但在快樂過后,這些好朋友卻出于保護自家領地的目的被他們無情殺害,財富已經腐蝕了這一家人的良知,仿佛這個世界上一切的關系在他們眼中不過都是金錢關系而已。而當鉆石山最終不保時,男主人居然帶著一顆大鉆石,去賄賂上帝,此時,金錢不僅污染了世俗的各種關系,更是企圖去污染至高無上的神明。
與拜金主義和享樂之風一同到來的,還有上流社會的虛偽道德。《夜色溫柔》中的迪克,懷著美好的美國夢,憑借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出色的醫生,并且與自己的病人富家千金尼柯爾相愛并結婚,最終步入上流社會。然而他的這種成功并不被上流社會的貴族們認可和接受。迪克為了尼柯爾能得到更好的治療,不惜放棄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在醫學界大好前景,努力使自己融入上流社會的圈子,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并且真心幫助身邊的人,企圖改變上流社會的污濁空氣和虛偽道德。而在以尼柯爾一家為代表的上流社會成員眼中,迪克只不過是一個依附者,一個可以加以利用,在利用完了就可以拋棄的人。
上流社會有上流社會特殊的積弊,而放眼整個社會,則普遍存在著社會轉型之際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這一時代的社會風氣與之前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不僅是戰爭所帶來的失望和幻滅情緒造成的,而且與工業的進一步繁榮密切相關。工業的繁榮造就了經濟的繁榮,也改變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和一些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態度。而每當有改變發生時,就會有面對這些改變的不同態度,也就注定會產生堅持傳統與接受現代的思想沖突。
既然是夢,就總有醒來的那一天,爵士時代那些被夢境掩蓋起來的丑惡現實最終還是會打破夢境的美好,菲茨杰拉德清醒的認識到了夢境終將破滅的現實。“細讀他的故事便會發現一種基本格式:開首總有夢想,隨之便是奮斗,到頭來卻是失意和絕望。”作為爵士時代的命名者和桂冠詩人,菲茨杰拉德實際上是在書寫這個時代的訃告。縱觀菲氏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的一大部分小說都是具有自傳色彩的。菲茨杰拉德出生于一個不算太富裕的家庭,但父母還是把他送入了私立學校,他于1917年離校入伍,在此期間,他愛上了年輕貌美的姑娘澤爾達,澤爾達答應他,只要他可以有足夠的錢讓自己過上舒服的日子,就愿意嫁給他。可是當時的菲茨杰拉德沒能如愿,直到幾年后憑借《人間天堂》的發表,菲茨杰拉德在文學界有了一席之地,財富也隨之到來,這才最終與澤爾達結婚。婚后夫妻二人出入上流社會,成為當時美國青年們所向往的年輕、美貌、財富和幸福的象征。可是好景不長,菲氏自覺創作的靈感在枯竭,而他與妻子之間的爭吵也越來越多,最終妻子患上了精神病,菲氏不得不把她送進精神病院。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菲茨杰拉德深感孤獨與寂寞,常常用酒精麻痹自己,最終英年早逝。可以說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一生就是生活在那個爵士樂時代的“迷惘的一代”青年們的真實寫照,而他帶有自傳性質的一些作品,比如《夜色溫柔》、《了不起的蓋茨比》,短篇小說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則更是以一種藝術化的方式像我們展示了那個奇跡般的年代。
菲茨杰拉德在美國夢的紙醉金迷中,清醒地認識到了它的虛無本質和好景不長,他的作品無疑給了還沉浸在美國夢中的美國人一劑清醒的湯藥。菲氏的小說雖然在當時并沒有產生什么轟動一時的效果,然而它的價值卻在之后的幾十年問被充分的挖掘出來。菲茨杰拉德這種在盛世之中的危機意識,不僅對于當時的時代,而且對此后所有的時代都具有永久的借鑒意義,這也是他的作品如今依然暢銷不衰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