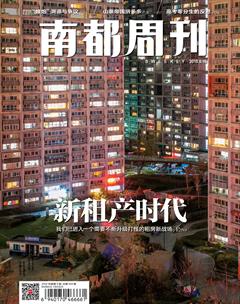這個大和尚做P2P,爆雷了
宋朝有不少寺院是當時非常活躍的P2P貸款平臺,陸游說:“今僧寺輒作庫,質(zhì)錢取利,謂之長生庫。”這長生庫,便是寺院設(shè)立的放貸機構(gòu)。許多宋朝人在急需用錢時,往往都會向寺院的長生庫借貸。
話說宋神宗元豐年間,開封府下轄的祥符縣知縣孫純,被提拔為梓州路(今川北)提舉常平官,要到川北赴任,路途遙遠,需要一筆盤纏,孫純可能手頭沒什么錢,便找大相國寺的住持行親借錢。
孫純與行親是舊相識。原來,行親出家之前,當過孫純的管家,替孫家“主治田產(chǎn)”。后來不知為何,行親出家當了和尚,并成為大相國寺的住持。
故人前來貸款,行親當然不敢袖手旁觀,置之不理。不過大相國寺大概未設(shè)長生庫,沒有從事P2P業(yè)務(wù),因此,行親便從寺里的“常住錢”中拿出100貫,借給了孫純。
但行親擅取“常住錢”一事,給大相國寺的僧人宗梵發(fā)覺了。宗梵便跑到開封府舉報:“行親輒持百千出,疑有奸。”意思是說,行親擅自帶了100貫“常住錢”出寺,很可能是侵吞寺款。
當時的開封府知府叫做蘇頌。接到宗梵的訴狀后,蘇頌一問,發(fā)現(xiàn)原來是寺院住持借錢給了老朋友,認為此屬民間借貸,你情我愿,沒什么不妥,便駁回宗梵的訴狀:“宗梵告非干己事,不當治。錢隸常住,非官給,無貣貸法。”蘇頌駁回訴狀的理由有二:第一,寺廟的“常住錢”并非政府公款,住持有自由支配之權(quán),行親用它放貸,官府不必干預(yù);第二,宗梵所告之事,與己無關(guān),不具備訴權(quán)。
蘇頌還以宗梵無事生非、誣告住持為由,將宗梵打了一頓板子,打發(fā)回大相國寺。此時,孫純已聽說了宗梵跑到衙門檢控一事,也趕緊將100貫錢還給了行親。
這事兒本來就這么過去了,誰知事情被御史舒亶得悉——宋朝的御史官,就是專門跟行政官過不去的。舒亶一看蘇頌的裁決,很不對勁啊。所以很快就對蘇頌提起彈劾,稱蘇頌司法不公,包庇孫純與行親。
蘇頌的裁決是不是有問題,要看怎么定性寺院的“常住錢”。按蘇頌的意見,寺院“常住錢”不是官款,用于放貸并不違法。但事實上,宋代寺院的“常住錢”,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政府撥款。換言之,“常住錢”屬于公款,而不是寺院住持的私房錢。
那么寺院住持可不可以將“常住錢”用于放貸呢?我們不妨再來看看金代《西廂記諸宮調(diào)》的一個細節(jié):張生為給崔鶯鶯送定情信物,找寺僧法聰借錢,法聰說:“常住錢不敢私貸。貧僧積下幾文起坐,盡數(shù)分付足下,勿以寡見阻。”可知在宋代,寺院“常住錢”是不允許“私貸”的。大相國寺住持行親的行為,已構(gòu)成挪用公款之罪。孫純私自借用公款,也觸犯了法律。
如此看來,蘇頌的裁決確實是大有問題的。彈劾他的御史官還指控說:聽聞孫純是蘇頌的姻親,又聽聞開封府接到宗梵的舉報后,立即便有人告知孫純,讓孫純趕緊將借款還給行親。宋神宗一聽,大怒:“輦轂之下,近臣敢以情勢撓法,審如此,則不可不治。”
于是,朝廷委派刑部、大理寺的司法官呂孝廉、韓晉卿,在同文館成立一個臨時法庭,徹查此事。北宋京師的同文館,原為接待高麗使團的館舍,因房屋寬敞,又常閑置,經(jīng)常被大理寺等司法機關(guān)借用來作為審案之所。這時候,蘇頌也“自請罷職”,請辭開封府知府之職,接受調(diào)查。
經(jīng)過調(diào)查,同文館臨時法庭發(fā)現(xiàn)御史官的指控基本屬實:孫純原為蘇頌“女婿堂妹之子”;開封府判官徐大方、推官許彥先曾密諭孫純償還行親貸款。因此,主審法官呂孝廉與韓晉卿裁定蘇頌“坐失出杖罪”,即存在輕縱犯罪行為的過失。
但御史舒亶又提出抗訴,認為孫純與蘇頌“實為近親,不可以失論”,蘇頌的行為,可不是“失出人罪”,而是更為嚴重的“故出人罪”。
最后,司法機關(guān)的終審判決裁定:孫純行親的借貸關(guān)系為非法,“貣貸之人各合有罪”;前開封府知府蘇頌在審理宗梵告行親一案時“故出人罪”。
涉案諸人也全部受到處分:蘇頌降官階,徒知濠州(今安徽鳳陽);孫純“奪一官,并勒停”,降一級官階,并且停職,提舉常平官顯然是當不成了;徐大方、許彥先“沖替”,一并降職;韓晉卿、呂孝廉也“坐理斷不當,各罰銅二十斤”。
大相國寺住持行親由于不是官員身份,史料沒記載對他的處分,但根據(jù)宋代“貣貸之人各合有罪”的法律規(guī)定,他觸犯了杖罪,將受到杖刑。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僧人生活可以世俗化,但沙門必須遵守王法。